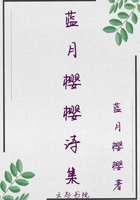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曾用笔名孤松、猎夫等,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著述甚多,现已编辑出版《李大钊文集》(上、下册)。其人口思想集中反映在《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等文中。
一
李大钊的人口思想,主要在于批判马尔萨斯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理论。
他首先指出“战争乃饥馑之子”的谬误及其危害。他说:“余曩居日本,时闻彼邦政界山斗,奋勖其国人者,辄提二义以相警惕。彼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他认为,今世列强之发动战争,其目的在于解决人口问题。人口过多,固应求解决之道,但以战争来解决人口问题,无异颠倒本末,趋于自杀。“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Pvadhon氏(蒲鲁东)‘战争乃饥馑之子’之言,今乃适居其反,而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荒谬的观念?其根盖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为马氏的人口论的要旨,就认为地球之面积有限,土地收益又为递减规律所限,食物以算术率增加,人口以几何率增殖,如不节制生育,必陷人口过庶之境,人口过庶,灾祸战争乃不可免。正因马氏人口论学说的影响,才有把人口过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之借口。
李大钊认为,马氏这种学说是不能成立的。他说:“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他列举了四条理由来驳斥马尔萨斯的学说。一是从各国实际情况看,不唯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他以英、美诸邦之统计,作为例证;二是就算人口多了,也会因“人类无限之天能”“求无尽之物力”,“使之裕如而得养”;三是即使有土地报酬递减之虑,人类也可发挥其天赋之能与自然力抗敌,他用科学技术之发展,文明进步的具体情况,阐述了战胜自然的成就,说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完全可以克制的;四是马尔萨斯武断地以人口过庶为确定前提,而又一方面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一方面暗示战争之难免,这就必然“潜滋”侵略者“贪惰之根性”。正由于马尔萨斯的这种人口论,“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以有今日之惨祸”。
李大钊认为,对于这种为侵略战争制造口实的学说,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如果听任这种谬论流毒于世,使它成为互相残杀的依据,则人类就和“禽兽之互相吞噬者”相去无几矣。
李大钊在批驳了饥馑引起战争的谬论后指出战争造成饥馑,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撕破了日本“政界山斗”借口地少人多,为图生存必须对外侵略的面目,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对于提醒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警惕性,更具有爱国主义的积极意义。但他对于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本质,却没有完全正确地分析。他说:“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什么是贪惰呢?他说:“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唯贪与惰,实为万恶之源。人间种种罪恶,皆丛伏于此等恶劣之心理。……唯在废除此等根性,是乃解决人口问题之正当途径,消弭战争惨象之根本方策也。”
李大钊还不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战争和人口问题,而在超阶级的所谓“贪”与“惰”的“恶劣之心理”去寻求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时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处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
二
如果说1917年3月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李大钊只是就战争问题一般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那么,在1917年4月他写的姊妹篇《战争与人口》这篇长文中就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观点,对战争与人口问题深入、具体地进行了论证。
第一,李大钊以渊博的学识、犀利的笔调,纵论古今中外学者的人口经济思想,溯自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外国的希腊、罗马。人物则管仲、韩非、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考察了人类历史上生存进化的演变,阐述了“处之而善,其生也荣;处之而财,其亡也必”的道理,指出:“夫天之生物,足以养人而有余,人不知求所以自养之道,唯贪人之养,以为攫取之计,则人之不智不义,非天之不仁也。”对于这种不智不义之事,“人口论倡守于前,天演论继兴于后”。他批评这些“硕彦宿哲”,“徒因一时之感想,远种前世之恶萌”。“足以助战祸之昌炽者。”这些谴责义正辞严,实在是一篇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檄文。其进步意义,应予充分肯定。
第二,李大钊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远不及管子的地数说。他说:管子的“五子二十五孙之说”虽“与马说相通”,但“管子地数之说,则非马所能见及”。他引用《管子·地数篇》管子与齐桓公的对话:“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韩非之策,虽用于秦而霸天下,当时受兵战之祸者匪浅。马氏之说,今虽渐明其误,而一为好战之桀所执,犹足以祸今日之苍生于无穷,皆未足喻管子能者有余、拙者不足之旨也。”这里指出的是:国家不在大小,人口不在多少,关键在于是否善于治理,是否发挥聪明才智。菽粟等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要治理有方,勤劳生产,就会富裕有余。马尔萨斯之流戚戚于地少人多之忧,不懂能者有余、拙者不足之旨,连中国两千多年之前的管子都不如。李大钊对马尔萨斯的借古喻今的批评,人们尚未多听引述,但这无疑是值得注意的思想。
第三,李大钊以自己的方式批评了马尔萨斯的所谓三定律。他首先概括指出马氏的三定律是:“(1)食物不给则人口不增;(2)食物充裕则人口繁殖;(3)人口增殖之度越于食物生产之度,则祸患与罪恶,必不可免,以为天然之遏制。”然后,逐一予以驳斥。他说,按达蒲得(Doubcday)的说法:“人类及他种生物繁殖之度,皆与资养成反比率”,而不是马尔萨斯所说的食物与人口增殖成正比。他用“天地刍狗”之说,批判了人口增殖超过食物生产,祸患必不可免之律。他引用老子的话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把这句话和加雷关于美国人口增加速度并不快的说法相印证,得出结论说:“乃知天地间之供人刍狗者,至无穷尽。唯人致物于适。所用莫不赡矣。此天地之不仁于物者。正天地之仁于人也。人乃欲以天地之不仁于物者,而亦施之于同类。”就是说,赖天地之恩赐,人类如能善处,本来应是所用赡足的,然而,由于人类的贪与惰,导致自相残杀的祸患,使“人类虽无供异类吞噬之患,而战乱不幸足以代之”。并不是人口增加超过食物,才使祸患必不可免的。
李大钊还以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来解决人口问题,批判马尔萨斯的“徒塞人口”的观点。他从两方面来阐述:一是增加生产,就可满足人口的需要。他说:“物力之弃于两间(即天地之间——引者)者,既无涯厩,苟有缺乏之感,要在不可依人类独秉之智能,谋于物力之开发,而必自抑天赋之情感,谋于人口之制塞也。”二是人们生活赡足了,人口增殖自然会减少。如果人们都达到“小康之域”,“足以致富而自养”,会追求“其境之益适,则人口之增殖,不节自节,即任其增,亦无过庶之忧”。因此,他认为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不此之务,“徒塞人口至于何度,贫困之苦,终惧无以自免耳”。
李大钊从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探讨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并把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放在主导地位,无疑是科学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然,李大钊在当时也还看不到在人口过多的情况下,自觉地节制人口的必要性,这是其不足之处。
三
发挥人类的智慧,发展科学技术,人类前途乐观论,是李大钊人口思想的重要部分。李大钊高瞻远瞩,展望人类的未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的前途。他认为,人口“就会增加无限,地积地力今犹未至穷极之域;纵有穷极之一日,人类之知力与自然之势力,皆无尽藏,用之不竭,取之无穷,其时当有以自为之所”。
他进一步推论:地球之于诸天,乃“沧海之一粟耳”,就算“人口之庶,遍于寰区,土地之力,穷于开发”,然而“星云无限”,“诸星之间,将来或有交通,人类于地球之繁殖,苟至于无地自容,斯谋转徙他星,依科学之进步,竟克致此,未可知也”。他用今昔对比,说明这绝非幻想和空谈,是有实现的可能性的。他郑重地说:“斯非驺衍九州之空谈,千年以往,有语以今世欧、亚、美、非之广漠者,人皆以荒诞弃之,有甚于今日之闻斯言者。而今则舟车络绎,天涯堂奥矣。”如果让古人看到今天的文明,“彼且惊神疑鬼,不信为人间之实境也”。对于所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李大钊说:“一旦文明进运,堪以制其势而胜之,一时著为定律者,安见其必存耶?”
如何才能达到文明进步呢?李大钊认为,要大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正确运用人们的才智。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未能普行,才智误于应用……不唯未能举其全力以战胜自然,反有以自杀其势,致任自然势力之独行,而犹不自悔悟,复龈龈焉虑自然惠与之不丰,文明进运之难恃,岂理也哉”?他指斥反动统治阶级滥用人类智慧和巨额社会财富,去制造杀人武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当然就谈不上战胜自然,为人民谋福利,而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四
李大钊的人口思想是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他的一段话却引起了不同的理解。李大钊写道:“余虽对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煞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稍存贪惰之心,必来穷乏之患,而以无敢邻于怠荒焉。余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
这一段话的本意应该是:人口问题乃是贪惰自弃的结果,只要废除此等劣根性,就能解决人口问题。而马氏的人口论,恰恰可以警戒人们勿存贪惰之心,勤奋前进,以求文明之发展。否则按马氏人口论的说法,就将招致穷乏之患。所以,关于“不否认其说之本旨”,无非是说马氏的人口论是警戒贪惰,鼓舞勤奋的,因而是不能否认的,其经济学上的价值也是不能抹煞的。李大钊只是在这种意义上肯定马尔萨斯的。至于马氏放言高论什么“人口无限,土地有穷”,人口贫困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等论断,李大钊是不赞成的。因此,不能认为除此而外,李大钊还有什么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肯定之处。
此文载于:西北人口,19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