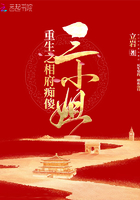没有胜利者的喜悦,李愚这两天倒是安静了很多,他还记得当年天牢中一个凤阳的官员说过一句让他记忆犹新的话“当你置身群狼之中,永远别为了一次胜利而放松警惕。”
李愚当时有些疑惑,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的人按理说不至于落魄到天牢囚徒的下场,于是便问道:“您既然这么明白事理,怎么如今到了这般田地?”
那人一脸的苦大仇深:“坏就坏在我赢了两次。”
李愚若有所思。
正如如今这般,自己已然算是连胜了张伯骞两场,若是依然不懂得收敛,很难保证这宛如铁桶的扬州官场会不会对自己群起而攻之,自己就算是过江龙,也架不住这扬州的群莽不是?
立于这边虽然对于打了一场大胜仗而沾沾自喜,但是吕承欢这几日确是闷闷不乐。究其原因,不过是之前李愚将几百两银子打了水漂罢了。没错,就是字面意思,这颗让一向勤俭持家的吕承欢十分不满,那日在公堂之上哭得梨花带雨,十分中有八分是哭那几百两银子倒是真的,这一点李愚倒真是理解错了。
再说张伯骞这边,经历了几天的意志消沉,张伯骞整个人瘦了一圈。把自己关在房间中也不出门,一应用度全靠下人伺候,就连扬州官场每月的例行聚会都不去了,仿佛变成了一个宅男。最重要的是,他好像换上了神经衰弱,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在嘲笑他,他仿佛能听到那些人的心声:“张伯骞,你啥时候挂印啊?”
“咚咚咚”
门外三声敲门声响起,惊扰了躺在床上发呆的张伯骞,张伯骞眉头一皱显得十分不耐烦。
“谁!不是跟你们说了没事别来烦我吗?”
张伯骞起身拿起地上的一只鞋向着房门丢去,恰在此时门外之人不请自入,一开门刚好遇上张伯骞的飞鞋,躲闪不及正中面门。
只见来人面无表情的将脸上的飞鞋缓缓拿了下来,脸上还挂着一个清晰的红色鞋印,足见张伯骞丢鞋之用力。
“怎么着张老弟,案子你也不办了,衙门你也不管了,聚会你也不参加,你这好好的扬州知府不当,练上暗器了?”
张伯骞一抬头,整个人仿佛触电一般,咕噜一下爬了起来,只因为这来人不是别人,乃是扬州府的同知,胡维桢。
这胡维桢虽然品级比张伯骞低上一级,但是扬州官场情况特殊,在这里几乎自成体系,说话的分量轻重自然是与官职有关系,但没有绝对的关系。相反,倒是与资历有关,例如这扬州府理论上最高的话事人自然是张伯骞这个四品知府,但是对于稍稍对扬州官场有了解的人来说,大家都知道资历最老的扬州本地人胡维桢才是扬州真正的土皇帝。而对于这位土皇帝上面还有个喜欢藏在幕后指点江山的“太上皇”褚庭春,大家到是少有耳闻。不过这扬州说到底,胡维桢说话的分量可以说是最重的,没有之一。这也从侧面可以让人们理解为什么张伯骞如此不顾一切的的想要表现自己,做一个扬州的“大英雄”,很简单,增加自己说话的分量呗,只不过,这一回他玩砸了。
原本还一脸怒容的张伯骞见到胡维桢,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了一个羞惭的微笑。
“胡大哥,你怎么来呢。不好意思啊,我刚以为是。。”
胡维桢倒是对于张伯骞的“暗箭伤人”没有生气,而是微微一笑,宛如到了自己家一般坐到张伯骞床前,用手安慰似地拍了拍张伯骞的肩膀。
“张老弟这是把我胡某人当了那条鲤鱼了?”
胡维桢不提李愚还好,胡维桢一提起李愚张伯骞整个人的气势顿时软了下去,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胡大哥不要取笑我了,胡大哥不用担心,我张伯骞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技不如人,我自然会依我之前所言辞官挂印。不会给上面任何一个借口对我扬州不利的。”张伯骞眼神空洞,哪还有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这次的打击对他而言真是太大了。
“胡大哥我就是不明白,那李愚难道开了天眼不成,我自认为我的计划天衣无缝!他怎么会知道了我的部署,而且还能在我眼皮底下玩了一招李代桃僵,我。。。只是不服气。。。”张伯骞恨啊,他双手紧握成拳,重重的砸着床板,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无能狂怒。
远在府中的李愚不自觉的打了个喷嚏,心中暗道“狗日的张伯骞肯定又骂我了。”
胡维桢与张伯骞相处多年,自然是知道他的脾气,此时无论怎样的劝慰估计对他都没用。张伯骞虽然为人为官都比较庸碌,但是极为好面子,这一点他是再清楚不过,索性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一次打击就这般一蹶不振了?你现在这般状态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你放心,这件事就算是揭过去了,这一次虽说你折了面子,但是对于扬州官场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胡维桢到底是老姜,几句话说得张博千里马来了精神,怎么自己还有功了?
“胡老哥此话怎讲?”张伯骞一脸的好奇道。
胡维桢起身站了起来,背对着张伯骞解释道:“有两个好处。其一,李愚来这扬州的日子也不短了,虽说他也算安分守己,但咱们要是不敲打敲打他,难免让其人为我扬州官场也“不过如此”。你此番所为,倒是可以给他提个醒。”
“第二呢?”
胡维桢捋着自己的山羊胡转身看着张伯骞道:“第二,之前褚老弟曾经试探了这李愚几次,如褚老弟之言,此人似乎并不属于任何派系,他来扬州倒好像真是走了狗屎运。而且褚老弟似乎极为看重此人,一再向我推荐,似乎是想让他加入我们。褚老弟的脾气你也知道,比较认死理,他认定的事情一般人改不了,我之前确实有心试试这人是否真如褚老弟所说那般,你倒是帮了我不晓得忙。所以这次你就不必过于计较了,这篇就算翻过去了,此时,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张伯骞闻言如蒙大赦,自己原本以为这一次自己的官就算是当到头了,如今虽说丢了面子,但能换来扬州官场的不赏不罚已然是万幸,哪还敢奢求别的,想到此处原本皱紧的眉头叶欢欢舒展开来,这一关,自己算是过了。
“不过,张老弟,为兄有句话确是要提醒你。”
张伯骞双手抱拳,对待胡维桢的态度就像一个学生一般聆听教诲。
“胡大哥请说。”
说到此处胡维桢面色一改之前的平和,转而多了几分阴冷,这瞬间的变化让胡维桢不觉打了个冷颤。
“你这次所为终究是自己肆意妄为,这样的事情,就这一次。而这一次机会还是看在你为扬州奔波多年的份上,加之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我这才为你出言作保,可若是再有下次。。。。”
胡维桢没有说下去,但张伯骞又怎能不心领神会,胡维桢所谓的下次自己怎会不明白,自己之前两任扬州知府“过劳”死在任上的手笔出自何人,自己又怎会不知道,没有人能将扬州的故事站着带出扬州,除非是扬州自己人。想到这,张伯骞诚惶诚恐的对着胡维桢鞠了一躬。
“伯骞明白,谢胡大哥相保,伯骞自知自己罪孽深重,自愿减去今年的分红,就当是给大家赔罪了。”张伯骞语气颤抖,竟是连自己的恐惧都藏不住了,一个久在官场的老油条能如此失态,足见扬州官场下手的狠辣。
胡维桢懂得什么叫点到即止倒也没有进一步威胁,对于张伯骞这种扬州的“老人”来说,能力不重要,信任才是最重要的,毕竟想要再找到一个可靠的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段过程恐怕需要许多年。
“好了,张老弟,何至于如此。我此番前来想要劝慰张老弟倒是其一,最重要的是这次聚会老弟没去,老哥这次来是向老弟转达一件大事的。”
张伯骞心中一惊,大事?胡维桢此人极为严谨,看似谦和但是却是个很教条的人,在他口中能被称为大事的事情不多,上一次他说出大事还是在酒席间接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就连李愚来扬州任职,在他口中也不过是件小小的“麻烦事”而已。
“能被胡大哥称为大事。。。。。。莫非!”张伯骞也不算笨,本能的察觉到这件事可能跟上面有关,难不成上面的局势明朗了?
胡维桢一脸的凝重:“看来你已经猜到了。我们接到线报,锦衣卫在扬州的衙门主理换人了,算日子应该已经到扬州了,只是目前他还没有去锦衣卫衙门报道,只怕。。。”
“难道他们在暗中调查我们?”
“不好说,不过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密切监视一切外地来的人,这人上任必然不是孤身一人前来,身边随从应该很多,倒也不算难找。。”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已经吃过一次自作主张的亏了,张伯骞自然不会再次蠢到现在提出自己的意见,更何况眼前的是胡维桢。
胡维桢似乎在想些什么,淡淡地说了一句:“现在这些可以先放一放,不过眼前你得跟我去个酒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