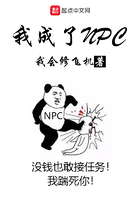7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年月,“老女人”是73年中大概六、七月份调走了,他老家是响水、灌云那边人,家里动了一些关系,到那边一个国营厂当了一个驾驶员。缺少了这个关系,尽管和张宁混得比较熟识了,但我还是到定埠“街上”时也总不好意思去“息个跘”,真正遇上也是站在路上谈上几句话,或多或少,完全凭双方的心境和时间。73年年初小五子也调走了,到六合一个有他母亲关系的大队当“广播员”,之后在那里选入“工农兵大学生”,彻底离开了农村;“篮园的”也因其母身体原因几乎不再来村上,所以我几乎就是一个人住在村上。我那时也不下地干活,“金头”让我暂时在村上小学代课,除每周三下午必须到公社中学开一次会,其余业余时间总在忙活自己的“自留地”里的那些蔬菜和自己的养的几只鸡,晚上看书,过着平淡而无聊的日子。本来亲近的人越来越少,就更加不想外出“串联”了。不过,在与其它同学接触中,多次听到张宁的名字,总是些有关“风月”的“花边”。
73年底,张宁又来到我们村上,那天是快傍晚乡人要收工时,学校已放寒假,我也回到队里与乡人一起干活。收工回来,一眼看到张宁就站在我的屋门外边等着我,忙让进屋,正寻思去乡人那里买几个鸡蛋,被张宁制止了,说他带菜过来的,只叫我多准备一些蔬菜,说还有几个人要过来。冬天地里没什么菜,队里分给我两分自留地我种的全是“矮脚黄”,这是我从南京种子市场买来的品种,乡人不种这种,乡人种的都是长杆青菜,就是那种腌咸菜的。挑回七、八斤,和张宁一起到村口小塘洗好,回去到屋里,看见五、六个人已在家中,其中包括“三掌柜”和毛头,其余都不认识。铁锅里放着一个咸猪头,看来这就是他们带来的“菜”,我认定猪头肯定来路不正,也不管了,放上水埋锅烧饭。那时都是刚放下筷子就能吃第二餐年纪,何况有荤腥,七、八个人,连菜带肉一顿吃的干干净净,最后连锅里煮咸肉的肉汤被众人就着锅巴吃的一点不剩。
话说当年,说句实在话,“偷鸡摸狗”不仅是传说中“二流子”的“专利”,许多“知青”也做过这些不上台面的活计。搬入新房后,我们几个也抓过几只,只是吃的时候,并没吃出什么鸡肉的美味,满满都是“三八作风”中除“团结、严肃、活泼”外的感觉。我相信乡人心里总是会怀疑到我们,只是缺少“捉奸在床”凭证而已,否则定是会上门追讨的。因为母鸡在当时条件下,关系到一家人的包括小到“针头线脑,洋火煤油”,大到“油盐酱醋”等各项开支,断不可小觑。乡人说,在老太太眼里,母鸡和女儿是并列在一个地位上的。后来回乡,和熟悉的中老年妇女聊天时经常被追问过当年是否偷过她们家的鸡?尽管我从她们表情中看出问话中调侃意味占98%,依然“正人君子”般的咬紧牙关,全盘否定。先烈说过,“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但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那是我党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