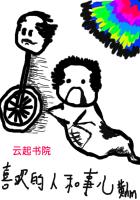风把卿欢的长发吹得四处飞舞,她捋了捋,对面的阮尽南没有回答她,接着她又被打了一下。阮尽南站在对面,手里还颠着几颗石子,风吹开他的碎发,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似乎在笑,淡到无法察觉的笑。
就你会扔石子吗?卿欢捡起他打过来的石子,看着他站的位置瞄准了用力扔过去,只是她命中率实在是低,几乎全都落了空。然后阮尽南又捡起她丢过去的石子反过来打她,两个人在楼顶,中间隔着风,朝对方扔石子,玩着小孩子的幼稚游戏。
卿欢有幸打到了阮尽南的脚踝,只略微擦过了他的裤脚,她也兴奋得边跳边叫。涂城收拾好衣服,准备下楼了,多待一会儿说不定还会殃及无辜。
卿欢捡起最后一颗石子随意一扔,没想到正中阮尽南脑门,他捂着额头对卿欢怒目而视。卿欢一看不太妙,连忙转身就往楼下跑去了,嘴里还喊着:“明明你先动手的,这可不怪我!”
涂城走到楼梯口的时候脸颊被石子击中了,他低头看着那颗本该打在卿欢身上的石子咕噜噜地滚下去,扭过头去看对面,哪里还有半个人影。
跑得真快,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下午吃完饭在房间里看着书,卿欢一直打喷嚏,流鼻涕,脑袋也昏沉沉的,她觉得自己感冒了,肯定是睡午觉的时候没盖被子又上楼顶吹了风,受了凉了。
傍晚,卿欢恹恹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涂城端着热水和药进来,卿欢从涂城手里接了药,连杯子也懒得拿,将嘴巴凑到杯边沿,涂城稍稍倾斜了一下方便水流进她嘴里去。
七点的时候涂城端着一碗白粥进了客厅,看见卿欢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把粥放在茶几上,把她叫醒。
她乖乖地喝完了粥,涂城叫她回房间睡觉,她点点头,走的时候对涂城说:“你比我爸都好。”
只有生病的时候才会这么乖,有女生的样子。涂城收了碗也回房间了,十点过后院子里一片漆黑,安静得只听见虫鸣了。
十二点的时候卿欢醒了,脑袋晕晕的,看什么都很模糊,睁了一会儿眼睛就酸涩。她睡得很不舒服,鼻子里塞了棉花似的难以呼吸,喉咙干痒,摸黑下床打开灯后发现床边放着她的保温杯。
她拿起保温杯,很重,打开,已经加满了水,喝了一口,温热地流淌进她干燥的喉咙,像雨落在干涸的土地。
她关了灯心满意足的睡下了,后半夜一直睡得很浅,被风吹窗户的声音吵醒了两次。就在她再次快要入睡时,听见了玻璃摔碎的声音,她微微睁眼,那声音消失了,以为是自己幻听了,又闭上眼睛。
闭眼不到十秒钟,更加清晰刺耳的玻璃摔碎的声音传到了她的耳边,卿欢睁开了眼睛,这一次她确定不是幻听了。
声音是从阮尽南家传出来的,除了玻璃摔碎的声音还有重物倒地的闷响,一阵一阵地,紧接着,她就隐隐约约听见了一个男人模糊不清的怒吼声。
她呆怔了三秒钟,猛地坐起来掀开被子,跳下床,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差点连鞋也忘记穿就跑了出去。
漆黑的凌晨一点半,弯弯细细的月亮高悬,月光很淡,星辰寥若,怎么也照不清楚脚下的路。
天地间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虫鸣声,仿佛是万籁俱寂的深夜,打开了家门的那一刻,只有突兀而尖锐的嘈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