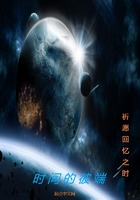雪如鹅毛漫天,把个天也下得沉重起来,司马黛钻进车里,手紧紧扣住垫子,马车慢慢的滚动,看着白茫茫的雪,心里空落落的,忽然眼前一晃,却见阮籍跳上马车,眼神深邃的看着她,过了一会笑道:“你不来,我们不是也可以去找你?”他端坐下来,用自己的手包住司马黛的双手,沉声道,“你这手再冻下去,恐怕就得废了,到时怎么侍候老爷我?”
他的手极暖,司马黛顿时觉得手热起来,过了一会,阮籍放开她的手,塞给她一个暖炉:“刚才你掉的,这么冷的天,以后就别出来了。”
司马黛点点头,笑道:“老爷你英明神武,体贴小人,小人定不辜负您的厚爱,以后定当竭心尽力侍候您。”
阮籍哼了一声,选择一个极为舒适的姿势,躺了下来。
风依旧刺骨,马车悠悠的钻在风雪里,渐渐远去,风雪中,站着一个人,一身白衣和白茫茫的雪融为一体,看不清,只是乌黑的发丝落满积雪,他如一棵松,站在风的劲头下,迎风独立,看着马车慢慢远去,最终看不见。
刘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过来,站在山涛旁边,极懒的说道:“巨源这次错了,她是一个好丫头。”说完又沉沉的睡去。司马黛从马车上下来,雪已经停了,阮籍对她挥了挥手,便让人赶着马车离开了,静谧的积雪中,司马黛望了望离去的马车,又低头看了手腕一眼,最终一言不发的从后门进了府。
司马黛还未穿过桃林,便见花间急急的迎上来:“小姐,你可回来了,大公子吩咐奴婢,说是您一回来就叫您去他的院子。”
司马黛点点头,便往司马师的院子走去,路上的积雪铺了厚厚的一层,仆人们早已经在清理路上的积雪,离司马师的院子近了,人便渐渐少了,四周静得只听得雪压过竹枝的声音,穿过层层叠叠的游廊,便见司马师一身单薄的衣袍,正在独自下棋。
“大哥穿得这么少不怕冷吗?”司马黛走到他面前,看着他专心致志的独自对弈,旁边的水呼着热气,竟沸了许多时。
司马师看着棋盘,含笑的说道:“刚起身,忘了。”
司马黛点点头,坐到他对面,笑看着司马师,司马师的眉目秀雅,眼下的那个血痣触目惊心,却徒添了一份华艳,心想原来大哥也是一个美男子,怪不得徽姐姐这么义无反顾。
“你看什么?”司马师温润的笑道,视线却没有离开棋盘。
“没什么,就是觉得大哥风流倜傥,艳冠京华,无人能及。”司马黛口一顺,便又开始溜须拍马。
司马师却抬眼看她,笑得更加温柔:“那比之嵇叔夜如何?比之阮嗣宗又如何?”
司马黛一愣,随后笑道:“大哥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司马黛瞧了一眼棋盘,说道,“各执牛耳。”
司马师看了她一眼,却看见她双眼盯着棋盘,眼神一敛,却只是昙花一谢,温柔的说道:“你是指什么?”
“指人,也指事。”司马黛笑如春花烂漫,“各有千秋,无法比拟,但都是美男子。”她顿了顿,又伸手指指棋盘,随后说道,“这棋盘上已经势均力敌,哥哥可要加把劲才好。”
司马师微微有些诧异,柔柔的说道:“阿黛看出什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棋盘相当的凶险,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只是不知道哥哥意在哪一方。”司马黛忽然吐吐舌头,笑道,“阿黛本来就不精棋艺,胡乱说的,哥哥别在意。”
司马师忽然眼神汹涌波动,他站起身来,拾起狐裘便细心的穿上,看着司马黛说道:“我倒是快忘了,叫你来是想告诉你,皇太后让你进宫一趟,说是宫里的梅花开得盛,听闻你又喜欢,特意备了晚宴,邀你一起赏梅。”
司马黛惊呼一声:“我何时说过喜欢梅花了?大哥,这是鸿门宴么?”
司马师微微一笑:“哪里那么多鸿门宴?不过说说话而已。只是说话注意点就行。”
司马黛点点头,却觉得司马师还有什么话没说,但是看他的样子,也看不出什么,只好笑着:“那我去准备一下,这就去了。”
司马师笑着点点头,看着司马黛拐身离开院子,复又重新走到棋盘旁,居高临下的看刚才所下的棋,叹道:“果然。”
天色渐暗,早有宫里的马车过来接她进宫,司马黛一身正装端坐在马车里,却是在盘算郭太后找她到底为了什么事,她不过见过她几面而已,她和她根本没有什么交点。司马黛双手捏着胸前的挂珠,怎么也想不透。
穿过抄手游廊,司马黛便被宫女带到了永宁宫,不同于永安宫的清冷,如今的永宁宫是太后的殿所,自然金碧辉煌,满殿都是金玉堆砌,锦衣绸缎装饰。司马黛还未走进去,便已经听到了许多欢笑声。
“司马府的四小姐到了。”前方的侍女唱诺了一声,有一瞬间屋子里便静了下来。司马黛一进门,便看到郭太后正中独坐,笑吟吟的看着自己。旁边的甄皇后静静的侍立着。
司马黛盈盈一拜:“臣女司马黛拜见太后,太后万福,拜见皇后,皇后千岁。”
“平常晚宴,用不着行大礼,你且过来这边坐。”郭太后招招手,指指身边的位子。
司马黛不动声色的看了旁边的甄皇后一眼,点点头便坐到了郭太后的旁边,等她坐定抬起头来,才发现坐中的都是一些公主,司马黛仔细看了一眼,发现长乐亭主曹姬居然也在,只见她温婉的端坐一旁,并不言语。她旁边的金乡公主见司马黛看她,对她微微一笑。其余的几位公主虽然见过,只是记不得名号,因此也不再细看。
司马黛团团的看了一圈,心里暗暗吃惊:坐中的都是公主,为何单单找她来?可是脸上依旧平静的微笑,看着宫女给她布上碗筷,司马黛眼睛平视,却感觉到郭太后在看她,她心里嘀咕几声:果然是鸿门宴。
“听闻太后对臣女的贺礼甚喜,所以又备了一份,不知太后可否喜欢。”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郭太后。
郭太后闻言笑着接过,仔细的看了盒子,抚着盒子说道:“光这盒子就玲珑剔透,有心了。”
司马黛微微一笑,见她轻轻打开盒盖,只是但笑不语。
盒子被打开,里面装了一根发簪,白玉为珠,小巧别致。
“这簪子放在盒子里到没什么稀奇,关键在于这簪子插在发间。”司马黛见郭太后露出狐疑之色,解释道。
她的话音刚落,郭太后便让人替她戴上,小小一根簪子,一插上发,忽然慢慢的抽出几根金丝来,渐渐的,金丝盘上发冠,变成了一朵精致的花。
周围传来几声呵气声,顿时赞叹声不绝。郭太后让人捧来镜子,照了许久,也喃喃说不出话来:“好灵巧的心思,好别致的簪子。”
“太后喜欢就好。”司马黛笑道,“这簪子原本就是做来为讨太后您的喜,打算在您寿宴上送上的,可惜这簪子做起来却极难,来不及送上,今日刚好做成,便送了过来,可巧太后喜欢,否则臣女的脸不知道往哪搁才好。”
郭太后闻言笑道:“有你的一片心思便好。”她似乎格外高兴,也赏了司马黛不少东西。
晚宴罢了,太后渐渐露出倦色,却只是挥退众位公主和甄皇后,单单留下司马黛,只言不提赏梅之事。
司马黛看着郭太后眼角微微的细纹,在心里感叹果然岁月不饶人,却听郭太后拉着她的手说道:“钟家那小子果然没有选错人,竟选了你这么标致的一个人物。”
司马黛心里一咯噔,暗叹她怎么知道这事,表面上还是恭敬的微微低头,只听郭太后话锋一转:“听闻钟太傅生前最疼你,他有不少字画在你手里?”
司马黛点点头,笑道:“那是臣女少不更事,只要是描涂在纸上的便喜欢,因此钟伯便拿他的字哄我。”
郭太后似乎叹了一口气,有意无意的说道:“想当年哀家向他讨了许多字画,却怎么也不给,亏我还叫他叔叔呢。”
司马黛闻言心思百转低回,好半天才想起来,原来郭太后跟钟家有旧,郭氏和钟氏是姻亲关系,理清这层关系,司马黛渐渐的了然,知道原来这场宴原来就是家宴,郭太后已经把自己当成钟家人了,那么她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想从她那里讨字?还是有别的什么?
她越想越糊涂,索性听郭太后继续说下去。
郭太后叫人送来茶点,笑道:“钟会那孩子如今远在荆州,怕是不能回来过年,又是冷漠寡言,在哀家看来也就是你能跟他说几句话,别的人他是一概不理。”
“是吗?这臣女倒是没有发现,只是觉得他有自己的事罢了。”司马黛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心道,你们到底什么关系,你如此大费周章到底想说什么?
郭太后却好像兴致极高,拉着她扯东扯西,却是半句不离钟家。司马黛耐着性子听着,就在她差点坐不住的时候,郭太后盯着她说道:“听闻一年前你们把婚事往后推了三年,不知道司马太傅怎么想的,不如哀家赐婚,等钟会回来,你们就把婚事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