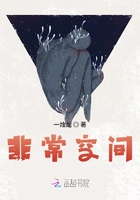我是戚晓月。
韩姝林似笑非笑:“你看看你俩,羞不羞。”
我正在床上躺着,叶天冬把我俩手摁在胸前,我正抬脚作势踢他。想来,姿势的确有点不雅。
叶天冬松了手,我坐起来。
我说:“既是男女独处,有什么羞不羞,你不看就是了。”
我心想,你不总是觉得我和他有什么事,那我就承认了,你能怎样。
韩姝林说:“天冬哥哥。”我闻言起来一身小米粒。
她不看我,继续说:“我奶奶,最近得了肝硬化,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如今出院了。医生说怕还会复发。你有没有好的办法?”
听到肝硬化,我头皮紧了一下,我想起姥姥就是这个病没的,我想起她最后一口气咽下去,握着我的那只手瞬间松开了,想起其他人拉开我给她穿衣服,让我把眼泪憋回去。
想着这些,耳朵又似是堵了东西,半天回不过神来。以至于叶天冬喊我很多声,我才听见声音。不知何时,韩姝林已经走了。
叶天冬喊:“晓月,晓月。”
我问:“天冬,这个病,你当真能治吗?”
他说:“如果已经晚期,我也只能减轻症状,兴许延长些时日。但有些疾病,医学总是无能为力。”
我点头。我说:“天冬,你回吧。”
他说:“我晚上再走。不然你今晚上又难熬了。”
我无力和他争执,随便他好了。
我移步办公室,想起韩姝林说奶奶生病的事,心里产生了同情。
我告诉韩姝林:“何辉把课题带回去整合了,署名他在前,你在后。”
她说:“我做的并不多。”
我说:“但挺关键的。”
她说:“谢谢姐。”
我想着,她今天撞见我俩闹一块,现在竟然不生气,不知为何。
寒假里我也没有回家,我想着总不能把叶天冬带回家去。又得多一番解释。
再说我这种状态回去,也只是引的父母难过。不如不回。
父母未免又是伤心。我说,春天一暖,我就回家看看。
韩姝林也未回家,她是觉得好奇,想知道这里如何过年的。我俩就在校长家里吃饭。李老师和侯老师在家团聚,没有过来。
校长的儿子回来了,但是并未带回媳妇来,校长免不了又是骂他一通,不过比去年好听多了。说他“没主意”,“耙耳朵”。他儿子就一口一个“爸爸好,好爸爸”地哄他,校长老婆也是光笑。韩姝林抬头看着,不知校长啥意思。我则是见惯不惯。我笑说:“姝林,快吃饭。”她又低头吃饭。
吃完饭出来,韩姝林问:“姐,爬耳朵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还能爬耳朵?”
我说:“耙耳朵,耙子的耙,猪八戒的九齿钉耙的耙。就是怕老婆。”
她听了就笑:“如今男人有几个不耙耳朵的。”
我说:“咱们校长就不。”
她说:“叶天冬一看就耙耳朵。”
我说:“一看就不会。”
她问:“为啥?”
我说:“因为他没老婆。”
哈哈。我俩人笑做一团,似乎只是谈论着一个共同的好友,似是从未有过隔阂。
我记得在大学宿舍时,和小米也是如此夜谈,谈到徐卿文,谈到小胖,也是一番无伤大雅的调侃。
想到徐卿文,我打开手机,头像依然灰灰的,我感觉似是沉了海底,身体就冰冷,到了宿舍,坐在床头上,动也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