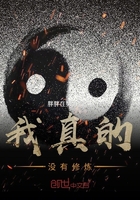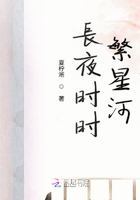我是戚晓月。
给小孩拍了片子,诊断的确是锁骨折了,安排好住院,第二天做手术。我通知了他家长。又是个父母不在身边的,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出门不方便,光着急。我只好说,你们在家等着,我接你们来。
韩姝林在那里看着孩子,我来来回回忙活这些事,待安顿下来,天色已经黑了。
爷爷奶奶见了孙儿就哭:“康康你哪里伤了?”
“怎么摔了?”
“可怜的孙儿,老疼哩吧?”
“你说你娘多狠心,你娘要不走,康康就没事了。”
孩子这会已经止疼了,听见说他娘,又按住伤处连哭带嚎起来。真是俩添事精。
一会孩子的婶婶来了,婶婶住县城里,来的快些,我心里略安心一些,毕竟有些决定,需要有个管事的家长来做。老师越俎代庖,有时只会好心做了驴肝肺。
我和婶婶商量:“俩老人年龄大了,我送他们回去,别连带得身体不好了。”
婶婶也是这个意思。起初二位老人不肯,后来也是觉得累,我就送他们回去了。把韩姝林也一路送回了。
我想着,把两个添乱多事的,和一个百无一用的都送回去。
送完他们,天已经黑透了。我去宿舍收拾一些东西,去往医院。
路上黑漆漆,只有车灯照的这一点光。一个人也没有。我心里乱糟糟的,手脚都疼痒难忍,熬了这几日,头也晕晕胀胀。
不知为何,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个灰灰的Q头像,心里更加不安。山路上一个弯没反应过来,直直的就撞在了山体上。
剧烈震动,我的头和手都结结实实地撞到车上,疼痛起来。我想着,幸好车速不快,不然就再也见不到小米和爸爸妈妈了。脑海里又闪出那个灰灰的头像来。
车头塌进去,我也无暇顾及了。觉得额头上湿热,一摸,一手血,在这荒无人烟的路上,红的瘆人。接着头皮发紧,似是戴了紧箍咒一样,又是头疼欲裂了。
叶天冬回来时,小孩已经手术出院,回家休养去了。我正在宿舍里心乱如麻,头上贴了纱布,左手上扭了筋,动也不敢动。又是日夜折磨,此时定是狼狈不堪。
他就是这时进来的。
数日不见,他似是瘦了不少。想必离家远走的人,同样是千辛万苦。
我眼里充了泪,说:“天冬,你回来了?”
他又生气又心疼,说:“我就离开这半月,你把自己伤成这样。”
我说:“都是小伤,不疼的。”
他走过来,仔细看看我,眉头紧锁,说:“晓月,拿手来。”
我想起这几日难熬的夜晚,症状又是一齐袭来,今日他要给我诊脉,定是看出什么来了。我躲过去,说:“外伤,看得见,摸得着,诊的什么脉。”
他一脸阴郁地说:“晓月,你旧疾复发了,是吗?”
我想着这几日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哪一桩也不值得向他描述,但却是引起了蝴蝶效应。尤其是那一手瘆人的血红,还有那个灰灰的头像,这几日连续出现在我脑海里,让我欲罢不能。
我闻言快要落泪,但忍住了。我想着一个成人,因这些小事掉泪,实在是没出息。
他说:“晓月,今后我定不会让步与你。”
我说一声:“天冬。不是,我......”
却不知该说什么了。
今日开始,他又要给我治病。只是这次行针的部位非常多,除了胳膊,腿,头顶,连耳朵,额头,后背,脖子,太阳穴上都要用针。待一套程序下来,起完针,他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我看他专注了这么长时间,想哄他放松一点,说:“天冬,怕不是要把我扎成蜂窝了。”
他依然没有舒缓表情,说:“晓月,你信我吗?”
我笑说:“又说傻话,我不信你,还能信谁?”
他表情略缓和,什么都没说。但我想着,这次用针,怕他真的是走了险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