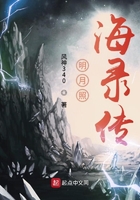手无寸铁的手迎上了银索,痛楚袭来,燕绥脸上拧成一团,表情狰狞。
皮开肉绽,被抽得鲜血淋漓,燕绥忍下疼痛,趁这一刻,将银索拉住。
银索落在燕绥手上,别瘟目光一惊,想将法器抽回。
纹丝未动,就像缠绕上了一尊磐石一样!别瘟不免加重了力气。
他加重了力气,燕绥同样也施了力气,一根银索在两人手中拉扯。
两人用得力气极大,肉眼可见绳索在颤抖着。
一场拉锯下来,燕绥抽不走银索,别瘟亦是收不回。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这样了!燕绥脚下运力,用尽浑身力气将银索甩了回去。
别瘟没想到燕绥敢用手去接他的法器,更没想到银索会被甩回来。
措手不及,别瘟被打中胸口,身子拍出了一丈远,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倒地不起。
孟阏脸上的伤痕触目惊心,飞霜看得头皮发麻:“君,君上,您没事吧?”
“放肆!”,空雨手中滑出一把长剑,直指别瘟。
“君上?”,别瘟浑身一个激灵,勉强自己站稳,这个突然杀出来的孟飞霜,在喊孟阏君上。
排骨被震撼到了,内心不能平静,他傻乎乎地问:“君上?哪位君上?”
巫族君上有几十位,孟阏是哪个啊?
被人拆了身份,孟阏也不遮掩了,地藏攀着她纤弱的身子爬出来。
犹如一条银色长蛇,在她肩颈处盘旋,看得人胆战心惊。
忽然钻出这么一个东西,笑颜吓得直往后缩。
地藏是一条银色长鞭,秉性霸道。
时隔多年,终于被放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地藏雀跃无比。
柔韧的鞭子垂落到地面,地面瞬间凝出一块寒冰。
地藏兴奋不已,清脆响亮的鞭声响起,寒冰瞬间被击碎,留下了一条沟壑。
沟壑不算很深,别瘟却胆战心惊,就这么一下,就留下了一道?
孟阏半边脸麻得厉害,修长的手指轻抚脸颊,指尖满是黏稠湿滑。
多少年了,还没人敢这么伤她,眼中风暴积累,脸沉如水。
燕绥得了空,他扶住孟阏的肩膀,急道:“我带你去找巫医。”,这么深一道伤口,往后怕是要留疤的。
孟阏睨了他一眼,脸上的伤口发生异变······
伤口上迅速开始生长出一层冰渣,满满地覆在她伤口之上。
接着伤口炸裂,冰花争先恐后地从里头钻出来。
燕绥颤着手指去触碰,刚触上的那一刻,冰花再次炸裂。
冰渣子接二连三从脸上掉落,伤口不复存在,只留下一道粉嫩的痕迹。
皮肤是新长出来的,泛着微粉,但总归看上去不那么吓人了。
地藏攀在她的肩上,冲着别瘟的方向扭动着。
看在别瘟眼中就吓人多了,他退缩不前,浑身上下冰凉无比。
孟阏轻扯唇角,左手轻抚地藏,像是在安抚它一样,眼里却饱含讥讽,总算知道怕了,可惜已经晚了。
“别瘟是吧?”,她冷笑着开口确认。
“怎么,怎么了。”,别瘟吞吞吐吐的应道,她的眼神太吓人了,看得他害怕。
地藏和她一体,自然也能感应到她此刻的心境,冷不丁蹿了出去,朝别瘟游去。
“回来。”,孟阏小指勾住地藏,地藏闹起了小情绪,扭动两下,复又安静下来,孟阏抚住它,冷冷出声:“你放心去吧,你陨落的消息会传回望舒的。”,不会让他死得不明不白的,她敢做便敢当。
燕绥陡然心惊,在场除了别瘟,还有谁是望舒家的,阿阏动了杀心了。
“你,你不能这么对我。”,恐惧感油然而生,别瘟不停后退。
他是望舒家的后嗣,巫族后嗣不丰,望舒一定会保护住他的。
在这里不安全,只要他逃回望舒,谁能奈他何?这个想法在别瘟心中疯狂生长。
脚往后退缩,他在等时机逃走,就是现在!别瘟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往相反方向逃走。
“想跑?”,空雨冷哼一声,手中长剑被她投掷出去。
“啊。”,别瘟及时刹住脚步,剑身贴着他的脚尖没入青石板中,入木三分,发出一声铮鸣。
只差一点,他的脚趾就要被齐根斩断,别瘟猩红的双眼看向孟阏,不行,他不能坐以待毙。
浑浊的呼吸声,口中白气飘出老远,别瘟狠狠抹了一把脸,又换了一个方向跑去。
“唉?他又要跑了?”,笑颜探头喊道。
叙阳恨不得捂住她的嘴巴,将她拉到一边,低声说:“少说话,不关你的事。”
“让我来。”,飞霜甩着胳膊活动肩膀,脖子关节处发出两声清脆的响声。
“滚。”,孟阏失了耐心,猫捉老鼠的游戏不好玩,她也没有这个耐心。
出拳的姿势猛地顿住,飞霜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地面生长出一根根妖冶的冰藤,上面长满了冰刺。
“什么东西啊?”,排骨哇了一声,直接跳到了叙阳身边。
冰藤得了操控,虽在地面疯狂生长,却知道避开人。
盘旋,交缠,生长,他们都只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别瘟。
别瘟被逼抱头逃窜,躲过一根根生长的冰藤。
一根藤尖挑起他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啊,放开我。”,别瘟悬空,腿不停地踢着。
冰藤继续生长着,藤枝朝着河面生长,生长愈来愈密。
别瘟没了法器,只得用手狠狠去拍打,挥开藤枝。
可惜得是,藤枝坚韧,冰刺锋利,反倒落了一手的伤。
“我爹爹不会放过你的,望舒家不会饶了你的!”,别瘟慌不择言起来。
望舒家要是知道他跟别欢狼狈为奸,怕是避之不及吧,她留他留得够久了,唇角掀起讽刺的笑容,孟阏道:“那本座便等着望舒家的问罪了。”
下一秒,冰藤倒向河面,别瘟悬在了河中央。
脚下就是令人胆寒的霜雪河,别瘟丢了那么多人下去,却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掉下去。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自己造的孽,终有一天需还的。
靴子踢踏着掉入河中,噗通一声,瞬间化为齑粉。
惊恐的叫声响起,刺耳至极,耳里满是别瘟的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