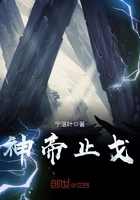先是点了两菜一汤——要是徐为民是迫不得已,不得不干坏事才维持的了生活,那程自怡会让老板再给他上一碗饭,打一碗白开水。要是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或者又是单纯的“偷是肯定要偷的啦,只有这样才维持的了生活。”那程自怡会毫不犹豫的让他滚蛋。
而且,从始至终,程自怡都是看在他还心存善念的份上才愿意和他进一步的接触,要是下次碰着了,那该送警察局就送警察局,不含糊。
这两人见了这么久,得开一个头吧,至少,得知道彼此的名字吧?
“你……叫什么名字?”
此时占有主动权的是程自怡。
“我?我叫徐为民,徐向前的徐,为国为民的为民。”
得,白瞎了这么个正能量满满的名字。
一人已经报上名号,接下来该轮到程自怡了。
“我叫程志强,程咬金的陈,志向远大的志,强大的强。”
不过比起老老实实说出真名的徐为民,程自怡是随便的捏造了一个名字。
以后两人不大有机会再见面,现在问个名字不过也是出于客套,甚至程自怡也不是没怀疑过,这“徐为民”也是个才想出来的新名字。
“你,有手有脚的,为什么不找个自食其力的营生,来干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啊?”
“我……我也不想。”
像是问到了心坎上,徐为民那张脸上,显现出了可以用双眼直接判断出来的纠结与痛苦。
“可是你确实干了!你偷了我的手机,你应该也偷过其他人的东西,你总不能嘴上说着不想,手却控制不住吧?”
此时的程自怡开始试图让自己的语言充满点压迫感,但是又不至于太过于直白,直白到把别人吓跑了。
在先充满压迫感的说完一句话后,程自怡看徐为民也没有继续解释,只见徐为民张口,口没张开,又闭上了。
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先一棒子打过去把他唬住,免得这人认为自己好欺负,蹬鼻子上脸,然后,再好言好语的慢慢说。
“朋友,你吃我这顿饭,能给我一个小小的答复吧?要是真有什么难言之隐,说出来,那我也理解你,这年轻时谁没干过点不那么成熟的事?”
“我觉得吧,如果我能够劝一个浪子回头,那几百上千元没了也就没了,我终归挣得回来,可我也得知道你这浪子还愿不愿意回头啊?这人都浪过太平洋了,我还拉个啥啊?”
“……”
也算是在程自怡的软磨硬泡之下,徐为民才决定说出了自己干这一行的原委。
那说的时间有点长,而且可能是触及了一些不大好的回忆,中途说的也是断断续续。
好在程自怡的记性不差,语言的整理归纳水平也不低,在静静的听完徐为民的话后,他也是知道了个七七八八,甚至能够用自己的脑补与推理将事情给还原个九成左右。
总结一下,就是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道的那样——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显然,徐为民的生活就是印证的那后半句话。
父亲是一个赌鬼,差不多的赌光了了所有能赌的东西,如果不是怕死,兴许还会把自己的命赌上,而他的母亲,也几乎顺理成章的离他父亲而去,改嫁他人。虽然在母亲离去的前几年,她依然会回到原来的家庭看看她的两个孩子,但是自从新的生命诞生之后,这种关怀变的越来越少。
说起这段事情的时候,徐为民似乎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坚强来让眼泪不至于划过眼角,声音也带着颤抖。
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父亲,能给他和他妹妹些什么呢?除了债务外,还不如什么都不给。常年在外躲藏让他的父亲像是一个幽灵一般,虽然就活在身边,但是却几乎不会出现。
原本抚育孩子成人的工作交到了徐为民奶奶的身上。
好吧,总算是比没父没母的孤儿们好上一点,至少有个长辈照看,但是一个农村老人,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种了一辈子地,将所有青春奉献给土地的人,身上又能有几个钱呢?
念完初中后,九年义务教育的义务也就完成了,徐为民当时倒还想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知识,只是经济条件的不允许让他不得不早早的出来打工。
他能打什么工啊?进场都嫌年纪小,所以他是有什么给他干,他就干什么。
也许日子辛苦一点,但是还算是过得去,而他也打算攒够钱,让自己的妹妹完成自己没有完成的心愿,上高中,读大学。
可是有些时候,品性恶劣者的亲人仿佛是带上了原罪一般。
他父亲赌博的事情,像是瘟疫一样在他妹妹的学校里传开,不说传的有多远,至少在整个班级的范围内,这件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其实说到这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他只知道校园暴力这个他曾经没有遇到,以后也不太可能遇到的事情,不知道在何时,降临在了他妹妹的头上。
如果不是他去给妹妹送新衣服和不多的生活费,他甚至不见得能够看到自己的妹妹被人欺负。
一帮小屁孩能干什么呢?
抓头发、打脸、踹人,似乎她们想把自己过剩的精力,用暴力甚至更甚于暴力的方法发泄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这自己妹妹被欺负了,那当哥哥的总不能在一旁看着吧?找老师?找教导主任?找校长?
不搞这些有的没的。
听徐为民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的眼睛又恢复了神采,语气也充斥着力量。
他手舞足蹈的说了自己是如何将那些施暴者打了一顿。
徐为民他人高马大啊,又干了不少时间的力气活,那打初中、高中的学生,和打幼儿园、小学的小朋友一样轻松方便。
要是真如他所言,他在人群中就如吕布再世,关圣亲临,拳打、脚踢,甚至抱着一个对自己妹妹下手下的最重的人,就是一个过肩摔。
他相信这样——用自己的暴力,就一定可以解决他人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