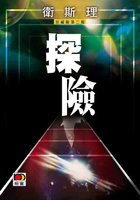罗知县回县的消息几乎是立时便传进了田廷生等人的耳朵。他们做好了接受召见训斥的准备,可一夜过去,纹丝儿动静没有。派人打听,先是说罗知县因为受了风寒,躺在床上动不得身了;随之说罗知县一整天只是一个人低着脑袋喝闷酒儿,喝过闷酒儿就胡写乱画,写的什么画的什么连王凤也摸不着边儿;接着又说罗知县给朝廷上了奏章,请求调回开封或者离开封近一点的地方去。田廷生等人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那些苦苦盼着罗知县归来的百姓们,心里却凉得结了冰。于是一切照旧,一切都像是罗知县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承宣布政使司时一样,田廷生和豪门大户们又开始了催逼搜掠;只是为了遮人耳目、减少麻烦,催逼搜掠由白天改到了晚间,夜深人静的时候。
那天半夜时分,田廷生再次外出时,半路上竟然与只穿着布衣长衫的罗知县撞了一个迎面。
“哎哟!这不是田大人吗?”田廷生有心躲避,罗知县先自打过招呼。
“哎呀,是罗知县哪!……这……这个……”
“天阴月暗,田大人这是到哪儿去呀?”与两月前相比,面前的这个罗知县,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啊啊……哎呀,这几天不知怎么搞的总是睡不好觉。这不,随便走走,就走到这儿来了。……罗知县这是……”
“巧啦,跟田大人犯的是一个毛病。”指指街口:“夜风太凉,到小店里稍坐片刻如何?”
“多谢罗知县好意。只是小人身上确乎有些不适……”
“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杯小酒下肚,保管田大人身轻体安。请!”
罗知县头前引路,田廷生心里纵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得随后而行。
酒店名曰酒店,实则不过是一户人家倒出的一间小屋,里面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木凳,外加一个老翁。酒旗、灯笼是十二时辰挂着的,关门闭门并没有个定准时间,无非是有人来则开无人来则关。罗知县、田廷生进门,酒家老翁当即把一瓶老酒几碟小菜摆到二人面前。
二人喝起,酒家老翁站在一旁,不时地添着酒加着菜儿。
“老叔今年贵庚多少啊?”罗知县随口同老翁拉起呱来。
老翁伸了伸指头:“七十有四。”
“好岁数!过了孔老夫子的大限啦!”
“嘿嘿。老也不死,还不是光受罪?”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人?耗子倒有一群。……一个孙子,早两天也饿死咯。”
“哦?春上不是借了粮米?”
“不提那也好!秋粮原本就少,一个借一还五,嘿嘿!……”
“借一还五?这是哪个这么歹毒?”
“你两个是外乡来的?”
“那是,那是。”
“这就怪不得了不是?田廷生!那个人面兽!春天借的1斗,现如今硬逼着还5斗!那些财主们也都跟着他胡来!用不了几天,这块地面就算是毁咯!……”
田廷生听酒家说出这种话,起身要走。罗知县随手拉住,无事一般地招应着:喝酒喝酒。田廷生满肚子是火也无法发作,只好勉强又举起了杯子。
罗知县给酒家倒过一盅老酒,酒家谢也没谢就倒进嘴里。
“不会吧?听说田大人知书达理,是个好人哪!”
“好人?好人堆里拣出来的!还不上粮就要占地、占房、占人家的大闺女小媳妇!听说夜里还出来逼命哪!”
“嗯!老叔,这就不足信了。田大人真要催粮,白天出来何等威风,怎么会夜里……”
“你哪里知道!他是害怕罗青天!……县太爷,好人哪!可就是他一个人,咋整得了田廷生那一窝子?听说就是他们想了法儿,把罗青天给骗到那个承宣……使么个司去的。要不,还不定有这一出哪!”
酒家愤愤地叹着气换酒去了,田廷生起身,两人来到街上。
田廷生诚惶诚恐,连连打着躬儿:“方才酒翁胡言,还请大人明察。”
罗知县无事一样:“本县又不是3岁童儿,哪有轻信几句闲话的道理?田大人只管放心就是。”
“多谢知县大人。”
“你我再走走如何?”
“小人实在不胜疲累,还望大人……”
“也好,我也该回去了。就请先行一步。”
田廷生如得大赦,深施一礼匆匆离去。罗知县朝那背影一笑,嘴里哼着昆曲儿又回到了屋里。
酒家老翁换酒回来不见了人影,正觉纳闷儿,见罗知县进来,道:“看看,看看,那位客官哪?”
罗知县坐下:“老叔,有狗肉没有哇?”
“狗肉?这么说你也是馋狗肉的?”
“狗肉乃上好之物,难道只准老叔一人馋不成?”
“好好好好。”酒家老翁离去,顷刻端来一碟,道:“话可说清,这可是真真实实的狗肉,不是那种假冒的死孩子肉。我连味儿也没舍得闻一闻,为的可是个好价钱。”
“好说好说,老叔只管放心就是。”罗知县应着,倒上一杯酒,示意让老翁坐下。
老翁不肯:“这是哪儿话来?”
“就算是我敬老叔一杯行不?”
酒家见罗知县确非虚情,这才坐下端起了杯子。
“老叔,晚生为你算上一卦可好?”喝着,罗知县说。
“算卦?我这半死的人儿还算的么个卦来!”
罗知县只管认真地打量着,道:“不好!老叔,据晚生看来你有一场大灾。”
“大灾?还小灾呢!大不了哪天小店关门扎了脖子去。”
“不!血火之灾!”
“……血火……多时?”
“不出一个时辰。”
酒家一惊,随即笑了起来:“客官,不是喝多了吧?”
“不不,老叔,你得罪了大富之家,可对?”
“田廷生?”酒家更乐了:“嘿嘿!老汉恨是恨他,可连他的鬼影子也从未见过。”
“不不不!你可是当面骂人家人面兽、好人堆里拣出来的。”
“你是说方才?这位客官可真会戏弄老汉。哈哈哈……”酒家伸出一手,半是认真半是戏谑地:“客官再看,这血火之灾可是有救?”
罗知县果真拿过酒家的手,端量片刻道:“嗯,有救,有救!老叔虽有大灾,却自有救星庇佑。”
“唔?救星又在哪儿?”
“老叔看晚生如何?”
“呀呀呀!”酒家失声而笑,“这位客官!这位客官!……”
“老叔,晚生果真救你一灾,你请晚生再吃一碟狗肉可好?”
“你想是被狗肉馋得疯啦!哈……”酒家把眼泪也笑出来了。
也就在笑出的眼泪要擦还没来得及擦时,门外一阵脚步夹着一阵吆喝,接着门被訇地一声踢开了,几个家丁模样的人汹汹地闯了进来。
罗知县一笑,埋头只顾喝酒。
酒家慌忙迎上前去:“各位客官,各位客官……”
为首的家丁一把揪住酒家的衣襟,道:“你就是开酒店的老东西?”
酒家看出事情不妙,连连后退着:“……么……么……么事儿?……”
“你好大的胆!带走!”
罗知县这才站起,连连地摆着手:“放开放开!酒家是我,你们有事跟我说好啦!”
“你?找的就是你!”为首的家丁一个眼色,几名家丁立时揪的揪拥的拥,把罗知县带出门去。酒家瞠目而视,半晌定下神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血火之灾……救星……神,真神!……”
田廷生和一班豪门富户今晚原是准备逞逞威风的。不少欠粮的人至今软顶硬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希望暗暗寄托在罗知县回来上。如今罗知县回来了,他们有意要让那些报有幻想的人家断了那个念头。众人约好集中地点、时间,没想田廷生偏偏让罗知县给截住了,又被一个开酒馆的老东西咒了个底儿朝天。与罗知县分手,与众人会合后田廷生把情形一说,众人一致的意见是把那个老家伙弄来当个靶子,给大家开开心儿,也给那伙不老实的百姓们过过眼神儿。
一路上家丁们少不了要让“老东西”吃点苦头,等到被带到众人面前时,罗知县的那身布衣长衫已被撕得七零八落,他又故意低垂着脑袋,直到田廷生等人发了好一阵狂言和得意,喝令要让“老东西”看看马王爷几只眼时,罗知县才缓缓地抬起了脑袋。而这一抬,把田廷生等人惊了个魂飞魄散、呆若木鸡;早已奉命等候的一班军士衙役,随之也包围了整个院落。
那伙被抓来的百姓认出是罗知县,一齐跪到地上:“罗大人救命啊!……”
那伙本想逞逞威风的豪门大户见此情形,自知罪不容恕,一阵扑扑通通也跪到了地上:
“罗知县饶命啊!……”
田廷生望一眼面前那副挂着血迹、冷如生铁的面孔,和显然是早已布下的阵势,身上不由地打着哆嗦、冒着冷汗,腿一软,也跪了下来。
罗知县却哈哈大笑着,上前挽起了他的胳膊。
“田大人这又何必!……百姓无辜,放掉可好?”
“……但凭大人……”
“灾荒未除,性命不保,所借粮米不还可好?”
“但凭大人……”
罗知县指指案上的一堆借券,威逼地:“借券作废,烧掉可好?”
田廷生禁不住一阵震栗:那是原先借出的几百担粮米,少说也值几千两银子,如今该是上千担、上万两的数儿了;那是他的心血、本钱,哪怕天王老子来也是无论如何……
然而除了点头,只有点头:“……但……但凭大人……”
罗知县这才目视跪在地上的一班豪门大户,说:
“你等粮米借一还一可好?”
豪门大户们见田廷生尚且如此,哪里还敢有半句多言。
“……但凭大人……”
“凡已多收的粮米,两天以内全部退还可好?”
“……但凭大人……”
罗知县这才示意让跪在地上的百姓们起来,说:“各位乡绅体谅你们的难处,所借粮米借一还一、不加利息,凡已多收的一律退还。田大人则自愿烧毁借券,把已经收去的粮米如数退还,作为赈济百姓造福乡邻,你们可是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好!请转告各位乡亲,两天以内哪位粮米未退只管到县衙找我,本县言出必遂,如有半分错漏,甘愿死于乱棍之下!”
“多谢青天大老爷!……”
“也要谢过田大人和各位乡绅。”
“……也要谢……谢过……”
“点火!烧券!”
一声令下,院中燃起一团火苗。火苗在百姓们苍苦愁凄的面庞上,映出了一片亮色。
12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与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问询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月妈妈,本姓张,骑着驴,挎着筐,专给小孩看口疮!
……老猫老猫,上树偷桃,听见狗咬往家跑,到家拾了个破棉袄。你怎么不穿?怕蚤子咬。我给你抓抓吧?哪可倒好!……
背过一段唐诗,背过一段宋词,又唱起一段野曲;野曲唱过该再背唐诗宋词了吧,偏偏又唱起了野曲。唐诗不好背吗?宋词不好听吗?不是,可就是背起来不如唱野曲自在。母亲问聪儿这样回答,父亲问聪儿还是这样回答。怎么想的就怎么回答。从懂事起父亲就是这样教导的,从懂事起聪儿也是这样做的。开始父亲每每还要训导几句,说唐诗宋词那可是千古华章、万世瑰宝,堂堂罗宰相的后人、小小罗知县的千金,背不下几十上百首来,那可是丢人显眼得很呢。说过几次,说得聪儿两眼红红、眼泪巴巴要往下掉,罗知县心里就有些软了;自己把那民歌野曲细细品一品,也觉得确乎朗朗上口有滋有味,也就不说了。不说不等于放任,父女俩立下个“君子协定”:怎么背、什么时间背一概不管,一年以内,唐诗宋词达到随口而出的不能少于100首。因为有了这,聪儿才得了自由,那稚气未消、娇柔鲜丽得让人心醉的面庞上,才不时漾起少女特有的笑靥和娇情。
扮过两年吃苦得罪人的黑脸包公,灾荒一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盛阳境内四野靖平、秩序井然,罗知县的日子也随之变得轻松了许多。思妻思女之情油然而生,聪儿和她的母亲孙氏,也就从千里之外的开封城,落脚到这偏远的祖先的故土上了。
罗知县有一儿三女,聪儿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得欢心的一个。她的到来,在罗知县的心灵和生活中,播下了说不尽的甜蜜悠扬。
从开封到盛阳,从城市到乡村,面前整个儿换了一个天地,聪儿不仅没有一般少女的那种生疏、隔膜,反而如鱼得水如鸟投林,快活、欢跃得跟只蜜蜂似的,嗡嗡嗡,整天日里笑个不止、唱个不休。这自然是出自于聪儿的天性,但也要归功于桑叶和杏子、桃子、李子、芹儿那几个小姐妹。那些好唱好听的野曲歌谣,不用说,是从她们和她们的奶奶妈妈那儿学来的。好多好多的新鲜事儿,好多好多的好吃的、好玩的,也都是从她们和她们的奶奶妈妈那儿听来、得来的。头上的那顶卧兔帽,身上的那块披云肩,是桃子、李子几个帮助选的。连那幅时兴的、从额顶横过的遮眉勒上的圆形图案和花绣,也是照着杏子的那幅样子,由桑叶手把手儿教出来的。原先总听父亲母亲讲老白果树和金羊庙,总不理解老远老远的那么一棵树、一座庙,有什么值得讲的;到树下和庙里一看——老白果树已经重新站立起来,金羊庙也已经重新建过了的——再听桑叶她们讲起那么多故事,尤其是遭到大火和龙卷风的故事,聪儿几次都是泪眼汪汪,那个崇拜敬仰的劲儿,比起父亲母亲来似乎也还要胜出几倍。花生果儿,聪儿原先一直以为是从树上长的,直到两眼圆圆,看着桑叶从地里刨出那丛根根蔓蔓,眼看着捌开壳儿露出红红饱饱的果实儿,才伸长了舌头。还有剪纸剪窗花儿。还有吃新麦饽饽儿。还有晒书虫子儿。还有“月明光光,小儿烧香;月明圆圆,小儿玩玩”。还有七月七吃巧饭、照巧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