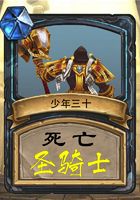一
中国的作家是很多的。“五四”时期曾经影响过我、做过我的老师的老一辈作家还大有人在,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同时代作家也很多,他们有很多人念的书比我多,对于外国文学的修养也比我好。比我年轻的作家也还有不少,他们生活的基础比我厚。比如我前几天写了一篇读《东方》的文章,谈到了作者魏巍同志,他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小鬼。打倒“四人帮”以后,一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很少框框的新生力量,也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的文艺队伍是很大的,也是很有希望的。这支队伍在新长征中,正在为繁荣党的文艺事业而努力地工作着。我自己只不过是这个文艺百花园中一棵经过风雨和严寒烈日、经过波折而至今没有枯朽的小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点。自然,一个作家不管他本身多么微小,在整个时代所占的地位多么微不足道,总不能不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不或是正面的,或是侧面的,或是反面的反映着这个时代。
我出生在中国社会最黑暗、最腐败的清朝末年。我最早感受到的欢乐和痛苦是辛亥革命。我永远不会忘记小时候家乡考棚的枪声。那些烈士的鲜血好像苦水一样浸透了我周围大人们的心。在这样的时候,我小小的心灵也受伤了,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和难受。然而,也就在这同时,我站在大人们的后面,看到了游行队伍的灯笼火把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在我面前滚滚地冲过去。我跟着队伍蹦蹦跳跳,高兴得大叫大闹。我究竟能懂什么呢?我那时还很小,但是那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的气氛感染着我。就在这样的气氛底下,背负着旧时代的封建重压和痛苦,满怀着对于生活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我一天天长大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那时我正在上中学。可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的呼声和潮流,猛烈地激荡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我们如饥似渴地去找北京和上海出版的各种报章杂志来读,想从里面找到中国应该走的道路,找到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的道路。我们也向西方和东洋的日本找过。后来,因为十月革命,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有了真正有力量的领导,出现新的局面。一些真正想革命的人纷纷投身于革命浪潮中,文艺界的许多作家也被卷了进来。在那个时期,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我也张开了年轻的翅膀,飞到了南方,飞到了北方,想找一条出路,放声歌唱东方升起的太阳。诚然,这中间,我也曾经消沉过,感到世界如同在一个灰色的深渊里找不到出路。但我碰呀,挣扎呀,磨炼呀,大革命失败后,终于投到了党的怀抱里。这时已经是三十年代初了,我已经长成了。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以一个作家心灵的感受、痛苦和要求,经过十年的思考和亲身的经验而投到党的怀抱的。我是一个作家,但我不满足做一个作家,我决心投到革命大家庭里面来,要在整个革命机器里做一颗螺丝钉,在雄壮的革命队伍中当一名小小的号兵。至于我这把号的音量大小,音色美不美,吹得好不好,不是我个人所计较的,也不是我所能计较的。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充满矛盾的,道路总是会有曲折的。比如在长江上行船,从四川到上海,其间要碰到多少礁石!五十多年来,我们的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历了艰苦的斗争。我自己的一生也是坎坷崎岖的。从二十年代一直碰到七十年代,碰过一些壁。不过我这棵小树并没有枯掉,仍然在风雨中站着。当然,我是要吸取教训的,我要重新清理、总结经验,作为自己在新长征中的前车之鉴。我曾经想,既然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剩下的惟有把自己尚存的精力献给党和国家,为着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阔步前进,努力不倦,如此而已。
二
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到北大荒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在那里,我参加劳动,也参加工作。
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差别不那么大。因此,作家到农村去,不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我既然愿意当一个小小的号兵,就必须跟着革命队伍向前走,到工农兵里面去,不然的话,就不能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忧戚结合在一起,所表现的就只能是堆积在自己身上的原来那个阶级的一些苦闷。所以,共产党的作家是非到工农兵中去不可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底下当过兵;下农村搞土改时,我当过农民。那时的生活,比五七年艰苦、困难得多了,条件也更不好。然而,我经受了锻炼。因此,一九五七年我到农场去生活,到底并不是太困难的。当然,这次下去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的身份变了。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浑身酸疼。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深入生活。五七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像是看猴子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
曾听到许多人说,我这些年是被充军到北大荒去劳改、受苦。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并不是接受处分而去北大荒的。那时有人曾劝我不要下去,说:“你可以住在北京,坐在家里写文章嘛。”我心里想,我是一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不能孤独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作,那样我精神上会感到苦闷。我必须重新到群众里面去。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吗?我就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个更加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吧。也有人劝我下去的时候改个名字,免得不方便。我说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什么了不起。就这样,我带着一点主观英雄主义,把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帽子放在一边下去了。
在底下工作的时候,我主动打破界限,对党支部书记说:“我是个老共产党员,过去做过不少工作,也领导过人;现在不是了,是你领导我,监督我改造。你比我年轻,比我经验少,但没关系,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尊重你。不过,我对支部工作,对队上的事还是要提意见的。我虽然是右派,但我心里还是把自己看做是党员。我对党是不见外的。”我就用这种方式和基层的支部、群众相处。我养鸡,还是个小有名气的养鸡能手。我还搞扫盲工作。有的同志会说,一个作家不写作,却去扫盲?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参加党的时候我不是讲过,我不满足做一个作家,而愿意做一个共产党员,做一颗螺丝钉,党需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吗?如今需要我扫盲,我自然就去扫盲。我想,我是个作家,又是个老党员,如果扫盲工作不如别人那是不行的。我全力以赴,结果也确实是我这个队获得了全农场的扫盲优秀锦标。我还锄草、养猪……因为长期参加劳动,在劳动上是有很多体会的。但是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我交了许多朋友,生活给了我很多人物,很多题材,我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可惜我现在已经七十五岁了,假使是六十五岁就好了。不过,我心里想,虽然是七十五岁,还是把它当作六十五岁干下去吧!
在北大荒,我感到在下面的人和上面的某些人不大一样,他们没包袱,不怕失去什么;他们不管你是不是右派,只看你对他们心思,便认定你是好人,正派人。否则,哪怕你官当得很大,或者是刚刚管他的顶头队长,也瞧不起你。我那个支部书记是个年轻人,工作热情,方法简单,一有事老要开会批评人。有一次,他到猪舍巡视,饲养员见他朝大门进来,便从窗户跳出去跑了,碰到我笑开了,说:“他来我走。”饲养员心里不喜欢他呀!结果,每当支部书记要做一个人的思想工作时,总是找我说:“老丁,你去跟他谈谈吧。”我当然想尽办法把这些工作搞好。所以,尽管我在队里是个大右派,可是支部书记倒好像把我当成他的小助手,有困难愿意找我。在那三年的困难时期,农场口粮标准都降低了,文化学习也暂时停止了。但我那个队还坚持照样学习。学什么?听我讲故事。那时,如果你说要学习,人们不一定来;我说讲故事,人们就愿意来了,于是我就开讲了。当然,这也是一种教育。而我也因此有了非常多的朋友。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情况就变了。革命造反派出来了,他们不管你几年的工作好不好,只知道你是右派,就要造你的反,就该打倒。他们说:“我们农场的场长、书记级别都没你高,你是最大的走资派。”所以非打倒不可。其实,我老早就被打倒了,然而他们还是要打,这就没办法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知识分子都是“在劫难逃”,大概是这样吧,只要你是个知识分子,起码也是个“臭老九”,难免要受点冲击。我因为什么都尝过了,见过世面,经过风雨,所以也就不在乎了。不过,有些事是很有趣的,以至于常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次开会斗我,叫我弯腰低头九十度,实在难受。但我不能说,否则头就得更低一些。这时,一个红卫兵过来对我凶道:“丁玲,站好,把头抬起来,让大家看看!”她是骂我,还是训我?都不是,她是让我休息休息,把腰伸直!我并不认识她,然而就是遇着这样的好人。黑夜抄家时,也有这样的红卫兵,在朦胧的灯光下,让我站在他的身后,这样,在那混乱之中,我就等于藏了起来,可以少挨几拳头。这样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底下碰到了很多。
一天,我在地里锄草,几个红卫兵又过来了,说:“丁玲,前天叫你背的语录,你现在背背!”我本来是背得下来的,但他们这么一喧闹,皮带又往我脑袋上一晃,而我毕竟不年轻了,心就慌了,就结结巴巴了。于是,他们一面训斥,一面便拳打脚踢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居然走来一个老头,是他们同一派的,好像比他们还凶。他把我拉过来,骂道:“你这个剥削阶级,你就是剥削我们的!为什么不好好干活?”骂了以后,把锄头给我,说:“去,锄草去!”他是真的骂我吗?不,他是保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不必背语录,可以不再挨打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农场里住两间很好的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我赶出来了,给了我一间最坏的小茅屋,七平方米。我隔壁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的,臂上戴着红袖章。我想,说不定哪天遇到我他也会给我几下子,所以老是躲着他。但有一天晚上,一个流氓——他过去是北京的一个社会青年——喝醉了酒,跑到我屋里来了。他把带铁角的宽皮带往我的木箱上一摆,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你的底我摸着了。我就是专管你们的,你是什么东西……”我想,他是不是要敲诈我,要钱?我有点儿担心,因为我总是有点儿怕那个皮带呀,何况他又喝醉了酒!我真紧张哪……谁知我那个邻居进来了,对他说:“走,到我家喝酒去!”把他拉走了。我想,这个小伙子还真是个好人,他帮了我了。又有一次。几个红卫兵又来抄家。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抄家,而是来找我的麻烦,因为我的家已被抄了又抄,没剩下什么东西了。他们一来就要我背语录,然后又是翻东西,找黑材料,打我。忽然,我听到门外有人嘟嘟噜噜地说什么,这几个小孩就赶快溜了。我想,这真是好事呀。怎么回事呢?我到门外一看,又是我这个邻居。他告诉我,他用“另一派来了很多人”的话把这些小孩吓走了,给我解了围。我在那时确实受了不少罪,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遇见有好人,而且非常多。
我曾经被关在“牛棚”里。开始是一个人单独关的。一天晚上,又关进来一个女的。他们不许我们讲话。后来,他们要她交代自己的历史,但记不下来,便叫我帮他们记录。我从中知道这个女人完全是冤枉的。他们说她是日本时代的汉奸,是抗日联军里的叛徒,是八女投江一案的告密者,可那时她才十二三岁,差得远哪!我很同情她。他们让她背语录,背“老三篇”。她背不下来,我就教她;他们打她,我就替她解释,说她很用功,只因文化水平低,背不下来。那时我的生活费每月只有十五元,除吃饭外,还得买肥皂、牙膏等,所以不能买别的东西。她有肝炎,家里还有一点积存,女儿在外面,可以经常送点白糖、苹果来给她。她每次都非得强迫我吃不可。我们两人虽然不敢讲话,怕被人听见,但心里的感情很好。一个月以后,他们把她叫出去谈话,回来时我问她:“审的结果怎么样?”她说:“他们叫我回家过年。”我说这很好,便帮她整理行李。可是她却呜呜地哭开了。我说:“让你回家,这是好事,哭什么呀?”她说:“还有你哪!”原来她是因为我还没有放出去而哭的!“还有你”,虽然只有三个字,可是这种感情是人类最宝贵、最美好的,而我得到了它。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也就把我挨骂、挨打、下跪等等都抵销了。另外那些人,那些红卫兵,小孩也是可以同情的,他们同样是“四人帮”的受害者。两派联合在一起以后,他们曾经问我哪些人到过我家,拿过东西,做过坏事,要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认识一部分,但我一个也不说。他们是错了,但他们会自己教育自己,将来会懂得自己是错了的。
有人也许会问:你在下边受苦,这些好事是不是故意说的?不是的,我说的这些人都是真的。他们有人给我来信了,我也给他们回信,并且按他们的要求寄照片给他们。不错,我在底下是吃了一点苦,一天到晚劳动,甚至有时一天劳动十四个小时,但这些在我感情上所占的位子很小,而我从人民那里得到的东西却很多。正因为这样,所以,二十年过去了,我还很好,还很乐观。
这些年,我也写了东西。刚下去时,领导上没有分配我劳动。可我住在农场,不参加劳动怎么行。所以我自己提出参加劳动。他们说:“那你就少劳动一点,身体好就动动,身体不好或有事就回家。”但我基本上是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我利用晚上的一点时间记笔记,像美术家画速写一样,天天写一点生活里看到的东西。我想,把这些材料积累起来,将来写文章时是有用的。我还替那些饲养员写家史,让大家传着看。个别的还用他自己的名字在《农垦报》上发表。那时,我不能发表文章,我自己写的就只好压在箱子里。我喜欢买一些好看的本子稿纸,所写的东西就分散在那些本子里。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娃娃们见我的本子漂亮,又没有用完,就把写了字的撕掉,把本子拿走了。这样,我写的东西也就都被弄散了。我曾经写过一个长篇,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停停写写,已经写了十二万字。“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要把它拿走,我说不行,这是我的命,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要我的命也可以,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拿。然而他们非拿走不可,说看看再还给我。还好,他们真的还给我了。后来形势越搞越乱,为了保全这部分底稿,我请一个熟人帮我藏起来(还有别的一些稿子)。可他也参加了造反派,两派打起来以后,他对我说:“不行了,人家也要抄我的家,抄出你的东西来,我就不得了,还是你自己保管吧。”我想:在房子里挖个洞,埋起来?不行。我隔壁一家人是好的,可是另一家派性太强,老是派他的小兄弟监视我。最后我想了个办法,将稿子卷成一卷送到农场公安局去。我对他们说:“请你们留下来,这是我的罪证,将来定我的罪就靠这些材料,千万不要丢了。”他们收下了。后来,另一派的人把公安局抢了,很多东西都丢了,我那一卷稿子也没了。前几年组织上派人到东北去找过,但找不着了,没办法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当然,我可以重写,但这需要很多时间,而我现在最主要的恰恰是时间不多了。不过我又想,“文化大革命”十几年,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这么穷,这么落后,而且风气这么坏,我们的国家损失了多少东西!我那一点点算得了什么呢?我还是从头来吧!《人民文学》本年第七期发表的《杜晚香》,就是过去被抄走现在又重写的。
我现在要写的主要是一个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已经写了十六七万字了;最近要在安徽的《清明》上发表头几章,约十二万字,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这本书从刚解放时开始写的,已经二三十年了。我这个人多灾多难,我的书也是多灾多难,因此常常搁笔。周总理逝世时,我曾想:这一辈子大概就这样了,永无翻身之日了,我的书也永远不会出版了。但是,我能就这样活下去吗?不能。我得写,得把这本书写出来,活着不能出版,死后也许能出版呢!所以我就继续写。今年一年没写了,因为党要给我平反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可不容易平静啦。我现在惟一的想法就是下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到庙里当尼姑也行——写我的长篇。自然,这当中我也可以写一点短篇。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写这个长篇了,就写你自己的一生吧。”我也想,写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也可以写;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吧。前些日子,我在医院里随笔写了一点我在“牛棚”里的生活。现在有“伤痕”小说,我看过一部分,这是在文艺上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写的“牛棚”小品不是当作伤痕,而只是抒写当时环境下个人的感情,我把这当做有趣的东西来写。
三
最近,有的小青年给我来信,说他从过去的《文艺报》上找到我的《“三八”节有感》,全文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说文章写得好,要学习。我个人看,如果现在把这篇文章再发表,相信读者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曾经翻译成外文,外国人看了觉得实在没什么,不理解为什么要批评,后来还说是反党的毒草,并做为把作者定为右派的一条理由。这对于外国人来说,恐怕是很难理解的。我以为,对于事物总得了解它的历史和环境,《“三八”节有感》我已不记得全文了,大约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一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土包子”老婆另找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个我认识的女同志离了婚,在我面前发牢骚,我对她们有同情,当时我对于事情缺乏全盘的调查了解,也未考虑影响和后果。因此,报社晚间来信约我写稿,说第二天要发表,我就一挥而就,连看都没再看,便匆忙送给编者。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人拥护。但过了几天却来了意外的批评。
第一次听到对我的批评是在延安的高干学习会上。有同志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竟有人骂起领袖来,那不行!”我还想,这是在说谁呀?听来听去,原来是说《“三八”节有感》。当时,有的同志怕我受不了,坐到我旁边来,问我:“怎么样?”朱总司令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也不放心地看着我。当然,会上不只是批评了我,还批评了《野百合花》。但在总结的时候,毛主席还是保了我,这是大家不曾知道的。但这是事实,当时与会的同志可以证明。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这次会后,我被调到文抗机关领导整风,担任机关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这就是说当时我这个问题不严重。我在延安整风学习时检讨了这篇文章有立场问题,而延安从来也没有把《“三八”节有感》打成什么反党毒草,更没有把写文章的人打成反党分子。可是一九五七年再把这篇文章拿出来批判时,说它是反党文章,是反党分子拿它向党进攻的。为什么?理由我就说不清楚了。
当时,我们对首长、对领导都是忠心耿耿、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就会打败仗,革命会完蛋。因此,我们队伍里面的东西,哪怕一根草也是宝贵的。可以有批评,但一定要考虑历史条件,并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们的延安,我们的敌后根据地,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吃了那么多苦,干了那么多好事,你不说好,倒说不好,挑毛病,我听了也会不高兴。那时正在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我们条件不好,敌人有大炮、有飞机,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来。国民党反动派又封锁延安,天天骂延安。因此,我们工作上如有缺点,可以向组织上提意见,可以在适当的会议上批评;公诸文字,帝国主义、反动派就会拿去利用。后来毛主席曾对我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这话说得我很信服,以后我再批评人时,就学着先估计到人家的优点、长处,然后再说缺点。现在要从文字上来评论《“三八”节有感》是不太好评论的。当然,现在没有人再说这篇文章是反党毒草,写文章的人是反党分子了。不过,我自己想来,这篇文章也确实有一个大毛病,它有点仅从妇女本身来谈问题,说妇女要奋斗,要独立,要有见解,就不怕男同志离婚了,这是不足为法的。因为你再强,他同你没有感情,要离婚还是得离。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
同学们问我“一本书主义”。过去有人说我是“一本书主义”。我没讲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拿我的某一本书去向党、向人民要什么。但我确实在几位青年作家面前这样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哪怕只是一本好的、有用的书也是好的。”一个作家,如果尽写一些不好的书,有什么意思?过去曾经和一个外国作家聊天,他说:“一百双皮鞋不太好,我们可以欢迎;但是对于作品,我们宁肯要一篇好的,也不要一百篇不好的。”他着重的是质,而不是量。我至今还没有写出这样一本好书来,我还要为写出这样一本好书而努力奋斗。我的朋友很多,我要写的人也很多,但我并没有很好地写出来。我想挤一点时间,磨几个人物出来,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我这一辈子。
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今天就谈这些。讲得不周到,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