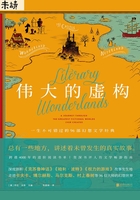(京西友谊宾馆东北区二单元7217房间)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丁:你这次回来,见到哪些作家啦?
於:我这次回来,就只想见你一个人。周而复先生我看到了。主要的是想来跟你谈谈。
丁:你到中国来,比其他一些外国朋友方便,你中国话说得好,中文也好,文笔很流畅,很细致。
你在国内只念到中学?
於:嗯!念到高中一年级,然后我到台湾去了,大学是在台湾念的。我大学念完才走的。
丁:在大学是谁教的?
於:大学是李大采,是四十年代的,我念外文系然后转历史系,中文系。是台静农台先生,然后是沈甘伯,都是一些老教授。
我有几个问题,假如你太累或太麻烦,就简单答复一点好了。很多人想了解你延安以后的一些情形,能不能概括地讲一些。
丁:没什么好讲的,一般的嘛,大家也都了解。
於:我们想比较细致地了解一点你这么多年的生活,离开延安以后的生活。
丁:离开延安以后。那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啰!
於:嗯!
丁:日本投降以后,我就到了晋察冀,到张家口了。本来我们是想到东北去的。但因为交通不好,国民党进攻我们了,所以我就暂时在张家口留着了。说老实话,我那时不太想到东北去了,我有点舍不得老区了。晋察冀是老解放区,有点舍不得,所以我呢,并不急于走。
正在这个时候,“五四”指示下来了,就是四六年了。
“五四”指示是中共的一个文件,叫“五四”就是五月四日啰!那个指示呢,就是要进行土地改革。这个指示一下来咧。我非常高兴,我就马上向晋察冀中央局提出,要求参加晋察冀的土改工作队。于是,我就在怀来,涿鹿,桑干河那一带参加了土地改革。走了好几个村子,学习了一些东西。
正在这个时期,国民党进攻张家口,打平绥路,八月中秋刚过,我们刚把一个村子的东西分完,战争就紧张了。我们的部队就要南撤了,那个时候我很不想离开那里,刚刚搞完土地改革,老百姓翻身了,和这个地方刚搞熟了,可是我们又要走了,这个地方哩,国民党又要来了,那个时候,心里头是难受的,不想离开那里,想留下来,和老百姓一块打游击,但是不行呐,那里是新解放区,不是老解放区,还没有游击队,而我们这一次撤军又比较快,没办法。我去县里,到这里来了解撤退道路的同志看见我了,就说,你还在这个地方呀!张家口都在撤了,你还不走哇!我想一想,没办法,孩子们还在张家口呢,所以我就到张家口了。到张家口后,有两个方向好去,但我提出要求,不到东北去,愿意到老解放区去。这样,我就回到了阜平。
於: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材料要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呢?
丁:一到阜平,我就和他们说了,大约这部小说已经有了,现在需要的就是一支笔、一个桌子、几张纸,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面就开始写了。
於:那是一九四七年吗?
丁:四六年十月间了。到四七年,又土改了,要复查了,规模更大了。那个时候土地法下来了,公布了,就比“五四”指示具体了,也修改了一些“五四”指示的一些东西了,也补充多了,于是,我又参加土改了。
於:去哪里呐!
丁:开始还是到河北,到冬天的时候就参加石家庄附近的村子的土改。过去的土改,是在打仗的环境里,这次虽说还在打仗,但部队是在前面,是我们打国民党。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长,在一个村子里待了半年呐!
於:那大概到一九四七年的夏天?
丁:到四八年了。四七年冬天下去的,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呢,已经写了一大半。这次参加土改收获比较大,我一个人负责一个乡,管五个村的土改工作,我自己专门搞一个村的工作,那就比较深入,对老百姓的关系就比较了解了。
於:你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呐?有一个什么职务呐?叫什么呢?我是看过你那本小说的。
丁:我们那时叫土改工作组,我的身份是组长。我管一个乡,五个村,光我这个村,就两千多人,比较大,另外的四个村子比较小一点,我是同华北联大一同下去的。华北联合大学。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新解放区嘛!吃的就是谷米饼子,不是小米,也不是玉茭,就是小米连壳一道碾的,刚去的时候,我们年青的学生哪,说老实话,都咽不下去。一吃到嘴里就散了,就满嘴巴都是粉了。
於:而且对胃也不好!
丁:噢——那就不管了。
於:你那时候就没时间写了吧!
丁:没有,全部作工作。这一次从头到尾,搞的比较细致一点,半年以后,我有点不想离开了,我想在那个村子当村长或者当个支部书记,比写文章有兴趣了,因为那里一个党员都没有,只有一个军属,二十多户地主。
於:你不是说那地方才一千多人吗?
丁:两千多人,二十多户地主,富农。地主里面,有很多国民党员,都是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主,不是那种“土”地主。土地主好对付,这些人哪,不好对付。我那时不叫丁玲,原来我姓蒋,我还用我姓蒋的名字。
於:我们都还不知道您姓蒋,只知道您叫丁玲!
丁:地主他们在房子里说,那个,她就叫丁玲,她是个作家,过去嘛,还有个作家叫谢冰心!我们的民兵听到了也不懂呵,跑回来告诉我,我就说,这些地主呵,是相当不好搞的呀!村子比较大,又离石家庄近,才十七八里路,又是平原,家里有在外边念书的。
我们还没去,他们就有贫农团了,他们的贫农团,表面上是贫农,骨子里是地主,你一去,又不能否定他们。他们都是贫农呵!所以,你就只好承认他们,你只能慢慢来了解,后来我们作了一些工作,才把这个假贫农团揭露出来了,才又组织真贫农团。
於:那时候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呵!
丁:是相当困难,民兵掌握在他们手里,有一次开大会,五点钟,他们把民兵站上去了,准备和我们干起来,发言的人,也是贫农,可是会说的很哪!在那个地方将我们的军呐!那天,我事先知道,我跟区委书记说,咱们俩一块参加会去,一开会,先揭露了他们的两个坏人,把他们的锋芒打了,他们没想到我们有这一手,结果他们慌张了。因此有些贫农呢,就不说话了,有的贫农就跑了。所以说,这半年的学习吔!比在哪个地方的学习都好。很多材料的了解,都是靠和老太婆睡在一个炕上说悄悄话。
於;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信任你们了吧!
丁:不容易信任呐!得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来呀,他怕我们走了,那里的人要报复他的呀!
那我后来是不是写那个村咧!没写那个村,我们后来太忙,没时间了,可是有一个好处,那个地方的人物,那个地方的生活给了我底子,我要写的时候,人物就多了,人物就丰富了,我了解的东西就多了。……
丁:我们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太长了。
於:重点还是先讲一下《桑干河上》是怎么写出来的吧!
丁:半年以后,我就回来了,华北联大要上课了,所以都回来了。
於:你回来在哪里呐!
丁:在正定,华北联大在正定,正定在石家庄北边一点,是一个县。华北联合大学从城里搬到乡下去了,那时我就住在县城里面,接着写《桑干河上》。
於:那是一九四八年年中的时候吧!
丁:这是四八年夏天啦,夏天就写完这本书了。正好世界妇联要开会,中央决定叫我去参加。这时小说也写完了。就从华北动身到东北去。从东北到外国去。
於:去哪个地方?
丁:原来是准备到波兰去开会。后来波兰不能去开会就到匈牙利去了。
於:你去的时候把这个稿子带去了吗?
丁:拿到大连出版了,大连的条件好一点,那年出国的时候,这本书就带到国外去了。我们这个妇女代表团是蔡畅带队。蔡畅是世界妇联的副主席。
於:你们去开会多半是讲些什么?开会的内容是什么?
丁:开会当然是讲妇女的问题了。不过,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外国人啦,记者啦,总是要跟你谈谈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吧!在苏联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法捷耶夫同志。还跟他们谈了一些解放区的文艺状况,也是一个任务哇,那时借这个机会,把文艺工作向国外宣传一下。所以,我这个《桑干河上》他们就翻译了,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出版了,在苏联就发表了。
於:四九年?
丁:四九年!在夏天我再出国的时候,就发表了,给我看了。
於:四九年你又出国了?你去哪儿?
丁:嗯!开世界和平会。那是郭沫若当团长。
於:那是在苏联?
丁:是到捷克。会是在巴黎开,可是巴黎不给我们签证。我们进不去。和平会就分两个地方开,巴黎一部分,捷克一部分。我们正在开和平会的时候,南京解放了。我们可高兴了。那是四月间,回来时参加苏联的“五·一”嘛,回来后,我就参加了第一次政协。
於:你那本书是哪一年得的斯大林文学奖?
丁:是一九五一年奖,五二年才通知我的。开完政协会,就开文联的会,第一次的文代会。完了又成立作家协会。茅盾是作家协会主席,我和柯仲平两个是副主席。同时我负责文联的《文艺报》。
於:这以后我们就很有兴趣地看到你的写作状况了。那个时候消息就比较多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很久以后我们才看到。我看到的是英文本。我现在介绍的就是你那本英文本。还介绍你那个《莎菲女士日记》,因为别的都还没有英文本。
丁:过去有一篇是龚普生翻的,她是龚澎的姐姐,章汉夫的爱人。这篇文章以后被批评了,说是毒草。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
於:《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一篇我看过。
丁:《文艺报》五一年的时候就交给冯雪峰编了,我就没编了。因为那时工作比较忙,我还有一个文学研究所要负责。文学研究所是培养作家的,大部分都是老解放区来的,有一些生活经验,也有一点创作,就把这些同志拿来培养。如现在挺有名的陈登科、徐光耀都是这个里面的学生。
於:你那时写不写呢?
丁:在研究所里呀?开始都在一块儿,我们老解放区的这一些人,都是只会打仗,没读过什么书,所以来了哩就有计划地给他们读一点外国的东西,一些古典的东西,再读一点现代的东西。讲讲文艺的理论。将来你有机会,找找陈登科,那是很有趣味的,他是个农民,刚参加革命时,是给游击队挑担子的。他识字不多,在部队里,一边行军打仗,一边识了一点字,他喜欢写,报社里看上了,就让他去当个记者。他这个记者是不能写的,只跟着别的记者一起跑,先看着人家怎样写,慢慢地自己学着写。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於:我看过他的短篇小说。
丁:他到文学研究所来以前,根本不懂什么“典型”什么“主人公”,什么文艺上的一套名词。至于什么“现实主义”就更不了解了。他只晓得在底下,在生活里,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把它写成个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加花,再把自己的东西放一点进去,就这样,他的成长,应该算是一个典型吧!因为有一些人,多少总还知道一点,他却实在是懂得的太少了。中国有哪些名作家,这些人都有什么作品,全不知道。现在呢?是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现在写长篇一本本的写,又是长篇,又是电影剧本,《活人塘》是他早期的一个短篇,就是这个短篇使我们觉得还不错,觉得这个人可以培养。
於:你自己哪?你自己写过一些什么东西?后来就看不到你的作品了。
丁:我没写小说了,在这个时期中断了,因为净忙于事务。《文艺报》要发稿了,明天一定要你写一篇,好!我就开夜车给他写一篇,这个时期我只写一些短文章了。
於:是杂文吗?
丁:都是杂文、评论等等。
於:那个时候是不是受到过批判?
丁:没有。就是因为我工作忙得很。作家协会副主席,编《文艺报》,文艺报不编了,还要管《人民文学》,又管了个文学研究所,还有许多外事工作,会议又多得很。没有时间写小说,就只写了这些短文章。到五三年以后,因为腰不好,腰椎骨增生、变形,坐着都很费力,就把工作交出去了。
於: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是在延安的时候你太劳累了?
丁:我这个腰在延安时就有病,主要是受潮了,后来慢慢地越来越厉害,但那个时候满不在乎,我写《桑干河》的时候,曾犯得很厉害,专门作了一个炉子,把背靠在炉子上,晚上睡觉,放个热水袋。就是这样坚持写下来的。从五三年冬天起,东跑西跑,到处搜集材料,到五五年,这两年当中,写了八万来字,写了五篇散文,(这五篇都没有收到集子里)只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下,后来我到农村去了,到五四年,我又重写了。
於: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下集?
丁:是的,叫《在严寒的日子里》。写了大约十二万字,到“文化大革命”时一抄家,就都给抄没了。所以,现在写的咧,是到山西长治以后,又从头写的,大约已写了有十七万字的样子,七月间有一个刊物要发表它十二万字。
於:是继“桑干河”写呢,还是另外的题材?
丁:时间、背景接着写下去了,人物就不是了。因为要照原来的人物写,就要受限制。所以就另外写,但生活背景都是那个时候的。
於:五五年是因为哪一篇文章开始被批的呢?那以后的情景我们简直不太知道了。
丁:这就不要谈它了。
於: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件事。就是要问你!
丁: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你去问过去的中宣部去吧,我个人是不想谈它的。横竖现在已经说是错了,那就算了吧,还有什么说头咧,你说是不是?既然已经说是错了,那就一笔勾销吧。
五五年那个时候在报纸上批判的是丁陈反党集团嘛!这是公开的嘛!现在说,这个反党集团根本就没有,那就算了。
於:什么反党集团哪?
丁:叫“丁陈反党集团”,还有一个叫陈企霞的,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这报纸上都有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这个反党集团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那就算了。
於:那个时候,你到哪里去了呢?
丁:五八年,我就到北大荒去了。
於:从五五年到五八年,这三年你在哪里呀?
丁:我就在北京哪!就在北京等哪!在北京我还在写,写些短篇,但都不能用,所以就都搁在那里,现在也都找不着了。
於:这就是说,五五年到五八年他们对你还没怎么样,你还可以坐在那里写东西。
丁:住的还是很好的,房子还是挺漂亮的,我自己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顶多就是没有工作,没工作,正好在家里写文章,写一些短篇!写着写着,噢,一听,有了反党集团了,写不下去了,要求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你干嘛用那么奇怪的眼睛看着我,慢慢你就会清楚了。
社会是复杂的,思想上也总是有曲折的。世界嘛,总是向前走的,我们也总是要向前看的嘛!
於:可是你这么多年没有写,这多么可惜呵!
丁:可惜的事多哪!岂止我一个人!
於:这么多年都浪费掉了。
丁:我们如果要写出这一部分的话,那就好了,有体验了。
於:我听到许多谣言,也不晓得你还在不在?也不晓得你到哪里去了。我七五年回来就要求见你。但那个时候一个作家都不让见,连惟一的浩然都不让见。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丁:不要说你这外国人了,就连我们山西本省的人,有的明明知道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要来看我们都不行,你要看,得问中央,得要有中央的介绍信才行。
於:那时我开了一堆名字,一个也见不到,连浩然也见不到,根本不知道丁玲在哪里。
丁:不要说一般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就连我们的女儿,儿子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直到后来,我们才写给他们,他们才知道我们在山西。从五八年以后,我们的儿女就和我们划清界线了,他们划清界线,并不是承认我妈妈是坏人。而是在一块没有作用,没有好处,他也不能帮我,我也不能帮他,他同我划清界线了,他还好工作一点嘛!我也很赞成。他如果在工作中发生一点问题,与我们没有关系,如仍与我们来往,那他在工作当中如果发生一点缺点(正常的,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缺点)那人家就会说:是受了家庭的影响。
於:五八年你到北大荒去,就是他们定了你的罪了是不是?你才去北大荒的?北大荒在哪儿?
丁:在黑龙江省。你知道大庆吗?就在大庆那边,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你就看看这个地图册吧。
於:你那时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丁:我去的是一个农场。说老实话,是我自己要劳动的,环境不太坏。
於:什么样的劳动呢?
丁:我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是他们跟我商量的,喂喂鸡吧!比做大田的事好一点,喂鸡的事,时间由我自己,他们说你看着办吧,累了就回去。养鸡队的人对我很好。我就从头学到尾,你在美国没有看到孵化室吧!把鸡蛋放在柜子里孵成鸡嘛!
於:参观的时候看过。
丁:先学选蛋,选种,选完了放进电柜子里,孵鸡也有些技术东西,我也学了。
於:你有机会写东西没有?
丁:没有机会写东西,就学搞这套,然后养小鸡。后来就养大鸡,养病鸡,养了一年又到饲料室,没有粉碎机,菜就只好手工剁,后来有了粉碎机,好一点。养鸡很好,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专门搞写作的人,一喂鸡,我的最高理想就是将来当个养鸡队长,就是想将来怎么发展养鸡业,怎么把鸡养好,脑子里装了一套养鸡的计划,我就是只想养鸡哟。
於:那怎么成?你不写作,根本不成的嘛!
丁:哎呀,你不理解,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我这个共产党员,不论走到哪里,都应该比别人要走在前面。我既要劳动,就要比别人劳动的好。我现在背着一顶帽子下来,就要给人看一看,我并不在乎。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工作就要比一个普通党员做的还要好!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我走到哪里,都要首先把我的工作当作我的主要任务来做好。
於:不过,你先是一个作家,后来才参加共产党的嘛!
丁:但是,我既参加了共产党,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嘛!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对所有的东西有爱好,我非写不可。但那个时候,我的条件,我是养鸡嘛!得把鸡养好嘛!
於:我就是想了解你当时的心理。
丁:你不懂我这个想法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工作都爱,只要说这个工作值得作,我都有兴趣,刚刚不是讲过土地改革吗?成天和一些老太太在一块,当时我就想,在这个村里当一个支部书记真不错。但也不是说就不想写东西了。
拿养鸡来说吧,养鸡的时候,我比普通的人养的好,每回开会的时候,队长都表扬我。本来不应该表扬我,我是一个右派,怎么能表扬一个右派呢?但他非表扬我不可!因为我的鸡养得好。我的鸡舍比人家的鸡舍干净,我的鸡产蛋率比人家高。鸡有病了,不生蛋了,给我,我养吧,结果我养了两个星期,鸡又生蛋了,比人家鸡蛋还生的多了。人家就说,老丁这个养鸡就是和人家不一样。
后来我养小鸡,小鸡每一回刚出来的时候,总要埋掉七八百个。为什么咧,因为那个鸡看起来要死不活,没希望,要去养它不合算,要喂精料,要喂牛奶,还得喂鱼肝油,青霉素,不合算。所以就把它摔死,埋掉,不要了。我呢,觉得可惜的很,七八百个小鸡都埋了,光蛋就不知道值多少钱,太可惜了。我就跟队上讲,这种鸡由我来喂,好不好?他们说不要了,算了。他们不在乎。我说不行。后来我就来喂这种鸡。我用一个大炕,分了格子,这是最差的,这是好一点的,这是又好一点的,我就自己喂,喂上五天,不死的话,那就说明这个鸡是好鸡,就应该养下去了。结果,我养这种鸡比他们养好鸡的成活率还要高。我的成活率是百分之八十,那就说明,每次埋掉的七八百个鸡都是浪费啰!是可以养的啰!至少,百分之八十都是浪费的啰!五天一批,五天一批,我养了一个多月,养了七批,养下来,把我自己养垮了。趴在炕上,爬都爬不动了。没办法了,只好说,老丁,你别养了,我就不养了。但这件事在饲养员里面就起了作用了,就认为,这种鸡可以养嘛!
於:你那个时候的精神食粮是什么?
丁:从早忙到晚,我是每天晚上非看报纸不可的呀!
於:你除了报纸还有什么东西可看的呐!
丁:我们的报纸、杂志订了二十几份,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订了。我们两个,那时候,还要自己做饭,这,你大概也不理解。
於:不,我总觉得那是浪费了你的光阴。
丁: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
於:我不了解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丁:那个时候,我写了也不能发表呵!我住在农场里,那里,人人都在生产,我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写,那就是把我同所有的人都隔绝了,这个隔绝对我的痛苦,比我不写作所造成的痛苦,厉害得多了。
於:我绝对不是说要你整天到晚写东西,总得要花一点时间……
丁:还有一点,我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去呢?本来,不是领导上说,给你个处分,要你到北大荒去。没有。是我们自己愿意去。为什么呢?觉得那个地方很苦。我去了。平地起家,来开辟事业,很有兴趣,这样才去的。
当右派是很孤立的。在社会上最臭了,报上登了那么多次名字,社会舆论很臭,你要想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脚,周围还有人的话,你不和他们在一起劳动那怎么行。你在社会上很孤立,人人都觉得你很反动,谁都不理你,你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和群众在一起,你还可以证明你是很好的,他们才会喜欢你。人都需要人嘛,不能每天都是孤立的。那精神上多痛苦。这样才是很大的安慰,我还是每天能为人民创造财富,大家觉得我还不错,也还能积累生活。这,你会觉得很难理解。
於:不是,我只觉得这事这么可气!
丁:在那时候,写作也不能发表,反倒脱离群众,人家觉得你顽固不化,不愿意改造。而且,在那个时候,不管现在看起来对不对,在我自己的脑子里,受党的教育,看到农民的生活很苦,总是愿意首先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北大荒是一个垦区,我能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垦荒工作,我觉得很高兴。写作只是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嘛!不是我的全部。
於:一个作家,写作不是全部是什么?
丁:你不能光写自己呀!不能只写自己的小天地吧!有机会我们可以陪你到那些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大家在一块,精神是很愉快的。
於:他们不知道你是谁噢!
丁:当然知道!知道我是一个大右派哟!第一天下去的时候,那些小姑娘正在吃饭,就跑过来看,还转着圈看,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后来嘛,我们就住在隔壁,当然也就熟了。
於:先是当一个奇怪的人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呢?冷淡……
丁:还不止是奇怪。而且脑子里还印像着你是个大坏人喏!……
於:是仇视的?
丁:老百姓嘛,主要的是要看,他要慢慢地来看你,他要看你好,他就对你好,总而言之,他脑子里有个大疑问。
於:他开始的时候对你就不太接近啰!
丁:接近呀,底下的人,总是不怕呀!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不怕丢官,也不怕开除,我种地,你开除我,还是种地。越是高一点的,越是要考虑。接近上就要有一点距离,怕受批评!当然,底下的人咧,也受批评,一个饲养员,过年的时候跑来给我拜年,回去就挨了批评。而且马上就来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的门口,“给右派拜年是什么立场!”他跟我一块养鸡,我们一同劳动,当然就有感情,他当然对我好嘛!我的鸡少,他的鸡多,我的鸡舍小,他的鸡舍大,我铲完地了,就去帮他铲,我的汗就那么淌,根本没时间去擦!我就是这样给他们去帮忙。
那个剁菜的,她是个大肚子,我们两个切菜,我住的地方离切菜的地方近,打夜班的不负责任,往往炉子夜里就灭了,菜呢,都是从外面搬进来的,冻的像石头一样,硬的很,可难切了。我就半夜跑去加炉子,清早又去加炉子,等上班的时候,菜可以稍微软一点。我总说你少切一点,我去切,我的胳膊切的都抬不起来了,穿衣服都穿不了了。切也不能切了,真的不行了,那你说她对我能不好呀!在感情上,人家再说我是右派,她也不相信。关系就是这样子的么!并不是说,我劳动时只是在那里稍微干点,而是和他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我们就是自己人,我对那些年青的女孩子呢?就像对我女儿一样,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感情搞得很好。
於:从一九五八年到哪一年哪?
丁:我十二年都在北大荒呀!你都愁死了吗?那是我的第二故乡。
於:很难得的,精神没有垮下来,真是少有的个性,想的开!
丁:我想的开,有些问题根本我就不管它!我从头干我的。从头做人哪!
我劳动了一年以后,王震,就是现在的副总理,他过去是农垦部部长,到那里去了,找我去说:不要劳动啦!你都劳动一年了,改个劳动办法吧,你去教书吧!莫说给工人上课,给干部上课也行嘛!你就可以教政治嘛!你也可以教文化嘛!都可以教嘛!
於:你不要教?
丁:不是我不要教,但我怎么能教政治呢?他当然是好心……
於:你就教文学嘛!
丁:我教文化!就在养鸡队里当文化教员,这一个队的学习归我管,不止学习啰!
於:那养鸡呢?还养不养?
丁:不养了。养鸡可有趣了,养鸡不可怕!
於:养鸡可费时间了!养鸡一共养了多少时间哪!
丁:养了一年多。
於:那好!
丁:我刚说的养小鸡,是我当教员的时候养的。是我自己找来的,那是第三年,是低标准的时候养的,我要求的,我看到丢鸡丢的太厉害了,那个时候当教员有空,我说,业余来养吧。
於:是不是还在农场里当教员?
丁:还在那里,在养鸡队里。
於:教贫下中农?
丁:职工。农场工人。
於:教什么样水平的呢?小学的吗?
丁:有初中班,有小学班,都是我去计划,我去布置有人教。我自己教扫盲班。你听了又奇怪了吧!什么叫扫盲你知道吧!
於:扫盲就是扫除文盲。
丁:因为教中学、教小学都比较容易,扫盲最难了。
於:都是成人嘛!
丁:有些人是因为没有太学习,但有些是认了几回也还是文盲的那种人,扫盲工作,在整个农场里,我这个队是得了锦标的。最突出的一个,她从认识六七十个字到能写一千字的文章。她的学习本二十多个,摆在那里给大家看。半年的业余学习,从开始写字都不容易,到后来连文章都写的很好,不止是认识一千字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十八岁。
於:你十二年就没离开过北大荒哪!
丁:没有离开过。到北京来过两三次。
(……换磁带,漏录一段)
丁:我刚才跟你讲过,我新朋友很多嘛!
於:你一九七〇年离开北大荒的,是不是?
丁:嗯!
於:完了你就到长治去了。
丁:监狱,七〇年到七五年在北京坐了五年牢。
於:是德胜门外那一个牢吗?
丁:是高级监狱,在秦城。
於:是什么罪名呢?你已经有了那么多罪名,现在又加了什么罪名呢?
丁:反革命分子啰!群众提意见,要逮捕,晓得是哪个群众,也不知道,就逮捕了。逮捕的时候,我跟你说吧。人家的心情是受不了,铐起来的时候是不舒服的。那就是表示,你是个犯人,不自由了,你今天是有罪的,当犯人来铐,是很不舒服的,怎么铐起我来了咧?但我脑子里另外还有个想法,救命的来啦,救我的来啦!牢监里总有法律啰!就可以依法办事了。我大约就可以出来了,就可以没事了。我在那里不止是当教员,后来去劳动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当道的时候,就又去劳动了。
於:那是六六年?那就是重一点的劳动了?
丁:谁革命,谁就叫你劳动的多,那是革命。
於:你一个人在北大荒,哪个去找到你的?
丁:北大荒也有革命造反派嘛!有当地的造反派,也有北京去的造反派嘛!我想,“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的事就算了,不要讲了吧!
於:我倒是希望你尽量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丁:当时,我是作为坏人被揪出来了,革命群众自发的起来对我进行斗争,对我进行管制劳动,不仅劳动,还要斗争呵!游街呵!脸上划黑呀!……
於:您也经受过这一套呵!
丁:家常便饭嘛!第一次揪我出去游街的时候,我在房间里,一群娃娃跑进来,中学生嘛!我就问他们有什么事,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什么事。他们也不好意思,因为过去都是一个农场的嘛!他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都是蛮熟的。“你出来一会儿。”“你出来一会儿。”我出来一看,这边有人,那边也有人,到处都有人,都站的远远地看着我,好像看一个大老虎一样的,好像我这个老虎出来一定很厉害。
於:都是年青人?
丁:都是年青人。还站的远远的,不敢走近来,噢,我心里明白了,我说,我先上厕所去一下,上厕所回来我一看,有人拿来一个碗,有墨汁,噢,我心里懂了,我说,没关系,来吧!就来了。向我脸上一划,高帽子一戴戴出来了,哎呀,两边的邻居都不敢看我,他们心想,怎么把老丁这么闹去嘛!他们就这样子,这样子地看我,我就这样子地看他们,我不怕嘛!他们看我都难过,又不敢说话。带我到十字路口,可多人了,有人喊:“叫她站在凳子上!”我就站上去了,他们说:“你讲话吧!”我心里想,讲什么咧?我也是第一次吆!我就喊了:“毛主席万岁!”“拥护文化大革命!”有的人也跟着我喊,群众也没有经验嘛!有几个人发觉不对,“不对!不准你喊口号!”不准我喊口号就下来呗。于是走呵,走。他们就喊起口号来了,“打倒大右派!”“打倒丁玲!”也有几个小孩子踢我,他是想表示对一个大右派的恨。走到文化宫前面,让我站在台子上,他们对我说,你讲你的罪行吧!你讲!我心里真不晓得怎样讲,我就讲,哎呀!我有罪,我的罪太多了,我一下讲不清楚,是不是我们回去后,慢慢地讲吧!面对着这些中学生,我一点也不讨厌他们,我不讨厌他们嘛!他们说,好好好,不讲了,下来吧!就回来了。回来后,把我怎么办呢?一脸的乱七八糟,坐在那里,他们想了一想,还是不对,就说,派两个人送她回去吧!还打电话叫陈明来接我,他也没有去接。送回来后,我往炕上一躺,心里想,不错,我今天不错,考验过了,我也没有恨这些小孩子,我想,现在革命需要我当一个反派,那我就当一个反派,演戏嘛!总有反派的嘛!那我就去游个街,没什么了不起!那个时候,哪里晓得“四人帮”后来那个样子搞咧!我们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嘛!
於:你真的会这样想吗?当时?
丁:就是那么想的嘛!我那时就想写封信给我的儿女,告诉他们说:你妈妈今天受了考验,但是,考过来了,我没有怨党,我没有向老百姓,向人民对抗!我的情绪和他们不对抗,我考验过了,我很好!但是不能通信呐!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几天,他们又把我揪去,和地富反坏站在一块,等他们一个一个地审问,我呢,因为和他们站在一起不舒服,就一个人站在一边看语录,突然有个人发现了,他说:老丁,你念念嘛!叫大家跟着你念嘛!好,我就念语录。地富反坏跟着我念。轮到该审问我了……
於:什么人审呐?
丁:红卫兵呐!我弯着腰,站在那里,他们很天真,不那么可怕!“丁玲!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说:“我现在很高兴。”“你高兴什么?”“我高兴这几天你们成长的很快啰!过去,什么国家大事你也不管,你到我们家来玩,来听收音机,现在,你们要革命,要和我划清界线,我很高兴,你们成长了。”你一定以为我又是说假话了。
於:我相信你不会说假话,但我想你当时一定会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丁:哟!他只十几岁的小孩子嘛!有什么气呢,后来他们叫我去看电影,又和地富反坏在一块,每人挂个牌子在身上。完了,叫我写一个看电影的汇报。我就写了看见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感想。我说,我很感谢你们叫我来看电影,(否则,我是不敢去看的,有人打我,怎么办呢!)但我也有一个意见,我不满意,我不愿意和地富反坏站在一块!
红卫兵也是慢慢变的,开始很纯洁,就是打我,他也是很好的!后来,里面有些人,逐渐地变坏了。
开始,有些红卫兵没有钱买“毛选”,要学习嘛!陈明在书店里看到了,就买一部“毛选”送给他们,他们也接受了。开始抄家的时候,他们到我家里来,把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要拿我稿子的时候,我跟他们商量,我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就是不要拿我的稿子……
於:那是什么稿子?
丁:《在严寒的日子里》。
於:你已经写了吗?
丁:我已经写了,虽说没有条件写,没有机会发表,我还是写了十多篇散文嘛!写了一些人物嘛!这次发表的《杜晚香》也是在那时写的,这次又重写的嘛!我说,这是我的心血!开始,就没有拿走嘛!有几个人说我们拿去审查审查,后来又交还给我们。到后来,有些人就拿掉了一些,小孩子一看我的本子很好看,就把我前面写的撕了,空白纸拿去自己用了,慢慢的有些东西就失散了,我们就把一些长篇的稿子卷了一卷拿到公安局去,陈明说,我们有几样材料放在你们这里,这是丁玲的“罪证”。将来要定她罪这就是证据,请你们保存起来。
最初,我们是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存了几个月,打派仗了,他们家也有被抄的危险了,他同我们讲,这是你们最宝贵的东西,抄走了,我负责不起。同时他也要受牵连,没办法只好交还我们,我们才去交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也是一会儿这一派掌权,一会儿那一派掌权,换派别的时候也没什么交接手续,登个记呀什么的,乱七八糟,我的稿子就丢了,后来,再去找,也找不到了。我的笔记本毁的毁了,扯的扯了,一些谈话记录,材料,都完了,浩劫!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算好的,比我们惨的,死了的,像我们的贺龙,像我们的陈毅,周总理虽说不是挨整,可是那个位置,多难受呵!丢两篇稿子没什么,还可以再写嘛!
於:一九六六年以后,你受的罪更大,是不是?
丁:那当然啰!“四人帮”那时候的事,有什么讲头,总之没有好日子过。天天快黑的时候,就等着吧,今天晚上不晓得哪一个来!听到村子头上有狗叫就知道,来了!他怕我难过,怕我心跳,怕我血压高上来,说:你睡吧,我看着吧!他就坐在窗户那儿看着,我说你看着有什么用呀!他要来还是来,看见了,马上也就进屋了,早知道几秒钟有什么用?别看了。他说,我看着,你睡觉!就这样,坐等着,有时十点钟来了,有时十一点钟来了,有时十二点钟来了。开始,我们还扣着门,人家一拉,门就坏了,后来就干脆不关门,你们来也省事一点,真是风雨飘摇呵!我们俩住一间房子,原来还觉得怪不错呐!主要是场长,对我们还不错,后来,只给我们一间七平方米的房子。
於:这样的房子,一定是泥地啰!
丁:泥地,茅草屋。人家来抄家时,怕我们有东西藏在里面,经常把屋顶捅坏,人家走了,我就站在炕上糊顶子,很矮嘛!一个炕有五尺宽,六尺半长,炕这边有一个门,有一个小火炉,那里放一口小木箱,我们两人要干活只能一个在炕上,一个在炕下,两个人同时在炕下,就挤了,住“牛棚”以后,我们俩都还十分想念这个小茅屋。茅屋再坏,总还是两个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牛棚”,在那种情况下,生活上很苦,精神上也很苦闷。但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於:我就是说怎么活下来呵!
丁:我的邻居,有一个女工,她是好心,就说:你死了算了,像你这个日子我一天也活不了。我说,哪里能死咧!不能死!我是共产党员,要打死我,就打死吧!
於:打不打你?
丁:家常便饭。(看到於呜咽,抽泣,就转口说)但也有好人哪!我讲几个好人的故事给你听听吧!
不要难过,现在是我劝你了。……
丁:我刚才不是讲,我晚上过不去了吗,我睡不了了,我害怕了,没办法了,今天晚上又要来人了,陈明就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值班的是一个妇产科医生,陈明和她说:丁玲头晕,心跳的厉害,他们今晚很可能来揪她,是不是可以叫她在你这里待一会儿。她马上就把看病的床整理出来,说:你睡这里好了。
於:保护你了?
丁:嗯!医院里也有两派呀!要是人家知道了,就要打她,你保护右派!那还了得!
我睡在那里,家里果然来人了,没找到我,走了。
有一个眼科医生对我也很好,我的腰坏了,她帮我注射,打封闭,她是眼科,并不会搞这个,但她却到我这里来,帮我打封闭,把腰麻醉起来,使我疼的好一些。
刚才不是说过场长对我很好吗?这个场长是个好场长。前几天还收到过他一封信,告诉我又回到佳木斯了,又是局里的副局长了,官复原职了。
那会儿他们把他揪出来斗他,要我陪斗,我们俩就弯着腰,站在那里,我是有经验了,他们叫你弯腰,你就弯腰,你别反抗,反抗是不会有好受的,也别求他,求他,他们也不会依你,反正你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松一点儿,你看见的时候,我就弯一点儿。那个老场长呢,他还是老红军呐,资格蛮老的,但挨斗还没经验,他大约弯腰弯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求他们,他说,我弯不了啦!腰疼呀!腰疼呀!他愈喊腰疼,那些人就愈往下按。我心想,你这个人!求他们干什么?你别求他们!后来,他实在不行了,说:叫我跪下吧!他以为跪下了,腰就可以直起来了,好,就叫他跪下了。跪下了,再踏上一只脚,还是弯着腰,连腿也弯在底下了,那就更难受了。我是陪斗的,结果弄得我也得像他那个样子。还有两个专门看我的女红卫兵,那是我们农场的。这时候,这两个人就跑来了,向看着我的那两个人说,你们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吧!那两个人就休息去了,她们两个来了,可有味道了,她们大喝一声:“丁玲!站起来!把脑袋抬起来!让大家看看!看看你这个老右派!你这个大右派!”我就站起来,把头昂起来,呵——!舒服多了!
於:噢!她们是来帮你忙的!
丁:这都是些好人,她要帮你!也只能这个样子帮。
有一次,我在地里除草的时候,碰上红卫兵来了,他们两派刚打完仗,这些小孩子气还没消,正好拿我出气,就把我给拽出来了,叫我背语录,其实,这些语录,我是连睡觉都在背呵!我要背不出,是要挨打的呀!所以我都能背!可是,那么一群人围着要打你的时候,我就紧张得背不出来了,一背就背差了,于是他们拳头、皮鞭就全都来了……不说啦!不说啦!(看到於梨华哭了)
於:看你,就像讲别人的事情一样!
丁: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头子,当然,也不是太老哇!他一跑来,就把他们推开了,摆开比他们那些人还厉害的架势,指着我骂呀!“丁玲!你这右派!你还不劳动呵!你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叫你背你怎么不背呵!”他又对孩子们讲,叫她劳动去!他看见孩子们把手套给我扒下来了,就命令我:“把手套捡起来!去!劳动去!”一边骂,一边叫我除草去。我不认识他是张三李四,他也不认识我,结果,帮我解了围,那些人就不能再打我了。我就去劳动去了嘛!这种人在我脑子里,随时都可以……
(因换磁带,漏录一段事情)
……那些人往外跑的时候,就把我掩护在他后头,幸好,房里的电灯不太亮,就把我保护起来。第二天我们俩又在马路上碰见了,我不敢先开口,他推着自行车,问问我的事,我就跟他说了。
就是在这种时候,还是有人来帮忙的!你看我这样高兴,这样快活,就是因为我自己体会到,还是好人多呵!都那么坏还得了哇!小孩子坏,不怪那些小孩子,怪“四人帮”,是他们教成这样子的。
今天你来这里谈材料,谈的吃亏了,你精神上受刺激了,锻炼锻炼吧!你这样子,太不经风雨。毛主席教育我们:见世面,经风雨。我们是经了风雨的。
於:(呜咽)……那时……到了一……九七〇年……对你越来……越厉害了?
丁:嗯,越来越厉害了,后来不打了,关在“牛棚”里,“牛棚”出来,就又去劳动了。
於:关“牛棚”是什么样子的?
丁:是一个房子,把我们关在里面,关的人多哩!没有自由,不打了,给十五块钱一个月生活费。
於:养鸡的时候,你多少钱一个月?
丁:养鸡的时候?我没有钱,用他的钱呀,我是没有钱的。关“牛棚”的时候,给我十五块钱生活费,也给他十五块钱生活费。
於:你是哪一年关进“牛棚”里去的?
丁:六八年,关到六九年。我关了十个月,他关了八个月。
於:关“牛棚”,有没有审问交待什么的?
丁:也有,有审问,主要是不让你自由!主要是调查别人的材料。不打人了,过年还给饺子吃呢!把肉馅给你把皮儿给你,自己包饺子吃。他们哩!比较好一点,是集体的,一个屋里住上好多人,还可以聊聊天。
於:你是单独一个人?
丁:我是单独一个人。当中有一个月,进来了一个女的,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啦!人家说她是日本时代的汉奸,是日本特务,说抗联战士“八女投江”就是她告密的结果,是被她出卖了,日本兵才来的。把她弄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们审她,没有人记录,叫我在旁边记录,我听了心想,真滑稽,那时她才十二三岁,又没文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怎么会是特务呢?过年以前放她回家过年去,我挺高兴地帮她收拾行李,她却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叫你回家过年不是很好么?她只说了一句话,“还有你哩!”她哭,是因为我!我心里有点难受,也很感动,但我没哭,我默默地在那里帮她清理东西。一会儿,带她的人来了,我们就不能再说话了(我们虽然关在一个房子里,按规定,是不准讲话的)。就这样,把她带走了。巧得很,她的丈夫就是路上曾经保护过我的那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后来也被关在另外的一个“牛棚”里了。你说,这样的感情,叫我怎么不喜欢这些老百姓呵!叫我怎么不想她!所以,我现在呵!就是为这些人在活着。要写,也就是要写这些人,不写他们,我写谁呀!
这样的故事是讲不完的。有一天,有些人又来抄我的家,实际上,当然不是来抄家,已经抄了多少遍了嘛!实际上是来看看有什么顺眼的东西可拿的。其实拿来拿去的,也没什么东西了。他只剩了一件衬衫,还给人家撕破了,每天穿着它上班,汗水都把这件衣服渍成白的了,没有换的,只有星期天才脱下来洗一洗。他们一来,总不是说来拿点东西,总是说我在家里写黑信,这一派说我帮那一派写,那一派说我帮这一派写,找这么个罪名,就在我家里来翻箱倒笼,同时,就要折腾我呐,他不揍你两下也要捣你一家伙,碰运气吧,有时厉害一点,有时就少挨两下。我求他们:我说我欢迎你们来监督我,我希望你们白天来,你们半夜晚上来,把屋子里的东西弄得稀烂,你们走了,我们还得清理好,明早还要按时上班,还要劳动呐!
这一天,他们正在折腾得厉害的时候,忽然间窗子底下有个人说话,话说完了,他们一群人就都走了。什么事呢?陈明就跑出去看,原来说话的是我们的邻居,他告诉他们,另一派的人马上就要来了,赶快走吧,要吃亏的,他就把他们给骗走了。他和我们不是一个队,过去也不熟,所以,像这样的人多了。他了解你,也了解农场,他敢这样做。
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先是在汤源农场,后来到宝泉岭农场。后来,汤源农场把我揪回来。我一听,是汤源农场来的,我就不怕,他也不怕。这个农场,我待了六年,我在这个农场里喂鸡。当文化教员,熟人多,朋友多,所以不怕。回来后,当然要批斗,不斗你,他揪你回来干什么?但只是形式上的批斗,在批农场党委书记的时候,叫我陪斗,斗完之后,我陪他坐汽车游了一趟街。但他们对人总是说,大右派在我们这里放了很多毒,我们要消毒。事实上我坐在那里天天没有事。大家问我,你在那边,他们把你怎么样啦,看把你折腾的这样瘦,你在那边受罪啦。他们说,你就在值班室给我们烧炉子吧,晚上喂鸡的,喂猪的,打夜班的都到这里来,休息的休息,喝水的喝水,聊天的聊天,有些人晚上还特意来看我,来安慰我,所以很不寂寞。住了一个月,我们才回去。
於:那是哪一个时期哪?
丁:那是六七年,正是挨打的时候。把我接回来之后他就后悔了:“把你接回来干什么!住在那里比在这里保险哪!”当然,我们心里也明白,揪我去的人,不一定是要保我们,但去了以后,因为我们熟人多,朋友多,就自然地形成一个保我们的局面。养鸡队就曾开过我一个批斗会,主持斗我的那个人,是个技术员,他那时是造反派。他们的本意是要通过斗我,整过去的那个支部书记的材料,然后寄到他现在的单位去。他们就说,支部书记包庇我,我嘛,拍支部书记的马屁,我们的关系搞的很好。我说,是呵!过去我和支部书记来往多,关系比较密切,他叫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我做的事是好哇,是坏呀,六年了,大家都是看得见的,大家来评论好了。至于我和支部书记之间有私人关系没有,我说没有。他经常到我家里来,我留他吃饭,他都没吃过,有一次他吃了我个馒头,咬了一口就扔了,他说:唉呀,这样子的馒头多难吃,我老婆给我做的馒头可好吃了。那也是事实,我不会做,他老婆会做嘛!我一讲,大伙儿都笑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大伙儿就笑哇!我在那里讲,大家就像听我讲故事一样,都是熟人嘛!情况也都了解嘛!后来那个主持会场的人就说:“下来!下来!今天的会不开啦,改天再开!”以后,也没开了,我就住在那里了,所以事实证明,他要想斗,也斗不起来。
我要是那个时候不和他们一起养鸡,不和他们把关系搞好,要是我关起门来写文章……,那他们就不会管我了,谁敢保我呀!当时看守我的,都是背着枪的,他们两派武斗起来,也还是蛮厉害的。他去看我,武装排的一个副排长就说过,“你放心好了,老丁在这里,我们保证没有一个人,敢动她一个指头。”所以,把我一接回来,他就后悔了。“你就住在那里,多住几个月不好么?”我们家这里还在打吔!在那种大动乱的时候,脑子里想不了那么多,总希望两个人在一块儿,总愿意两个人一起度过。
於:在“牛棚”里怎么就放出来了?总不会随随便便就放出来吧!
丁:“牛棚”之所以能够建得起来,就是因为看到全国都有“牛棚”,后来,大家也觉得这不像话,在机关里关了这么多的一批人,你又不是监牢,你又不是法院,关了这么一批人干什么?准备怎么办?所以“牛棚”得取消!但“牛棚”里的这些人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宣布他无罪呀!那么,就都放到生产队去监督劳动。这样子才把“牛棚”解散了。
於:那个时候的劳动是很重的体力劳动了?
丁:也有。也不一定。譬如我们去割麦子,因为我原来就没干过这个活,我原来是喂鸡的嘛!一把,才抓了几根,拿着刀也割不下来多少,人家就说,丁玲,你别割了,你到后边去捆麦子吧!我就去捆麦子,捆也捆得慢的很,干什么都不行。厨房里有几个老头子就帮我说好话,“她能搞什么大田劳动,叫她来帮我们的忙吧!”结果就把我给弄来了,这些老头子看不惯那些人,觉得他们太不像话了,老头子们对我很好,叫我到菜地里下菜。菠菜好了下菠菜,黄瓜好了下黄瓜,下洋柿子,下豆角,帮他们锄草,浇水,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我的劳动可以轻一些了。
但是,我同房间的这些造反派太厉害,都是些年青人,高中毕业生,她们每天中午一睡睡两个钟头,但不准我中午休息,还得在那里干活。白天,我干了一天,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总该叫我睡觉了吧,还是不行。
於:她们不让你睡觉?
丁:她们在唱歌!在唱样板戏呀!她们都是城市姑娘,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可有精神了。我可不行呀,我还有个毛病,一睡就打呼,越疲倦越打呼,结果,一打呼她们就踢我的床铺,“哎!起来,起来!”她们甚至还叫我写个保证书,保证睡觉不打呼!没办法,我只好找医生,说,医生,给点药吃吧!医生说给点什么药?我说,给点不打呼的药。他说:没有,没有这种药。
於:怎么会到这种程度呐!
丁:小孩子嘛!慢慢的咧,到了早上,她们说:丁玲!你去打些洗脸水来!好,我又给她们去打洗脸水,打水来给她们洗脸。慢慢的咧,她们又说:你不知道扫地呵!好,就扫地了,到后来,连她们的尿盆也要我倒,晚上还要起来为她们添炉子。我侍候她们,为她们做事,给她们当老妈子,表面上看来,我倒楣的很,倒的不像样子了,可是,我心里想着一个人,我们那个农场里有一个标兵,过去她领导过知识青年。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刚到这里,早上起不来,她呢,就每天早上跑去,替她们倒尿盆,替她们扫地,叫她们起来,帮她们铺炕。这个标兵和我是好朋友,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她,我想,她能自动地照顾这些女孩子,我为什么不能自动地照顾这些女孩子呢!她们也许觉得我是一个右派,我不革命,我应该侍候她们。但她们毕竟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怎么能怪她们哩!我现在不能从其他方面帮她们的忙,说上几句教育的话,但我以那个标兵朋友为榜样,替她们服点务也可以嘛!
有一个时候,她们又把我叫去打扫厕所。没有打扫过厕所的人,一听到这工作,就会以为这是最不好,最下贱的工作了,事情在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那里地下水位高,要是一下雨,水再冲进来,厕所里的水就涨得很高,大便就很不方便啰!因此,一定要把这个稀粪弄走才行。开始去,我心想味道一定很难闻,还戴了一个口罩,后来,我才明白,戴什么口罩呢,没什么了不起的难闻,待久了,有一点难闻也不在乎了,我就成天在那里弄。就像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有个神犯了错误,宙斯就罚他打干那个井里的水,但他老是打不干。我也是那个样子,老打不干,因为地下水位高,我打下去那么一大截子水,第二天就又长上来了。我自己挖了一个沟,让粪水流到地里去浇菜,弄个瓢来舀水,舀个两三百下,休息一会儿,有时舀个一两千勺子,每天拚命地打,要是一直打到底,我就可以有三天不打了。……
於:你那时的身体怎么样?
丁:怪,人就是怪的很呐!那时是不病的。我心里可高兴了。我心想,谁都不愿意干的事,我愿意干,那就是说,我比人家了不起了。再有,每一个走进厕所来的人,都不害怕了,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大便了,都高兴了。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心里很高兴。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七〇年了,她们搬到有暖气的好房子里去了,她们说,丁玲还能住有暖气的房子呀,那以后,我就没和她们住一间屋子了。……(磁带完了)
(周良鹏根据录音整理,陈明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