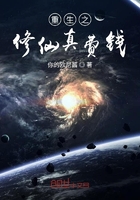白医看了看伤势,从他那木色的小药箱里拿出来一个红色小瓶,继而瓶底朝天的倒出只能覆盖大拇指面积的白粉,转身狠按在白衣满是沾血的胳膊上。白衣闷嗯了一声,脸上的表情比刚才还痛苦,可看到他那样痛苦不堪的样子我这心里更痛苦。
“白公子伤势严重,手臂已是骨折,需要静养,平时不能……”
“什么?骨折!”我打断白医的话,不确定的看着白医。方才在路上我就已经想过这件事了,如果真的那么严重,白衣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又如何面对他。他白衣救了我数次,如今又是为了救我而废了一条胳膊。那,那我这一辈子不就活在愧疚当中……
白医有些不耐烦,“听本医说完,他虽然骨折了,但是只是轻微的,并没有说一辈子不能不能动刀弄舞,吃喝拉撒。”
我舒了口气,愧疚的低下了头。
还好,只是轻微……
白医道:“这段时间,他不能随意触碰任何东西,就算是用膳也不可以,钟小姐你找几个细心的下人好生照料一段时间,等过了这段时间,就可以自理了。”
我着急,道:“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
“那这要看白公子的恢复情况了,再具体点就是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
“这般长!”我道:“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白医淡淡道:“并无它法。”
我咬了咬嘴唇,看着眼前因我而受罪的男人,心里对之前的讨厌和恨渐渐消磨。
其实那日,他也是为了我吧,如果他没有吻我,也不知道我会看到怎样不堪的一幕。
可是我竟然歪头斜脑的怪罪他,还以为他是故意坏我名声让我狼名虎籍的。
如今竟是最对不起的人。
白医离开后,我一直在他身边守着,现在也就只能用最快的方法让他康复,让自己赎罪了。
那么……这段时间就由我来照顾你吧,白衣。
黄昏,我趴在塌边,一抹暖晕映在身上照醒了我,我晕乎乎的起身,伸了个懒腰,刚睁开眼就看见白衣满脸笑意的瞧我。
我雀跃,道:“你醒啦。”
他淡淡的“嗯”了一声,笑道:“你打算让谁照顾我这一阵?”
我刚睡醒脑子有些转不过弯,假装思考了好长一段时间,道:“我吧,毕竟也是我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当然是我!必须是我!如果不是我那我肯定堵一辈子这个梗!但是我可是钟溶汐啊,这种照顾别人的话怎么能一下子说出来,那可多没面子。
“我心甘情愿的。”白衣看了我一眼,道:“你知道,我心悦你。”
我顿了顿,被这突如其来的坦白有些茫然,我知道他是心甘情愿的,可是我让他受伤可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低头掰鼓手指头,舒了口气,道:“我……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一遍了,我希望白衣能够清楚。
“我知道。”声音越来越低,“可我就是不相信你不会爱上我。”
我道:“可是小离子追了我十六年都没有成功,你觉得……你有可能吗?反正我对自己没信心。”
他道:“我对自己有信心就够了,喜欢你,不关旁人的事,也不关你的事。”
我尴尬的笑了笑,不知如何是好。
他如今这样一说,那我以后照顾他岂不是很尴尬,时长数月啊,每天我都要面对他。虽然已经被告白过一次了,可是我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舒坦。算了算了……这里可是钟府,没什么好尴尬的,这以后就把他当成救命恩人看待就好了。
回到汐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好好的清洁了下身体,要知道我的身上还有好多鸡蛋液呢。我收拾了几件衣服,赶着去白衣那儿。钟府本来就大,再加上白衣那里是贵宾区,图的安静,与我这鸡犬不宁小苑子相差好几里呢,我是去照顾白衣,但总不能每天这样来回跑吧。
落落拉住我,自责的看着我,道;“对不起啊小姐,我不是有意瞒着你外面的事情的,今日我太贪玩了,没想到你会出府,还让你受了惊吓,又害的白公子受伤。”
我笑了笑,这件事一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怪过落落,我知道她不告诉我是我了我好,怕我收到打击,毕竟前几天我实在是太丧了,一副病殃殃的模样,连我自己都觉得的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虽然它发生在我的梦里,还让我在现实痛苦的经历了一次,给我留下彻骨的记忆,但毕竟,人还是要活的不是吗,这个道理从我去找魏似弦他们茶饭不思的那一次,从白衣救我差点失去一条胳膊的这一次,我突然明白,原来人不仅仅是为了尊严而活,也是为了那些爱你,担心你的人而活,更是为了证明看不起你,让你失去翅膀的人而生,不是吗?
我拥抱落落,冲她笑了一下,道;“谢谢你。”
落落卡在原地,有些意想不到,可能等她缓过神来,我就已经在朝月阁的路上了。
我收拾好东西,坐在塌上出了神,我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就只是单纯的发呆,看着白烛被火光一点一点的烧成另一个白烛,只是形状扭曲罢了,就像我自己,成精腰直的像是白杨,现在经过世事无常变迁,大风大浪开始变得开始若似从心所欲般的老人。
看白烛的余光中一抹影影绰绰的白影映在眸中,我抬头看了一眼,白衣男子般亭亭玉立在眼前,我有些愤然,赶紧让他坐在塌上。
我道;“还是很疼吗?”
他委屈的点点头。
我自责的低着头,喃喃道;“对不起啊,都怪我,让你变成这副模样。”
他用手抬起我的脸,声音轻盈又温柔道;“没事,这件事其实也有我的责任。“
我最害怕我有愧的人像我道歉了,如今白衣这一说,我这心里就更是加了几百两黄金一样,很是沉重。
我又一次地下了头。
白衣起身,突然蹲在我面前,我与他的身高相差好多,所以他蹲下,我坐在塌上的高度相差无几。
白衣伸手,将手放分叉在我的嘴边,往上顶了顶,我的嘴角勾成了一定的弧度。
他笑道;“这才是我认识的钟溶汐。“
我呆滞在那,怔了一下,他的手好温暖,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可我是个大冰块,怎么捂都捂不热,就算捂热了也是一滩死水。我颓然道;“强颜欢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