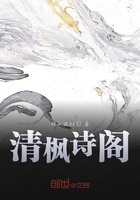严家的大宅修在长安城的中心地带,周围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大门在不超规制的范围内一家修的比一家气派。严家虽然算是商人,宅门也修的比一般的县衙大门要宽些。
严彪带峨眉一行人进门时,少林的僧人已经到了,一共有也就三人,一个老者带两个中年僧人,与峨眉一行三十来人一比显得人数稀少许多,好像不怎么重视,但慧刚却见过那为首的老者,是现任少林主持普善的师弟普慈,也算是少林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
普慈正在与一个矮胖子交谈,两人看到明光进来,都转身迎了过来。
“阿弥陀佛,贫僧路远,到的晚些,还请师太见谅。”
“哪里哪里。”
“两位看来认识,那我就不多介绍了。”
“这位是?”
“我就是严大,开这小镖局,出点事还烦劳二位跑一趟。”
三人寒暄一番,严大稍微压低了声音说:
“时间紧迫,咱们还是进入正题,还请两位随我到里面去一叙。”
他说着两位,普慈却带着身后的两个僧人一齐进去了,明光一看,便对慧刚使了个眼色,叫她也跟上。严大脸色不善,却也无法,带着五人到了一个议事的地方。
“各位都是自己人,我也就不说废话了……”
慧刚听严大语气不善,竟是要问罪的样子,当即警觉起来。
这时突然一个小厮低着头来奉茶,打断了严大的话,让他脸色又难看了几分,更巧的是不知是不是太过紧张,那小厮奉茶的时候手一抖,不小心把茶倒在了桌子上。
“这,这。”小厮慌了,连句谢罪的话都说不出,只又用袖子去擦,严大当即眉毛倒竖,抬手就想打人。
这时明光师太却突然忍不住笑了一声,用袖子掩住了嘴,严大一看,就像泄了气一般,最后只得挥挥手让他退下,室内本有一股压抑严肃的气息,这一来,也随严大一起泄了气。
直到小厮下去,严大才继续说道:
“两位应当也知道事情原委了,鄙人有一不成才的弟弟,唤作严二,小时候不爱读书,就被家父送去河北狮子门学了几手三角猫的功夫,回来替我走镖。”
河北狮子门是个小门派,慧刚只知道那派和河匪有关,上不了台面。
“前几日,家弟走镖时遇上几个没长眼的小贼,劫镖不成,放火烧了镖车,偏家弟是个直性子,怕东西有什么闪失,就一点一点打开了查看,结果翻到一个油纸包的时候,翻出了贵寺……”严大看向普慈,“曾经对外宣称是被毁了的金刚宝经。”
慧刚这一听才知道,原来严大把少林叫来不是为了求援,而是为了问罪。少林十年前广邀天下豪杰去少林赏经,后对外称那《金刚经》被毁,现那《金刚经》不但重现江湖,严二还因为走露了《金刚经》的消息被灭门,这怎么想,都和少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普慈微微一笑,低头不语,就像严大说的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一般。
严大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后来家弟就被杀了,连着全家十六口被灭门,连我那黄发小侄儿也没留得性命……”
严大欲继续说,却被普慈打断了,他向前探身握住了严大的手说:“善哉善哉,不知严大掌柜家里是否无虞?”
“我家没事。”
“哦,那便好,那便好……”
“好?可是我那胞弟……”
“哎?”明光又一次打断了严大的话“那这就奇怪了。”
“此话怎讲?”普慈接过明光的话头问道。
“这贼人若是为了抢经,谋害了严二兄弟也就算了,若是为了封锁消息,那便不该放过严大掌柜……”
“师太还想我严家三代一个不留不成?”
“掌柜勿恼,咱们是在讨论这贼人好抓他。”普慈说道。
严大哼了一声,不说话了。
明光继续说道:“你说这《金刚经》本是少林的镇寺之宝,少林乃武林至尊,我峨嵋历代掌门苦心经营数年却连望其项背都不敢说,若是真有贼人敢对这《金刚经》下手,必是有十足的把握和大破天的胆子,这样的人,却没有为害严大掌柜,说不通啊,说不通……”
“那师太认为……”
“贫尼拙见,贼人是不是为了《金刚经》尚且未知,镖师走镖向来容易得罪恶人,要说是是巧合也未必说不通,又或者是因为严二兄弟在开货物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别的东西,这才遭致身死……”
“砰!”严大听不下去了,一掌拍向桌子。“师太和大师唱的一出好戏,把家弟的性命当作什么了,少林十年前明明宣称是毁了的经书,现在让家弟身死,难道少林不该给个说法吗?”
“这……善哉善哉,贫僧这倒有点听不懂了,难道这说法,不该是抓到那贼人,再由他给严大掌柜吗,师太,您说呢?”
“贫尼也觉得这样更好。”
“不过严大掌柜既然这次求助于少林,少林自当倾力相助,帮严大掌柜查清事情真相,还严二兄弟一个公道。”
偌大的内堂,突然只剩严大喘气的声音,静的令人心悸。
“严大掌柜还有什么顾虑吗?”
普慈发话,听语气竟是要走。
严大的脸青一阵,红一阵,气越喘越粗,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普慈看严大不说话,慢慢起身,却不知怎么的一个趔趄,双手撑在桌子上。慧刚看他撑的缓,只道是岁数大了,久坐头晕,没成想普慈不知使了什么柔劲,看起来是轻轻一撑,那桌子竟然从中间断了开来。
“哟,严大掌柜手劲不小,一掌竟将这红木桌子拍断了。”
普慈说完,便带着两个僧人径直出门走了。
“走了,你的师兄妹们还等着。”
明光说完,也跟着普慈走出门去。
慧刚回头,只看到严大掌柜手捂胸口,五官皱在一起,两行浊泪缓缓流下,天色渐晚,他弓下的身躯仿佛慢慢没入堂内的无边黑暗中,显得无助而绝望,只有那差点被他掌掴的小厮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将他慢慢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