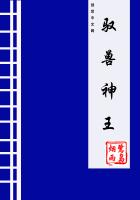小学毕业试后,童雨一点玩的兴致都没有,他在苦苦等待考试的结果——初中录取通知书。出结果那天,童雨知道自己考了全班第六,但却成了班里唯一一个没有通知书的。班里一些同学虽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他们都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其实考完试那天,那些没有买书的学生就已经后悔了,因为他们听说试卷上有几道题是从那两本教育局编的辅导书上出的,虽然当天文三胜什么都没有表态。
“文老师说有一些题目就是从那两本辅导书上出的,但你却偏偏听信了童雨那个小无赖,偏偏就不买那两本辅导书。”
“妈妈,这事情与童雨无关,是我自己决定的。”
“不要再骗我了,跟我去找童雨算帐!”陈雨涵的母亲一边说一边用手牵着她的女儿往门外走,她们到隔壁村夕阳谷要走好长一段路。
卢世杰家里的客厅空荡荡的,里面有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和一个挂钟——桌子桌面是长满白色霉点的,椅子是高低不平的,挂钟是天天要拧发条的。“考进三中那个垃圾学校,我打死你,你什么都不学,却跟着童雨那败家仔示威。”卢世杰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给太阳晒得黝黑发亮,两只手强壮结实,上面爆满了筷子般粗的血管,看上去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平时很少打骂儿女,但是真把他惹生气了,他打得特别狠。一旁围观的世杰弟弟和妹妹,身体不停地打哆嗦,眼中充满了恐惧。
“爸,这不关童雨的事,是我自己去的。”
“我告诉你这事情已经传到上头去了,人家是故意从那本资料书上出的,就是要教训你们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要不然来年还有谁会购买他们那些资料?”世杰父亲看着跪在地板上的儿子说。世杰妈妈坐在高低不平的椅子上,左右晃动,她望着墙上长满铜锈的摆钟唉声叹气,那铜钟是他们家最值钱的东西,是卢世杰曾祖父那一代留下来的。突然,她猛地站起来,拉着跪在地上的儿子说:“走,我们去童亮家里讨个公道!”卢世杰死死地钉在地板上,世杰母亲怎样拉也拉不动,然后她转过脸瞪着她丈夫,希望他能说点什么。“孩子她娘,我看这事情就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毕竟是邻居嘛!”世杰父亲劝说。显然,这不是世杰母亲需要的回应,她一面捡起地上的竹鞭,一面抓着他儿子的手,然后竹鞭像雨点般打在卢世杰的屁股上。卢世杰再也忍受不住疼痛,摸着屁股,呱啦啦地哭着站了起来。接着,被他母亲拽着手往童雨家里去了,后面还跟着他的弟弟和妹妹。
在周子明家里,他们家更穷,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用“家徒四壁”一词形容最为恰当。“子明,你给我在你死去的父亲面前跪下。”一个年过四旬,身体微胖,嘴唇发黑的妇人看着墙壁上的黑白画像泪流满面地说。那妇人的眼神异常忧郁和迷茫,夕阳谷的村民都叫她李大婶。画像里那个男人就是她死去的丈夫,那男人身着中山装,梳着一个三七分的发型,头发乌黑而有光泽,脸型清秀,嘴巴露出一丝和善的微笑,从远处看画中人只有三十多岁,如此看来周子明的父亲过世已有多年。
“妈,你别伤心,我跪下就是了。我考了全班第十名,成绩也不差啊!”周子明握着她母亲的双手慢慢跪下来说。
“二狗,你也过来妈妈这里。”李大婶挥手招呼二儿子过来,她二儿子只有六岁,头上长着一颗圆溜溜的脑袋,而最让人惊讶的是他那双硕大的眼睛,那双眼睛远看好像是长在额头上的,眼中蕴含着厚重的成熟,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此时,二狗正拿着竹筒对着火炉大口大口地吹气,他满脸都是黑黑的粉尘。“你曾向你死去的父亲发誓你会考上窦州中学的,但你只考上了镇的重点中学,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父亲交代啊!”李大婶流着眼泪语重心长地说。二狗看见母亲的泪水在溢出,他赶紧伸手去擦拭。
“妈,以后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会考上窦州中学的。”周子明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说。
“子明,你快去童雨家里看看吧!刚刚有很多人就是冲着他去的。”李大婶摸着他儿子的脑袋说。看着两个如此孝顺懂事的儿子,她眼中的忧愁消退了许多,渐渐还略带几丝欣慰,她接着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童雨待你如兄弟,记得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
那些愤怒的人把石头屋围得水泄不通,有的人左手拿着通知书右手拉着儿女,有的甚至还拿着棍子在院前大喊大叫……开始的时候,童雨的家人坐在厅里,一直保持沉默。其实,这时候童妈也没指望他的丈夫能站出来,她认为童亮一直没有变,还是缺少勇气回击批判。她还清楚地记得,那年镇公社前围着一大伙人,众人中间站着一位老人,老人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站在一张桌子上面。那些人群情激愤,叽叽喳喳地指着老人骂得多难听就有多难听,更有甚者往他的身上吐痰吐口水。后来,阿莲嫁到了童家,才知道那位老人就是她丈夫的爷爷,他是给村长何闻天陷害的。当时批判现场童亮竟然也在,那时候他已经十六岁了,但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而是在人群中擦着眼泪痛哭。
正直的童钢老人打开了铁门,让他们进院子休息,可那些人渐渐失去了理智,骂的话也越来越难听,而一旁的孩子则低着头,用手擦着溢出的眼泪。童妈终于忍受不住了,她就冲了出去,走到龙眼树下面,坐在大理石凳上。那些人也跟着童妈转移了阵地,童燕也跟着那些人走了过去。“燕燕,你年纪还小,不懂得是非黑白,你快回屋里,和你爷爷、你爸爸待在一起。”童妈摸着她女儿的脑袋吩咐说。待女儿回到屋里,童妈就在那群人面前站了起来,她站在大理石凳上,看上去她给那些人高出一截。
“我们家童雨有那么大的能耐吗?能让你们的儿女都听他的?”
“你们干嘛了?难道想拆了我们家不成?”
“我的儿子用不着你们教,等他回来,我自然会修理他。”
……
从下午四点一直围到晚上八点,看到天空乌云密布,像快要下大雨了,他们才肯散去。
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街道,一阵风扫过,几张破烂的报纸被那个人的脚挡住,被风刮得呼呼乱响。他有家,却不能回,因为他觉得没脸面对他的伙伴,他的同学,还有他的亲人。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大的罪人,最坏的坏蛋,他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天空的乌云越积越厚,越压越沉,像一个漆黑的圆盘,要把地面上的一切都吞没似的。“轰——轰——”几声雷鸣过后,天空就下起了倾盘大雨。剧烈的阵风把雨水拉得长长的,撞击着街道的地板,还有两旁街道窗户的玻璃,击打声交集在一起,迸发出各种怪异的声音。然而,这一切在那个人的眼中是一种痛快,他激动得站了起来,然后振臂高呼:“老天爷,你惩罚我吧!”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凭雨水泼洒,直到自己倒下去。“文三胜降职,王校长辞职,同学们又考砸了,爷爷……”童雨边想边用手狠狠地捶打街道的墙壁,任凭血水从自己手上,从墙壁上流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童雨觉得累了,终于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在梦中,他看见一个女孩帮他披上了一件蓝色披风,还把她的乳白色雨伞盖在自己身上。
晚上十点,童妈反复在大厅里来回走着,嘴里说着一些奇怪的话,而眼睛一直盯着门外的天空,那天空漆黑如墨,狂风骤雨。童亮和童燕半躺在竹椅上,眼珠跟随着童妈的身影来回移动。童钢爷爷则不慌不忙地旋转着一个带血丝的玉镯,这玉镯他们童家已经传了第五代了。按照规矩,这个玉镯应该戴在他两个媳妇的手上,但由于她们天天要干农活,童钢担心玉镯会损坏,便把它留在了身边。
又过了半个小时,“礑——”墙上的摆钟响了一下。童妈终于按奈不住了,拿着雨伞就要往门外走。童亮和童燕也从竹沙发上坐了起来。“站住,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他做错了事情,他就要承担责任,就要受到惩罚!”童钢老人喝住了他们。其实,他们也十分了解爷爷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比任何人都要焦急,但他又无法抛弃自己做人的原则。
一个小时过去了,暴风雨还在继续。童钢爷爷还是转着手上的玉镯,渐渐速度就不均匀了,时而快时而慢,玉镯光滑的表面反射着屋内暗黄的灯光。
“礑、礑……”墙上的摆钟一直打了十二下。
“快去找童雨吧!”没等童钢爷爷把话说完,他们就拿着雨伞冲出了家门,可刚走出门口他们又折了回来。“爸,外面那么黑,还下着大雨,你就待在家里吧!”童亮站在门口说。童钢爷爷挂上那副旧得发黄的老花镜,然后在微弱的灯光下,弯腰摸索那把奶奶留下来的天堂伞。
“爷爷,外面下着大雨,你还是不要去了。”童燕摇着她爷爷的手说。
“你们都以为我老了吗?走不动了吗?”童钢爷爷拿着雨伞边说边往外面走,右手还是紧紧握着那个血丝玉镯。
“燕燕,你扶着爷爷,快去!”童妈催促她女儿说。
“童雨——”他们挨家挨户去喊,由于雨声太大,他们的喊声根本无法让人听到。于是,他们又挨家挨户敲门,问他们是否见过童雨。有的村民眯着朦胧的睡眼不停地摇头,有的村民故作没听见索性就没有起来开门,还有的村民对他们破口大骂,可还是有一些人加入了寻找童雨的队伍之中。譬如说卢世杰、李大婶、周子明……多年以后,夕阳谷的小孩长成了大人,成人变成了老人,他们也许忘记了许多事情,但有两个夜晚他们一定还记得:狂风暴雨的夜晚,被人敲门的夜晚——被他们童家人敲门的那两个夜晚。
“童雨,我的乖孙,你在哪里啊?”童钢爷爷老泪纵横,大声呼唤着,他的声音低沉沙哑。村民听见了,没有不感动的,纷纷要去搀扶他,但都被他拒绝了。“燕燕,你留下来陪爷爷走在队伍的后面好吗?我们要到中乡镇找你哥哥。”童妈弯腰对女儿说。天空依然那么漆黑,肆虐的狂风夹带着豆大的雨滴,扑打在雨伞上,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妈妈,别丢下燕燕好吗?我好害怕!”童燕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
“怕什么,天塌下来,有爷爷帮你顶着!”童钢老人看着孙女笑呵呵地说。
天空微微泛白,还下着蒙蒙的小雨,中乡镇街道的雾气很大,那雾气泛着路灯暗黄的光。
“有没有看见童雨?”童妈焦急地问周子明。
“我们几乎走遍整个中乡镇街道,还是——没有找到童雨。”周子明低着头,声音越说越小。“血!童妈你看地上的血!”突然周子明激动地喊了起来。童妈也低下了头,望着地上的血水,心头一震,差点晕倒在地,幸亏一旁有童亮搀扶住。
“你们看,街头那里!”李大婶用手电筒照着街头,所有人都往那个方向望了过去,只见手电筒发出的光柱穿过滚滚白雾,最后落在一把白色的雨伞上。一把白色的雨伞,下面躺着一个人,那血水便是从那里流过来的。他们撑着雨伞,越走越近,每个人的脚步都是那么沉重,好像大家都在刻意放慢速度,也许他们害怕那一刻的到来。童亮搀扶着妻子步履蹒跚地走着……“礑!”童钢爷爷的玉镯掉落在水泥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但他没有倒下去,依然默默地站着。“童雨,我的孩子!”悲痛的声音打破了街道的沉寂,童妈推开她的丈夫,不顾一切地跑过去,积水的街道留下一条长长的水痕。童妈弯下腰慢慢移开那把白色雨伞,突然一股热气向自己涌来,童妈一屁股坐在地上。马上,所有人都停止了向前靠拢的脚步,街头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
紫色的脸蛋,右手的伤口堆积着暗红色的血块,血块间的缝隙还渗着淡淡的血丝……童妈迅速从积水中蹲了起来,她双手把童雨紧紧抱在怀里,仰天撕心裂肺地痛哭。街头的沉寂再一次被哭声打破,他们呆呆地站在原地,沉重的心已彻底被这悲痛的哭声撕碎。
“咳咳——”童妈隐约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便抬头向四周搜寻,但一无所获。
“咳咳——,妈妈你把我抱得好紧啊!”
“祖先保佑!”童钢爷爷看着手上的玉镯自言自语,仿佛它是一个活着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