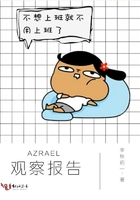陈蔚文
电影永远不能拯救任何人的生活,它不是济世良药,它不过只是一片阿司匹林而已。
——吕克·贝松
白色夹竹桃的汁液
白色,这是种温柔又凛冽的颜色。使人想起羊绒、花朵、墓地、冰雹……,还有日本的唯美主义作家川端康成在1962年说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以及“无言的死即是无限的生”。
生与死,都是白色的。像许多作家一样,川端康成在1972年选择了自杀,他从一端的白色走向了另一端白色。
我对白一向讳莫如深,觉得它有种冒险的成分,我几乎没有白色外套与裙子,因为怕自己会成为显眼的发光体与白色殉葬品。白色中陈藏着一种将人逼向虚无的力量。日本自杀风气素来很盛,不知这是否与终年积雪的北海道,富士山以及它白色的出产:樱花、雪、电影……有关。
《情书》就是部纯白的电影。
恋人藤井树的忌日——当人们要证明一段至爱,通常要借助死亡的力量来协助。女友博子找到了他旧时的通讯薄,按照那个地址,博子发出了一封本该是寄往天国的情书。她并不知道信寄到了与他有着相同名姓的女孩的家。于是她出乎意料收到了回信。这信使一直不敢相信恋人已逝的她愈发相信恋人活着,活在世间某个她不知道的角落。然而,终于还是知道了真相。两个女孩开始了对一个早逝男人的共同怀念。
覆盖的雪,山间行驶的有轨电车,风中的白色窗帘,借书卡以及白色封面的《追忆似水年华》——最初而又戛然而止的爱如同一片雪光,使一生都笼上了一层纯洁的寒意。这是部缓慢忧伤的电影。导演岩井俊二对白色似乎很着迷,他的《烟花》、《四月物语》也都是有银白色泽的电影,东方式的细腻忧伤,像李敖说的:有些冰冷,只能用洁白来表现。
说到白色,还有波兰导演基那斯洛夫斯基著名的“三色系列”中的《白色》,讲述一对不同国籍夫妻之间的爱恨情仇。丈夫卡罗尔是波兰理发师,他年轻的妻子是法国人,卡罗尔从波兰来到繁华的法国,诸事不顺,心理上很受压迫。直到他返回波兰生命境况才渐渐好转,偶然的机会,卡罗尔因炒地而一夜之间成了富翁,不久又当上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总裁。发迹后的卡罗尔决意要征服同他离婚不成而把发廊烧掉的妻子。他精心策划了一个骗局,他对外说称自己已死,遗产留给了她。她从巴黎赶来华沙参加葬礼,并继承了卡罗尔的遗产。“复活”的卡罗尔晚上出现在她的房内,他们狂欢一夜。第二次清晨,她醒来发现卡罗尔失踪了,随即警察赶来,把她作为谋害前夫的嫌疑犯逮捕了……
这部片子不知为何命名《白色》,是因为镜头几次呈现的白色?尤其是丈夫波兰家乡雪地的白,像一床可以遮蔽伤口的白色羊毛毯。但导演更深的含意也许是以白色做为一种嘲谑的“断层”符号。戏讽婚姻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间脆弱的情感积蓄的报复……
电影《白色夹竹桃》也是部白色风格电影,却是另一种白。这是部根据詹尼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1994年,这个短篇小说获得了年度全美最佳短篇小说奖。
坚强的诗人母亲英格里德用她最喜欢的花——白色夹竹桃的汁液杀死了负心男友,被判终身监禁,15岁的女儿阿斯特丽德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被捕。此后她孤苦无依,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在洛杉矶若干个收养家庭之间辗转的日子里,阿斯特丽德明白,如果要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活下去,就必须努力掌握生活的技能,她不能指望上帝援手,她要抛弃所有自怜哀怨,在生活中锻造自己的耐受与品性,学会愤怒与宽恕,学会爱与生存。而母亲在铁窗后面写下的一封封信传递到阿斯特丽德手中,成为她坚强生活的勇气的凭据与支持。
这是一段关于自我救赎的艰辛旅程。导演过《呼啸山庄》的导演彼得·科斯明斯基似乎总愿把更残酷的生活真相呈现在镜头面前,他无意回避或粉饰,无论是残酷的爱情还是疼痛的成长。他身上沾着酒精与药水的气息,用锋利的手术刀把事物暖橙色的外衣一刀划破,露出白色冰冷的内在。这白色是生活里被扭曲的,被侮辱的、被损害的。无论是《呼啸山庄》中漫天弥漫的绝望暴风雪,还是《白色夹竹桃》中有毒的夹竹桃花汁液,都是导演科斯明斯基要给我们看的白色物证:它证明生活的负心与寡情,证明罪与罚,生与死,爱与恨。看这样的电影,使我们感到寒冷,人世炎凉并且——振奋,是的,振奋!像少女阿斯特丽德一样振奋!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我们要像兽一般去适应,去争取,去反击,直到暴风雪或者夹竹桃汁液都无法消灭掉我们。
蓝色在风中
蓝色,这充满神秘寓言的色彩让人联想海、信仰、马汀尼酒、爱情……还有我喜欢的美国画家,金属器具商人的儿子,温斯洛·荷马。他迷人的代表作《八只船钟》如同部壮丽的海洋史诗,使人对愤怒的蓝咆哮的蓝有了惊心体会——事实上,荷马一直在探索海洋题材,为此他48岁时离开繁华的纽约,在岩石嶙峋的缅因海岸盖了小村舍,在这个小渔村呆了26年,直到74岁去世。他种蔬菜花木,烟草,修理房子,除了用来描绘蓝色海洋的时间,他像个勤勉的体力劳动者。如果要以色彩命名画家,荷马当然是蓝色的,就像米勒是伴随晚钟的麦芒色,梵高是阿尔的金黄,高更是土著的褚红,德尔沃是月光的银白一样。
少女时期,我对蓝的迷恋无以复加,似乎是因为一个单词blue flower(蓝色花)爱上的,觉得它象征了优郁,优雅,浪漫——这些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品质。
总是留心蓝色的衣物,不仅因为它的气氛,还因为康丁斯基说,蓝色对于身材的视觉压编效果比紧身内衣还好。也仅是一个阶段,过了青春期,对色彩的接纳宽容起来,只要不是太出格都敢披挂上身,想趁着三十未到赶紧穿尽世间百色。
对蓝色调的电影却始终专情。
因为韩星元彬的俊朗有了把《蓝色生死恋》看下去的冲动,那支动人的主题曲使内心百转千回:那是还未稀释的爱情带给心灵的伤感,像第一次乘上呼啸的火车,心口发紧地颤栗。看这部片子的过程使我看清自己尚未“成熟”或说深沉的现实,因此还会为这样的青春片激起涟漪,但我宁要幼稚的激情也不要麻木的深沉,前者使我觉得自己还有生机,心头还未荒草丛生。
《蓝》是导演基耶洛夫斯基的“三色”中的另一部,此片获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朱利亚·比诺什饰女主角。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她痛失丈夫爱女。未死成的她卖掉了房子汽车,搬到一个陌生地方。她随身只带走了一只蓝色灯具:无数蓝色玻璃球悬吊着,凄美空灵。
影片就在这样的抑郁伤感中行进,蓝色溅溢四周,文件夹、糖块和蓝色玻璃纸、蓝色幻境、蓝色泳池、蓝色音乐——然而她忽然发现丈夫生前有情人且已怀孕,她的痛苦一下失掉了凭证,她终于能开始新生活了,但很难说这是否是种解脱。
蓝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堪,当它正忧伤地充当着爱情与怀念的幕布,却不小心滑脱下来,落出了背弃与不忠的真相。蓝色中,女人经历了世间最复杂的情感,是该接着爱,恨还是宽宥?蓝被撕成碎片,凝结成粗砺的海盐,粗暴地揉搓着女人痛苦的心。这就是世间情感啊,像鸠一般的止渴又像鸠一般地毒。
有一部电影,却完整地还原了蓝色深瀚的本身。
是英国人德里克·加曼拍的电影《蓝色》。记录他患艾滋后的最后岁月。电影中,整个银幕都被蓝色所充满,背景是音乐和嘈杂的医院声,喧嚣的海水声。没有语言,没有对白,只有蓝。拍摄这部电影时,加曼几乎已完全失明,他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在艺术手法上,“他拒绝表现物象、景致和人体,把电影的形式推到极致。蓝色,是裹尸布的颜色,是沉默、受难的颜色,却也是天空、大海和飞燕草的颜色。”加曼就在这片广袤的蓝中向生命做最后的答辞与谢幕。
他说,“我献给你们这宇宙的蓝色,蓝色,是通往灵魂的一扇门,无尽的可能将变为现实。”
这位长于印度空军基地的画家,诗人,电影导演,独立制片人兼同性恋权利活动家,最终死于爱滋病。早在1986年,他发现自己染上爱滋病毒,他勇取地向世人袒露了这个消息。接下来的日子,他拍了许多油画般精彩的电影,在海边核电站旁买了一栋渔民小屋,命名之为“希望之屋”,他每日锄地拔草,将原本荒地土屋变成了美丽花园。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主动要求医生停止用药,而他双目已完全失明,皮肤肌肉都在脱落,不过加曼的尊严没有受损。潮润的蓝包裹了他。受难的尽头是宁静无憾。他这一生已做了许多事,比许多人几生加起来还要多。
一部《蓝色》是他最好的安魂曲。
红色年代
今年有种粉粉的肉红简直流行到泛滥地步。这颜色不难看,让人想起十七八岁的肤色,不过,用“粉粉的肉红”形容多少让人想起东来顺羊肉片,那么叫它“小桃红”吧,春天山上乍放的桃林,远望是如粉如雾的蓬松的红。
说起来,红和女人很有缘。童年的粉红,青春的水红,出嫁的大红……现在穿大红的女人是非常少了,那天在网上看到潘红穿大红宝姿裙子的图片,绸缎无袖礼服式衬得潘虹很优稚,然而——有一丝小小的凄凉。单身的潘红毕竟是老了,不是那个《人到中年》和《末代王妃》中的潘红了,她身上那一袭大红使人想到火焰最后的燃烧。
张国荣有首歌《红》,是他自己很喜欢的:红像蔷薇任性的结局,红像唇上滴血般怨毒……或许红像年华盛放的气焰,红像斜阳渐远的纪念……他主演的电影《红色恋人》的一张海报上写:红是爱情惟一的原色。
一直觉得红——这色彩与女人的命运有种潜在的秘密关联,而在电影中,它更经常与国家、革命、战争发生关联。我最早关于电影的红色记忆不是《闪闪的红星》,也不是《红色娘子军》,而是惊悚的《画皮》中的血。那时大约六七岁,把魂都快吓没了,可能就此落下了爱看又怕看恐怖片的病态心理。
没有比苏联战争电影更能说明红色的了。在那些红色影片席卷时,我还远未到被革命精神感召的年龄。我只依稀记得《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的台词,他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记住这句台词不是因为它兆示了革命的美好前景,而是因为“面包”这个词语,在以馒头包子为主要早点的年月,诱人的面包使我垂涎欲滴,十分向往。当然,这句话后来早已超越了对一种点心的期待,而成为一句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人生励志格言。
仅从那些片名你就能感受到那片壮丽的红色:《列宁在1918》《苏维埃国家》《乌克兰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联好像是战争电影的故乡。这些电影全都燃烧着熊熊的革命火焰,如果我是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子,我的理想一定也是像斯坦贝克的小说《月亮下去了》中的诗人中尉托德一样,“他希望能够战死在战场,让义母站在他背后流泪,领袖呢,在这将死的青年面前,显得既勇敢又悲切。他常想到他的死……舞台后面响彻着瓦格纳音乐中的隆隆雷声。他连临死前的遗嘱都准备好了”。
是的,在那个被红色电影燃烧的年代,一定有无数血液沸腾的年轻人像托德中尉一样,随时准备为国家献出自己,尔后在每年的祭日,有位娜塔莎那样的清秀姑娘含着泪水来到他葬在白桦林的墓碑前,献上一束洁白雏菊。
《静静的顿河》是另外一种红色,它不图解革命,而用史诗般壮谧的画面表达革命、情感与人的关系。这样的电影还有《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夏伯阳》……它们展现的革命构成不仅仅只有武器、鲜血、破碎的红旗、砍翻的战马,还有泪水、尊严与爱情。
一位六十年代末生的朋友最想去的地方是俄罗斯,他想看看红场,圣·彼得堡,看看那些凝重的灰色城堡,山楂树白桦林。他是看那些红色电影成长的,那些澎湃的,俄罗斯式的情怀植入进他和他那代人的灵魂里,以及还有那些优秀的片子,《山村女教师》《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伴随着雪地里拉响的手风琴和卷舌音的忧郁歌唱奠基了他们一生的审美。
在网上社区看到一篇谈苏联电影的文中写,“俄国的电影里有卑微如蝼蚁的小人物,但却从来没有轻薄如纸的人生。”是的,这就是沧桑而深沉的俄罗斯,被烈性伏特加浸泡的民族,西伯利亚的冰雪也不能使之冷却。但是,苏维埃失去了,托尔斯泰,普希金死去了,苏联成为了“前苏联”,壮烈的卫国战争和一个时代的信仰永远成为红色回忆。
据说那些昔日的苏联影星晚景不少都很凄凉。《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在现实中孤身住着简陋的两居室,梦想是买一部录像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金黄短发、翘鼻子的女中士基里扬诺娃不得不在55岁的年纪赚些钱贴补家用,为记者帮她清洗了一床客厅地毯她高兴不已;在纪念卫国战争三十周年拍摄的电影《解放》中饰演苏军大尉的男演员在屋内喝着闷酒度过了他的六十岁生日……如今的苏联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也已式微,卖座率与名声远不及日韩片。尽管如此,那些电影曾经的辉煌仍然在一代人心上镌刻,还有那些深情的电影插曲,一响起,在对应代际的人心中,等同于大地6级以上的颤栗。
我没能经历那个红色时代,我看过的台港片和欧美片远多于前苏联片。我的不少泪水都是为都市爱情流的,而不是为祖国与革命,即使偶看战争片,也多是美国数码制作的炫技大片,那里只有令人心悸的最新式武器最超前战术,但是,没有忧伤。
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这一代信仰脆薄的一个原因?我们没能领受红色的激情施洗,只在欲望越来越纷扰的年代筑起小庙,供奉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快乐与情感。
有时会揣想那个红色年代,人们走在街上,身体被一些崇高的情绪鼓动着,涨满着——读书时我住在省委大院旁,不止一次碰过有人哼着革命歌曲从身旁经过,有次是位三十岁左右,衣着简朴的女人,她边骑车边一路唱着“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她面庞发亮,嗓音清脆,我当时是个内向腼腆的女孩,对她的歌声感到非常吃惊!她怎能如此放声歌唱?她一路唱着过去了,像一切胸怀革命理想与阳光的人。我一直记得她的样子,那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人生状态!饱满,激昂,不为任何磨难折服的意气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