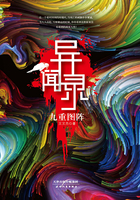“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哦,太遥远了/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一切全是为了另一些季节的孤独。那些数不清的季节和眼泪/它们都去哪里了?/我们的影子和夜晚/又将在哪里相逢……”
——柏桦《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在一个青花瓷筒中,装着十几卷画。有张春天景物的水粉写生,是Z画的。我喜欢那种静谧如米勒的《晚钟》般的调子,向他要的。画的下方有三个字母,他名字的缩写。
Z,我毕业那年夏天在S大的画室认识他,高挺而纯朴的一个男孩。他从一个小镇来,没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因为热爱画画,在一些院校的画室游荡(艺术院校的画室那时宽松自由,各路美术青年们来往穿梭)。
Z是有天分的人,画得很不错,他说他最喜欢的画家是米勒,一个诺曼底农民的孩子,一个在痛苦悲哀中寻找灵感的伟大画家。
Z比我小半岁,同样的年轻而敏感,我们除了彼此名字及一点点基本资料不知道更多,也从未问起。
在画室,我们很快熟了,Z帮我钉画纸,还帮我削了一盒铅笔,他削铅笔的手艺近似于一种艺术。每天晚上,我们和一些画友聚会在S大那间混合着颜料与调色油味的四楼画室,屋里响着齐秦或其他歌手的歌声,Z总是用好听的声音和着,一句歌词都不错。
我们中有位画得最好也最沉稳的女孩L,虽然她心气很高,但她对谁都谦和有礼,我们也都很佩服她,包括Z。Z总是向她讨教画技,L对Z也很好,时不时从家里带些吃的来,有次是滚热的萝卜馅煎饼。
有人开始开Z的玩笑,和L的。当着L的面不敢,觉得很冒犯她,L是那种不喜欢别人拿这事开她玩笑的人,而且L告诉过我,她暗恋她一位师兄,好几年了,从未告诉过他,毕业后他去了北京,没了联络。
L说她时常幻想在北京的街道(或胡同)突然邂逅他,那将是多么激动美好的时刻!尽管知道L的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开L与Z的玩笑时,我仍然心情复杂。
7月是我的生日。那天去画室我并未提起,晚上出来走到湖边,Z像不经意地想起什么,他说,给你,借着路灯我看清是盒碟,张国荣的,我曾在画室说过喜欢他。其实只是一张CD,但我忽然就有点别扭,我看了他一眼,Z说,你看我干嘛,又不是偷的,逛书店看到顺手买的,要不你请我吃刨冰?
Z这么说的样子很轻松,但我还是觉出了他的紧张。我想,没错,只是他顺手买的,它甚至算不得一样礼物,可内心,我知道我希望Z记得我的生日。空气闷热得像能拧出水。
一段时间后,画室沉寂下来了。深秋来了。
美院高考已结束,画室暂时静了下来。画室的一对恋人刚分手,平日挺外向泼辣的一个女孩晚上常跑到直廊掉眼泪,让人觉得心情黯然。
再就是画室开始从上届传一个凄美的鬼故事,说前几届有个美术系女生因为失恋跳楼了,有次,一个男生因为不愿去看电影独自在画室画画,他画的是一个书店老板要的一组玫瑰的油画。正画着,忽然发现身旁有位白衣飘飘的清秀女孩看着,那男生吓了一跳,但也有几分高兴,同她搭话她只是那样冷冷站着,不作一声。学校电影快散场时那女孩转身走了,轻巧地像踩在云上。那男生遗憾而又懊恼,还不知道她是哪个系的呢!正惆怅着,忽然惊出一身冷汗,怪不得刚才总觉哪儿不对,那女孩分明一袭白裙——天哪,正是三九寒冬,他还裹着军大衣呢。
这个故事就这样在S大美术系及美术系以外流传着,其实谁都知道那个叫李玫的女生自杀是真的,其它都是虚构,但在深秋的夜晚这个故事总让人不寒而粟。它让人觉得青春脆弱得像踩在一根琴弦上。后来看陈果的《香港制造》,里面那个一袭白裙为失恋跳楼的年轻女孩让我想起那个叫玫的女孩,唉,青春是美好的,可同时也不堪一击。
画室只剩下L、我和不多几个人,L想出国(或至少去北京)深造美术,我是因为无聊。Z也不大来了,他在一个厂区子弟小学找到份美术教师的工作,学校宿舍离S大很远,骑车大概要40多分钟。
有晚从画室出来,刚到校门口,看见Z骑在车上,一只脚点着地笑望着我。黄色的路灯光晕自他背后升起,我忽然一下慌乱起来,说,你等L啊,她马上就出来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明明知道L比Z大好几岁,他们间并没什么。
Z的笑一下有点凝固,我们推车走着。Z的手里拿了两听健力宝,他递了一罐给我。我不停说着,都是些拉拉扯扯的废话,生怕会有停顿,会有让人心跳的危险在空气中散布,而我,一切尚未准备好。
为了不绕个大圈,我们把车提过马路中的围栏。Z一只手就把我的车提了起来,轻快地像提了个空旅行袋。皮夹克混合着他身体的气息弥漫过来,他的身影在夜色中那么年轻,那么有力,在我日后的回忆中一遍遍被定格放大。而我当时只想着怎么回避——那时心理真是不可理喻,在无人处幻想一百遍的情景一旦在生活中遇到,自矜却本能地胜过一切,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无心,没想法,纯洁又凛然。
快骑到我家时,我像表明什么同时又装着无意,说,你以后别来了,那么远,不方便——我希望他来和希望他不来都是真的。我说的不方便一定让Z听出了不止是路途上的含义,健力宝罐被按得“啪”一响,一切静默下来。
那个晚上以后,我再也没见过Z。
过了几年吧,无聊的办公室上午,无聊的茶和报纸中,我忽然那么深地想起了Z,思念像一阵强烈的虐疾,没有任何预兆地来临。我打到114查到了那个厂区小学的电话,打过去响了好一阵,一个声音粗哑的女人接了,我问她Z在不在,她说什么,话筒里电流干扰声很大,我大声说,Z……Z在吗?她又问了几遍,不耐烦地说,没这个人。怎么可能呢?他离开了吗?话筒那头仿佛是联系Z的唯一线索,我竭力想抓住可不知对“没这个人”还能问些什么。电话断了。
一直到茶变得冰冷,我在想着Z。
有次在画室时他说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呆一辈子,除非……,我们都笑他,除非什么?Z不肯说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他笑起来很好看,发着光的年轻俊朗。Z走了吗,他没找到自己的“除非”?
那个晚上我想我是自私的,深秋的寒气里,Z来回骑了80多分钟路途我却只给了他伤害,我明知道Z比我更敏感——他从一个临水的小镇只身来到城市,除了对绘画对人生的热情一无所有,而我有稳定的工作和在城市的家庭。但天知道,我当时说“你别来了”,不仅仅只是回避或出于矜持,在内心我或许藏着另种渴望,我渴望他反对我,仍然坚持在S大夜晚的门口出现,但我不应那样去试他的,他在这座城市的情感外壳本来脆薄,一点外力便使之破碎了。
Z的那张水粉画几个朋友看了,说不像早春的写生,是的,画面那座灰色老桥和淡如轻烟的调子都隐藏着点忧伤——可那才是真正的春天吧,冬的寒意还未完全褪去。米勒说,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愉快的事物就是宁静与沉默。春天并非一开头就生机勃勃的,因为带着寒意才愈分明,而一段情感还未来得及展开就结束,才愈让人怀想。
L没有出成国,去了北京。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去北京的每条街道与胡同邂逅师兄,无论怎样,即使遇见也一定没故事。因为听说她到北京后很快结婚了,对方是外语学院的德语老师。
一株不起眼的小麦终于和一棵树比肩了,这需要的何止是勇气?简直是谋略,是定力,是智慧。小麦终于守望到了她的收获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