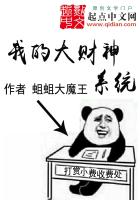“Te amo,Mi amor。”是韩梅梅在出彩艺术节后,全校学生请求她教的一句西班牙语。那时,整个学校都在崇拜她,像仰望古老的女神一样仰视她。没有了初中的疯狂,却削减不了韩梅梅一丝的魅力。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尽收在所有人的眼底,每个人都想和她成为朋友,她却礼貌的和所有人保持着基本的距离。她有心事,只有我能看得出来,特别是在花琦无意间告诉了我她更多的过去,所有的点全部连起来了。我知道,她的这个心事和谣言里她的男友有关。谣言就像人们手里的一捧沙,总以为没有伤害的扬出去就可以创建一个‘欢声笑语’的世界,世界是有了,可生活在里面的人们全部都在用力揉着红肿的眼睛。花琦听了我的劝,回校后就和对象分了手。没了那层保护,她赤裸如初生儿,被人们包裹在谣言中卷来卷去。由一变二,由二生四,直到把她说成贫瘠的沙漠才罢休。有些学生恶霸会趁着人少去她的班级,在黑板上用白和粉色粉笔画出两坨倒立长着眼睛的山峰,旁边落款‘花琦’。陈子鸣知道后,立马张罗了一大帮‘朋友’到十班门口准备来场世纪之战。当所有人都有参与,他能做的只有杀鸡儆猴,挑了两个柔弱的懦夫,但被韩梅梅拦了下来。她告诉陈子鸣,要动手就一个都不能落下。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的神策之一,化干戈为玉帛。最后,那场斗争没机会列入史记。但陈子鸣的声势警告起了作用,之后就没再有人去骚扰花琦了。这本应该是个圆满的结局,偏偏她和她的前任又一次同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她前任脸上不多不少与之前相仿的抓痕宣布了这场扭曲的复合。没过几天,花琦换了部新款的三星w579手机。她不时的把新手机握在手里,慢悠悠的朝着顶端走。看见她的样子,我好像看到了所有结婚后恐慌母亲的形象。她为什么又走回之前的墓穴,是因为只有那里安全吗?安全的定义她是否了解,有人跟她讲解吗?我没有答案。
“你能认真点儿么?全班就你自己不会,还好意思愣神儿!”
操场上总是放着国歌的大喇叭,在放着‘中国话’,里面扁担板凳的说个不停,俗话说不怕别人会绕口令,就怕会了停不下。前一阵萌萌班级里掀起一波‘黑灰化肥’潮,每次我去看她都会被她喷的胳膊溻湿。
初晨的露水不紧打湿了地上的青草,还打湿了我踏在上面的白布鞋。一滩半荷叶形水氲开在脚尖处,孤零零地没有一朵荷花在上面。
“跟我念,Te a,哎你看,门口那儿是不是妞儿。”
我穿过操场上星点的人头望去,确定她也看见我时,招了招手。
“还不嘞你啊,从你生日后你俩就一直这样,咋地了也不说,还当不当我是哥们儿了。”陈子鸣撇嘴赌气,怪象欧阳锋在练功。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疑惑,除了韩梅梅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啊……听妞儿提过一次,就记住了,你生日太好记了。你还没说你俩到底咋地了,学校里传的是真的么?她真有精神病啊?”陈子鸣用手指了下头。
元旦开学后,韩梅梅多休息了一个月,谣言又起了一条,不过这条谣言的细节细微的可怕。传她回国就是为了找个大款,帮她妈筹钱盖楼,还有一个版本和这个相差无几,就是她们娘俩在美国早就破产了,她妈傍的美国老头把她给踹了,像所有的华人实在混不下去才回的国,然后找她弟装成华裔富商,到处骗钱,正在建造的大楼已经成为又一个烂尾楼。总之,她妈年纪太大了,当不了邓文迪2.0,所以用女儿作饵入海钓鲨鱼,毕竟她在上海做的就是同类行业。早在她们回国之前,她妈就已经通过之前的关系,勾搭上了一位教育局的高官,所以韩梅梅才能顺利跳级就学市里状元初中。没想到官员的女儿是她班的英文老师,最开始俩人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交锋才开始。最终,韩梅梅以蛇蝎的狠毒咬死了伟大善良的园丁。可她妈欠的债实在多到堵不住,又分别介绍好几个有权有势的男人给女儿。女儿承受不住身心上的折磨,终于疯了。这里面的情和小说‘扶桑’很像,不过不是中国未成年少女偷渡去美国被糟蹋,而是华人未成年少女主动回国给糟蹋。里面说不出的纠缠,就像作者对白人的恨与爱,也像莫言笔下对高密东北乡的情与恶。当然有人质问里面的真实性,但当疑问一个个被解答,故事就可以放入古典书籍里珍藏起来。例如她们为什么不在美国当地找大款,哪有亲妈让自己的女儿干那种作践的事儿。因为美国就是一座金炉,去里面镀层金,回来后身价就不一样了,谁不想尝尝鲜儿?再说她的长相在外国就是一般话,哪儿能和当地的美女比,咱们呐,天生基因就有缺陷,再怎么长也长不出金发碧眼。还有那美国思想多开放啊,啥儿都不是事儿,听说那里的人每天和不同的人上床,有时还是一大帮一起,多恶心!往往听的那些好奇的学生张着贪嘴点着空头,不住称是。我要是在旁,看着他们一板一眼的神态,都会不气反笑。我觉得这个国家才是最开放的,十四亿人里出现过几次‘与未成年发生性关系入狱’的新闻。有几个未成年人知道这是错的,最主要的是又有多少个成年人明白他们在违法。道德沦陷,也许。所以当陈子鸣问我谣言的真假,我只是笑笑。
“笑啥,一天天跟个大傻子似的,就知道笑。来跟我念,Te amo,Mi amor。”
“你说老师为什么叫她打牌,学她教的西班牙语?”
她还在休息的时候,我去办公室送改错的作业,里面只有一个没见过的老师对着镜子在整理自己的妆容。放好作业本,我看见韩梅梅的请假条摊放在班主任的桌上:精神抑郁疾病,需修养一个月。字迹虽然潦草,但还是能认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地脚有个猩红的圆戳。我拿起来,揉成团,顺手扔进桌底的垃圾桶里。
“啥?”
“朋友,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在嘴里,有时你需要自己去看,去理解。”
“Te amo,Mi amor。”我知道陈子鸣是在抗议我的间接回避,所以把句子念的声音更大。
他已经不厌其烦的教我无数次,可我怎么都发不出来舌尖顶在上颚的‘r’。我跟他说,这应该在一大群队伍中足够了,没人会在意我的不标准的发音。可他还是不愿停止,我觉得他是在炫耀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许他有祖先是死在西班牙人手中——牵强的关联。
韩梅梅从我身边走过,到了最后一排坐下。她一路上微笑着,看到每个盯着她看的人都会轻轻点一下头打招呼。这是韩梅梅上学以来,第一次为班级打牌,前两年这项美貌的任务一直扛在花琦的肩上。经班主任委托,她穿了一件白色斑点的连衣裙,腰间扎了条黑色细腰带,裙摆处长满了蓝色的‘勿忘草’。脚底由两只裸色粗高跟凉鞋支撑着,她挺直的腰身,披肩的卷发,若有若无朝气的态度,和她休息结束,回到学校面对所有议论时的表情一样,她没变,也没让谁击倒。她有着怂人们最畏惧的武器,自信和自由。哪怕是假装,她也会丝毫不露痕迹的彰显她令人生畏的气势。她不会躲闪任何人的凝视,她的眼睛里看见了整个世界最清楚的模样,却再也看不见我。我不为我做的决定后悔,因为自私里容不下爱。
随着太阳升高,操场上的人们渐渐多了起来,风也旺盛的不成样子。大家开始吹气球,绑彩旗,拉横幅,有四五个男生又从教室里搬出两张桌子,三张长椅。铺上白布的桌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上面的破旧与斑驳。即便是在晚春,还是能看找到冬天的痕迹。陈子鸣在两班空地伸腰压腿,班主任终于挖掘出他身上的黄金,几乎所有的跑步项目都写了他的名字。他的六项名额报满,班主任让他到时候再换上别的同学的号码牌接着跑。我则专心致志的在地上找寻那一寸已故的草地,野草上的水珠挂在我干裂的掌心,为我修复上面条条裂痕。空气潮湿的寒冷,我听到韩梅梅在后面打了个喷嚏,想要脱下身上的校服拿给她,却晚了一步。她身上已经披了旁边男生的衣服,我盯着她看了一小会儿,看着她和另一个男生风声笑语。是我的错觉吗?那个皮肤黝黑的男生怎么那么像我。
第一声喇叭响起,高一学生集合,第二声,轮到我们。三声,检阅开始,我和陈子鸣戴上了领来的白手套。两男两女激情高昂的照着演讲稿,重复着和去年相同的话,不过所有的‘猴’都换成了‘狗’。相隔八只队伍,是花琦白色皮衣加上蓝色彪马运动裙,如果运动会要是在冬天举办,她一定会穿件貂皮大衣在身上。
韩梅梅举着贴着太阳和月亮的木牌站在我的前面,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带我回到了那年的升旗仪式,我们的距离比现在要近一些。她用头发刺激我的下巴,却让我的心痒了起来。披在她肩上的衣服已经回到原主人那里,她光滑的双臂上,皮肤正在慢慢收紧,抵抗着连阳光也无法完全驱散的浓郁寒气。这个世界很安静,我们很安静。大家就这么站着,没人说话,没人回头。
韩梅梅先迈开步伐,就像之前排练好的,一米的距离。结束后,我脱下白色手套还给老师时,被埋怨我跟的太早了,一米的距离有那么难算吗!正步落脚余一掌的距离。可见她走,我只能等待呼吸长短的时间。
撤走了球门的操场,看起来比之前还要开阔,从校门口绕一圈走到场地中央,有几次我差点儿踢到了她,幸好我及时刹住了步伐。在观赏我们的上方来看,我的样子一定滑稽极了,走几步要摔跤,又没倒地的形象令我着实难堪。
“同胜利,爱飞扬,Te amo,Mi amor。”这是韩梅梅为班级起的口号,同学们和班主任很喜欢,虽然不是特别理解她想要表达什么。抛开关于对她谣言的偏见,每个人都想在运动场上变得洋气。有什么会比‘洋人’的东西更洋气的。
我们和其他队伍一样,走到自己班级布置的会场前停下,韩梅梅依旧双手拖举着牌子,不过高度比之前矮了半截。她右臂上隐现的肌肉正在慢慢萎靡,气息奄奄的抖动着。十班路过时,陈子鸣吹了声口哨,被花琦白了一眼。
“……体育健儿们,我们知道你们的辛勤,我们了解你们的辛苦,加油吧……感谢校领导和市领导的支持与参与,感谢老师们的无私付出。我相信在他们公正的评选下,一定会为今年的春季运动会增光添彩……”
检阅结束,全员解散,运动会即将开始。陈子鸣接过韩梅梅手里的木牌,让她往前坐,坐在我们那里。她没说话,用行动给了答案。待她坐下后,那件衣服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过了晌午,气温才把奔跑的热炉燃烧起来。100米、100米障碍、400米、400米接力、800米都已经比过了,多亏陈子鸣,我们班目前拿到了第二的名次,总是喜欢争第一的班主任,对这个排名满意的合不拢嘴,她说她带过的班级,运动会从来没拿过这么好的成绩。她带头,从桌上的纸壳箱里,拿出大小镲和锣,递给前排每个人,只要陈子鸣一出现在比赛场,就吩咐大家死命敲喊。韩梅梅和我一样,什么项目都没报,只是来当观众,分享他人的荣誉。我们俩都守在自己的领地,适应的鼓鼓掌,绝不上蹿下跳。我不知道她静如止水的本领从何而来,我的是来自于习惯,从小坐惯了冷板凳。在前方,中央,或者角落都无所谓,没人会刻意在乎我的举动。
我的头不停的回转,期盼她愿意与我交谈,哪怕只是一个点头也好。有几次我们的双眸像之前一样对视着彼此,我眼里有她,却看不到她眼里的我。我没见过谁真的可以拿另一个人当空气,就算在生气时也少不了瞪眼筋鼻。可她的眼神直接穿过了我的脑袋,继续向下一个目标望去,没有躲闪,没有慌张,单纯平静的观看比赛,一点儿都不介意我这个障碍物。
我身边经常有人过来逗留一会儿,在地上敞开的三个大塑料袋中随便掏摝零食吮嘬饮料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乱搭。我又一次回头,看见韩梅梅,返璞归真的韩梅梅,没了华冠丽服。蓝色的背心紧贴胸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牛仔保护着她的双腿,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换的衣服,就像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她。有时,我质疑她的真实性,特别是在看完‘24个比利’,我在想所有的一切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她不是真实的,陈子鸣和花琦也不是,萌萌、马思德还有葛娇一家,我在地下看到的其实是王叔和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像女人的男人。这个纷杂的社会可以把人逼疯,然后冷眼旁观的从此没有垃圾和人类的区分。我会成为下一个大军吗?从他跳出来到我身边,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纯粹,一种无法被污染的人性疯癫到随心所欲又善良到孤寂,我有这个荣幸吗?韩梅梅令我质疑她的真实,何为真实?我看着她,她看不见我,就像那天我们从冰雪世界里出来,她走在前,我折回了家里,只为等她与我之间的距离可以模糊的化不清界线。就像我们去年只有四次的交集,其余的时间都处于平行。但我还是知道她一切的行踪,譬如她每周会见一次马思德,规律不定,场地不一,但每次都会避免在人群多的地方会面,他俩大多数时间都在争吵,偶尔短暂的和谐让我急促不安的以为他就是那位躲藏起来的男友,直到他把她递来的纸袋推回,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则站在那颗长着树瘤的老榆树下目睹一切,看她任由撞开她的人继续前行,慌张的蹲到地上捡拾洒落在纸袋外的人名币和露出一角的黑色金属直管,她看不见我;就像我习惯于放学后沿着轿车的轨道跟随她第一次去葛娇家里时,我有多么想破门而入,最终只是颓然的坐在了门口。然后,她衣衫整齐的走出来,我在花丛后看着她,她看不见我;就像我叛徒般,揭发了所有的事情,让她被囚禁于高塔里,我愧疚的站在楼下看着她,她看不见我。
最先空荡的塑料袋被风卷了起来,落到操场上的沙坑里,让下午第一场比赛三级跳的选手摔倒在地,那一幕不断的在人们脑海中慢动作回放;他是怎么得意洋洋的挂着笑容摔个最惨烈的‘狗啃屎’。胳膊和腿上有不同程度的擦伤,皮破了,血却不愿意流出来,周围葛藤的青紫让人看着难受,又不忍挪开目光。有紧张的,有大笑的,有无动于衷的,还有和我一样后知后觉的。那人被扶下了场,第一句话是对我说的,带着些怒气。
“许威仔,那帮孙子们,把我的水都喝没了?”这才提醒我,原来第一个空了的袋子里装的上水。水没了,他之前让大家随便吃喝的豪气也没了,我把我脚下四瓶还剩下三瓶半的农夫山泉取了两瓶递给他;我妈昨晚在桌上扔了五十块钱给我,示意让我和大家一样去买零食吃,我早上只在楼下的小卖店里买了四瓶水。为什么四瓶,我不知道。
陈子鸣用着没受伤的手捏紧塑料瓶,咬开瓶盖边喝边撒在脸上,有几滴趁机滚到伤口处的水红的不彻底的接着滚到木凳上。一个女生拿着邦迪和红药水过来帮忙,发现邦迪太小遮盖不住伤口,又跑去医务室,拿了一大团纱布,像包粽子似的在陈子鸣的胳膊上左缠右裹。
“妹子,以后别学医,考上了咱也不去,这手法,你挣那点儿工资都不够赔的。”陈子鸣疼痛感终于被唤醒,在一旁狼叫月似的咆哮。
“埋汰谁呢你,臭不要脸的。你个个儿整吧。”女孩儿走之前,在陈子鸣胳膊上狠狠一掐。
“哟哟哟,疼啊大妹的。急啥儿眼呐,我不是还没说完呢吗,多收几个红包也能满足温饱。”他转过头跟我说,“哥们儿,看没看见,最毒妇人心呐,谁找这样的谁完犊的。”
“这就是你为什么保持光棍儿的原因?”
这句话令我俩同时陷入了沉默,我不清楚他的理由是什么,幸好他也没问我的。
下一秒,我陡然到了洒了石灰的跑道上,和另外十几个人交叉站着。那个在我点头应允前的压力和焦虑不仅没因此减少,反而激增。我的身躯正在无限的缩小,特别是在我感觉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其实也许根本就没人在乎我。但我无法放松,如同受绞刑时的囚犯,不愿提前伸出舌头坏了惊喜(也许它不会出来)。我开始分不清场外的表情,我恨五岁,因为那年我发现了笑容里隐藏的层次。当我看见大人们冲着电视里一群搂脖抱腰跳着舞的外国人咧嘴开笑时,我发现他们也对我这么笑过,那笑声像是生了病,忽高忽低,吓得我不停的后退,却被身后的门槛绊倒。那笑声立刻寻到了新猎物,音量拔到g7,激起了夏季野猫们的情欲。而那时,电视机里放荡不羁的异国风情印刻在了我的脑海,让我好奇起他们如何在这种笑声下自由的存活。不是像我现在这般,紧张到全身发麻,认为死亡竟成了简单的选择。我后悔答应班主任帮陈子鸣跑一千米,在这种悔恨中,懦弱如我,什么都做不了,原来过了这么久,我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小孩儿。因为过度紧张,眼前模糊到昏暗。昏暗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排成排那么有层次的笑着看我,有我能叫出名字和叫不出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笑容,像是不同病毒滋生出不同的疾病那样,独特到致命。多可笑啊,要是我把这些大声说出,给别人听,他们一定会笑,就像我没舞伴却自发的跳了一段华尔兹。紧接着,黑暗扩散到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有一柱灯光打了下来,里面站着一个人影,挂着可以驱散阴霾的微笑。看来,我还是长大了,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可以让一切恐惧显得微不足道的女孩儿,她大于生命的激情,和扣在她身上让她真实的枷锁。
在体育老师举起发令枪大吼:预备。我用仍旧晕乎的眼睛瞄着旁边的男生,学着他的模样双手拄地,半躬着身子,看着脚上不是半荷叶水渍的白布鞋,是双乔丹——我们陪陈子鸣买的那双鞋。他强烈命令我跟他换,似乎不换就要还回我初中时无意推倒他的一记仇,也不管最后是谁鼻青脸肿了一周。
发令枪被勾响前,我抬头看了一眼观众席,韩梅梅正在专注的谈笑风生,花琦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陈子鸣不停的击打手里的镲。她还是看不见我,但我能看见她。
“起。”一阵白烟轰声升起。
也是像这么奋不顾身的跑,那天夜里,我回家拆开礼物,把围巾围到脖子上,跑下楼去追她,想要当面跟她道谢,并且回答她之前问我的问题。我决定不再等了,我是有话要说,我想要告诉她我的感受,没有拐弯抹角,一脱到底最诚挚的感受。我跑到路边时,已经没了她的踪影。我沿着结冰的江边和落满积雪的松树继续跑,路灯下是我的残影,没有欢呼,只有不时刮起的寒风,它怎么也吹不进我受到保护的脖子,这恰恰也是我想要给她的。
前方,有一盏断断续续的路灯在随着风的速度摇曳,下面有一辆没开车灯的黑色轿车,与这场夜合为一体,宛如熟睡的野兽,任由人们在它的尾处恣肆发泄。灯亮的时候,三双手互相搭伴共同托起头上的明月,路灯暗的时候,深色的黑粘住了所有欲张开的唇,让万籁俱寂成了主唱。近一点,三个种子般的颗粒壮了些,再近一点,他们都有了雏形。我停下脚步,推开另外两个,我的手伸向里面酒气最大的那个人,她没了我之前印象里的端庄。
“阿姨,能站起来吗?”
“这不是薇薇的同学吗?阿姨没事儿,你去帮帮你叔,左边那个。”
在我拉开了撕扯的汉子,警车也从远处开始的暴躁警告,到了眼前的干练行动。红蓝充斥着街道,使食物看起来更加的迷幻。警车开走后,留下我和韩梅梅的母亲。没了之前的端庄,她身子不正常的倾斜着想要往轿车里挤,可车门却像人心,不论她怎么用力就是打不开。
“哔,钥匙在你叔手里。走,小孩儿,咱们打车去。”而我只是在想,她嘴里的那个我不认识的‘叔’是她的伴侣吗?
我们顺着我来时的路往回走,韩梅梅母亲不用我扶着已经可以自己行走了。她把手抬到我的下巴,温柔的摸着我的围巾。
“薇薇跟她常姥学了一个多月,才动手织了这条围巾。看来你对她一定很重要。哈,我就不行,即使和她爸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没想过织条围巾送给他。她的浪漫随他爸。阿姨平时不是这样,没吓着你吧。”是吗?我对她有那么重要吗?
她的半边脸给风打的亮红,比她的嘴唇还要红。
“习惯了。”
“也是,我都忘了我是在哪儿了,要不是薇薇张罗要回国,我跟你说,我也不能为了应酬被灌这么多酒。我有病,孩儿,酗酒的病。我敢说,在满大街的酒鬼中,只有我一个人敢承认,因为在别人眼里这不是啥毛病。薇薇就烦我喝酒,所以我回来之前已经戒了,我每天都去aa。”aa?难道这就是她为什么几乎不回家住的原因?
上了出租车,韩梅梅母亲告诉司机去最近的派出所,然后跟我讲了事情的经过。我脑里一直在想她跟我说我对韩梅梅很重要的事。结果司机听得入神,挤进了话题里。
“就我这破车,有时还有过来趴车讹钱的。你开啥车啊,大半夜的还有讹钱,那帮人不都是中午出来吗?”
“嗯,太不像话了,不给钱就不走,还要动手。德国车,也许不是同一帮人,在钱的面前,没人有身份。”
“艾妈,说话还挺有学问。开德国车,有钱人呐,大众还是宝马,不会是大奔吧!啧啧,不像俺们,起早贪黑勉强糊弄口饭吃。你是干啥儿的,要是有啥好活儿介绍介绍啊。”
出租车驻泊在长安路一处不起眼的平房前,我以为我们是回到了80年代末要不是下车才看见墙上庄严的三个字。门口有一扇铁门,没人把守,推开时,上面的寒气灼烧了我的手指。韩梅梅母亲从我身后超越,快步向那个蓝白色闪着幽冥灯火的房子里走。
一进屋内,是一张长椅——这个城市爱它的长椅,学校、公园、医院、商场还有这里,它是唯一不被纳入歧视范围的东西,不论在什么地方,坐在它上面的人们都不会对它大放厥词。天花板上吊着的灯泡,比爱尔兰人的脸还要白。甬道分为东西两侧,一间间小屋顺排下去。这里和我陪花琦去的诊所一模一样,都是充斥着两种不协调的味道,那里是消毒水和香水,这里是饭香与馊酸——味道传自同一桶泡面里。
韩梅梅母亲走进了一间房间里,剩下我独自承担夜里驱散不尽的孤寂。我从没戴过围巾,我把它从脖子上摘了下来,感叹这个从未出现在我生命里的物件,今夜带给了我多少温暖。我用手掂了掂它的重量,轻的浪费不了几分力气,又沉的无法脱离重力在空中自由飞翔。我看着上面的每一针每一线,她是用了多少功夫才完成这份礼物。在围巾的尾端,有一处一寸长的尾巴吊在那儿,也许是太着急,所有的线都已经连接好了却没有打成最完美的结。就像她回国,只是为了上演她眼中的哈姆雷特。她每次问我还不想问她吗?眼神里都在暗示着‘相信我’。她可能发现了在暗处的我,可能没有。我只知道过去的一年里,她和屋里的男人都相安无事的呼吸着。我自以为的帮她保守秘密,却是我不想打破我们之间羽毛般的平衡。但我忘了,平衡是靠双方。我想,现在,此刻,同一座房子,是否关押过那个令她铭心镂骨一辈子的人。如果羽毛般的平衡被她打破,她会不会也沦落到这里,体会这里叫人失心的孤寂与绝望。我需要坐下来,却怕习惯了压抑的美味。白墙上被烟熏的一幅幅晕开的黄渍,拼凑着张口的饿鬼图,它们饥饿着年轻的肉体,配上腐朽的心灵……
“孩儿,没事儿了,走吧,让你叔自己先去提车,姨送你回家。”
出了派出所,我又把围巾围到了脖子上。
“许薇找到打死她父亲的那个人了…….”
四百米一圈,一千米需要跑两圈半。我像一个芭蕾舞者练习原地转圈,眼睛固定往一个点上盯。我想我的表情一定非常奇怪,不论跑到何处,头永远保持相同的方向,就算心肺要从嘴里跳出来也绝不动一下我早有所属的脑袋。
当我躺在水泥下面的黑土地上,我为我做的决定感到骄傲,即便它可能要了我的命。
“姨,我知道我不该瞒你这么久,我以为我这么做是为她好。你要是想骂我,尽管骂。”
“为什么要骂你,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要感谢你告诉我。女儿是我的,枪也是我的。你们之间存在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我只是怨我自己没多陪在她身边,什么应不应酬,到最后是你身边的人,大过你银行里的纸。我也以为她能照顾好自己,况且还有你们在,所以我就放松了。其实,我考虑的都是我自己,忘了你们都还是孩子。你知道吗,孩儿!我估计你再也不会听到这句话了,但姨要告诉你,自私里容不下爱。”
5.2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