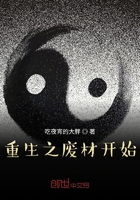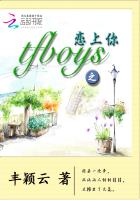不出老冯所料,靳武确实邀了秦先生赴宴,其中还包括我跟房文,这一点让我忐忑不安,房文的身份特殊,任何有南晋官兵在场的地方对他来说都非常凶险,可镇子周围全是官兵,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只能乖乖听话。
靳武并没有住到镇上,而是在镇外扎了行帐,就在踏进营门第一脚时,我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即便囚车挡去了不少视线,可我几乎能肯定那是屈氏,很巧,她也刚好抬头,当我们俩的视线相撞时,我的心一沉,她也微张开嘴,从她苦笑的眼中我明白,这次是真得逃不掉了。
房文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的囚车,自然也不会看到囚车中的人,我暗下深吸一口气,挡去了他更多的视野,拉他紧走几步跟上前面的秦先生。心里毅然做了决定,事已至此,我只能全力保住房文。
就在这抉择尚在心中酝酿时,却又被眼前的景象狠狠一击,跟随靳武前来迎接的人中,竟然会有大都王宫的人,而且还是我非常熟识的,早年曾在王后寝宫侍奉的宫人,我记得很清楚,他叫王平,曾因宦官专权受牵连,被王上罚以重罪,没想到他竟然没死……也许是太过惊吓的原因,我倏然躲到了秦先生的背后,抓着他衣襟的手控制不住地抖动着,我明白,这个王平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未姐姐?”房文好奇于我的举动,一边抓着秦先生的手,一边回头看我。
秦先生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不安,略微侧过脸来。
“先生,我还是……先回客栈吧?”说罢就想拉房文,心头存着一种侥幸,希望王平没有认出我,那么房文也许可以逃过这一劫。
没抓到王平,手却被他给抓住,“我能带你们进来,就一定能带你们出去。”
我现在连自己都不相信,又怎么能相信别人?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先生……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怎么知道我想得就简单?走吧,这种时候才想临阵脱逃,太晚了。”不容置疑地拽着我的手腕继续往前。
一直到大帐前,我还低着头,可我能感受到人群中那道不善意的盯视,他似乎正在等着我抬头,等着看我惊吓的表情……倏得抬起头,正视那道目光,确实,这种时候才想到临阵脱逃,已经太晚了。
也许是没想到我敢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王平显得有些惊讶,不过很快恢复,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复仇的笑意。
靳武的视线从我的脸转到王平的脸上,看罢我们的神态,眉头微蹙,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靳将军,您可是又立了一大功。”王平对靳武微微鞠躬,宫人独特的尖细嗓音,此时听来尤为刺耳,“云小姐,别来无恙啊。”
他的声音唤起了我头脑中两年前的诸多记忆,如同打通经脉的银针,惧怕随着放弃消逝而去,“王内侍都还活得好好的,我怎么能有恙?”想来王家子孙接连遭诛,也有这群先前受打压的内侍宦官的挑唆。
从鼻子里冷哼一声,“那就请吧。”一扬下巴,十几个王宫护卫装扮的人围到我们跟前。
“慢!”秦先生插言进来,靳武等人都很吃惊。
“你是谁?胆敢管南晋王宫的事!”王平蹙眉打量他一眼。
“天下人管天下事,有何不敢?”
“想管——那就一起抓起来!”王平的仇恨来自于数年前宦官专权遭灭,我当时也不过十多岁,并不清楚太多内情,只知道当时宫里抓了很多宫人,后来长大一点才知道王上那几年努力想肃清宦官专权,杀了不少内侍宦官,王平也是当时受株连的一员,没想到如今又东山再起了。
两个护卫伸手想拿秦先生,没到跟前就被靳武身侧的老冯一脚一个踢飞了出去。
“靳将军,这是?”王平既诧异又恼怒.
靳武却只是微微牵动唇角,“还请王大人给个面子,这是我少时的同窗,难得今日遇上,请他来饮酒叙旧而已。”
虽说京官小卒能抵封疆大吏,可现在毕竟是在他靳武的地盘上,强龙不压地头蛇,王平再牛气也不大敢擅动。
“既然是靳将军的同窗好友,那自然不能动,小人来襄樊之前,王上叮嘱,说靳大将军是我南晋第一勇猛悍将,只待王家守孝期一过,百官调整,大将军必然高升,到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小人我又怎敢得罪大将军!”虽然久离宫闱,不过这种看似恭维,实则威胁的言辞还是能听出个一二,这就是地方官员畏惧京官,尤其宦官、内侍的原因,他们距离权利中心近,更容易左右地方官员的政治命运,王平这番话不过是想告诉靳武,王上有意属他高官,他若想日后平安高升,就不要目中无人。
“靳武没多大本事,莽夫一个,就是给我高官,我怕也没那个福气带得称心如意,这个襄樊已经足够我逍遥了,不过还是要感谢王大人的吉言。”靳武这番话莫名让我感到了一点希望,也许……他是个忠臣,“这两个要犯,我看还是由在下先派人看着,大人刚到这里,还不知道最近襄樊匪患四起,安全起见,还是先由我的人看着吧,等王大人回大都时,再行押解也不晚。”
王平能在政变中活下来,必定不是愚蠢之辈,何急何缓还是分得清的,自然不会急着争这一时的高下。他完全有信心靳武不会乱来,毕竟他不过就是个不得志的武将,否则堂堂的中卫军不会被“发配”到这种地方来。
王平冷笑着退下后,靳武并没有让人押下我们,反倒还将帐外囚车里的屈氏也放了出来。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谁,可没人说出口,就是王平也只敢称呼我们“要犯”,毕竟房文跟屈氏是先王的嫡亲子女,绝不可能“光明正大”地恣意处死。
屈氏昨天夜里到了襄樊大营,倒霉的是正好碰上王平前来传达王命,被撞了个正着,自然没逃得掉。被王平的人一直压到现在,两天一夜滴水未沾,嗓子哑的早已说不出话来,手脚上还到处是伤。
“还要吗?”见屈氏碗里的饭菜吃完,老冯恭敬地过来询问。
“暂时不要了。”我先插言进去,饿了这么长时间,一下子吃太多并不好,“一下子吃太多,怕会撑伤肠胃。”
“也对,那我再去拿些伤药来。”
老冯出去后,顺带将门口的侍卫也撤了下去,这当中也包括王平的人,以便帐子里人说话方便。
“襄樊守将靳武拜过太子殿下、公主殿下,恕在下之前得罪。”抱拳鞠礼,而非单膝跪拜,看得出来,这诚意可不算大。
屈氏的嗓子说不出话,只好对我打个手势。
“靳将军是公职在身,身不由己,殿下与公主都明白。”一边处理屈氏手上的伤,一边替她说出想说的话,屈氏暗下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想看他要怎么处理眼前这个状况。
“如今这局势,将军也大概都知道,不知打算如何处置我们?”放下手中的药油,与其绕着弯子打探,不如直接把话挑明,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早早晚晚的都一样,屈氏也略微点头,同意我的说法。
“靳武受王上亲命,驻守襄樊多年,一切行动皆听王上号令,从不敢违命抗令。”这话说得很清楚,他不会放我们。
我与屈氏对视一眼,陷入沉默,他这么做确实也没什么不对,王位早已易主,我们这些“乱臣贼子”自然不能跟现今的王上相比,一没权,二没势,房文又只有六岁,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成事的。
这时,一旁的秦先生倏然发出了一声笑叹。
“笑什么?”靳武坐回桌案后,瞥一眼旁边的秦先生。
“笑你里外不合、前后矛盾。”
“说说看。”
“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想过安稳日子,你刚刚就不会得罪那个王大人,既然得罪了,又何苦吓唬这几个小娃娃?若老弟真想在襄樊逍遥度日,何苦煞费心机剿灭周遭匪患,留着山匪慢慢打,岂不可以长久享受朝中的粮饷?与韩国的疆界争端,又何苦那般计较?辛苦训练的马探、细作,鞭及西北赵国,连续几年屯兵秣马,老弟,你这可是有造反的嫌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