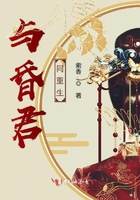清婉温和地说:“只是用银针在手指上取一滴血而已,不会伤及您的龙体的。”
苏淮静默良久,说:“那如果那个孩子不是朕的呢?”
清婉:“如果孩子不是陛下的,臣女会送他们母子出宫,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如果是的话,您可以不给陈氏名分,臣女不逼您,但那个孩子必须入玉牒。”
苏淮闭上眼,叹了口气,沉默不语。
这就是他捧在手心里宠了这么多年的女儿。如今他老了,能为她做主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他忽然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苏淮闭着眼很久,清婉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睡过去了,她轻手轻脚走到门帘旁,吩咐小太监取来银针和一碗清水。
清婉在炕上坐下,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
苏淮的眼皮动了动,睁开眼无奈地看着她。
“父皇,不会有事的,儿臣的功夫很好的。”清婉温柔地浅笑着,好像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您要是怕的话,可以把眼睛闭上。”
苏淮听着她温凉的声音,还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清婉取出一根银针,轻轻地扎了一下他的食指,将鲜血滴到清水中。“可以了陛下。”
苏淮却不睁眼,只说:“你不给朕包扎一下吗?”
清婉无奈地说:“这么小的伤口,过一会儿便自动愈合了,包扎什么呀?”他真的像个孩子……
苏淮睁眼看着碗中飘浮着的那抹鲜红,一脸不悦,“有事就父皇无事就陛下……”
清婉懒得搭理他,将陈桓的血倒入水中,苏淮屏息静待,身子都紧绷着,清婉看上去倒是轻松多了。
碗中的两滴血很快便相融了。
苏淮很快移开了目光,脸上表情淡淡的,看不出什么情绪。
清婉愣了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道:“陛下若是担心臣女取了自己的血来做假,可以派人去将那个孩子带过来,当面验一验。”
苏淮垂下头转着手里的佛珠,说:“没有必要,朕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事来。”
清婉让人将水和银针撤下,挪近了些,握着苏淮的手,苏淮被她手心的温度吓了一跳,取过自己的暖炉塞到她手里。
“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清婉说:“是个男孩,六岁了,叫陈桓。”
苏淮想了许久,说:“永熙公主前不久刚出降了,刘太妃一个人在宫里也甚是无趣,就将四皇子教给她抚养吧。至于陈氏,朕会让人另为她僻一居所,允许她每个月见四皇子一次。”
永熙公主是苏淮最小的妹妹,她的生母刘氏虽已成了太妃,年纪却不过三十左右,清婉听说,刘氏还是先帝后妃中唯一一位入宫前中过榜眼的人。
“那陛下打算把四皇子记入皇后娘娘的名下吗?”
苏淮摇了摇头,说:“皇后已经有了一位皇子,再有一位怕她生事端。况且,皇后曾与陈氏有过嫌隙,还是把他记入燕妃名下吧。燕妃入宫多年,一直恪守礼节,老实本分,对下人也都是以礼相待,还曾为朕小产过,把四皇子给她,别人也说不了闲话。”
清婉欣慰地望着苏淮,她忽然觉得也许自己可以让他改变呢?她能从苏淮的表情上看出来,苏淮并不愿意这么做,可她稍稍强迫了一下,他也就做了。别的父子相认都满是喜悦,他却一脸疲惫无力之感,好像一直在被她推着往前走。
“既然是四皇子,名字上也该用景字辈,他原先只单名一个桓字,便改叫景桓吧。”
苏淮伸臂将清婉揽到怀里,说:“这些宗族琐事,你将来也要学着打理,你高兴便好吧。”
清婉抬起眸,只看到他有些花白的胡渣,他听上去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可他不开心也没办法,清婉来之前已经决定好了,这事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苏淮抵着清婉的发,忽然问道:“婉婉,你已经及笄快四年了,朕给你取个表字吧。”
清婉直起身,说:“臣女已经有表字了。”
苏淮吃惊地:“你有表字了?朕竟然还不知?”
清婉点了点头,说:“臣女十五岁生辰的时候便有了,是老师取的,叫凌秋,取自宋庠的诗,此君高节最凌秋。”
苏淮表情有些僵硬,他不想让清婉看到自己的表情,转身去拿一旁的折子。“你们从前经常书信来往吗?”
清婉淡淡地:“也没有,就偶尔有一些学业上的问题,会写信请教老师。”这谎话编的实在拙劣,那张老先生张怀珏年轻时也是任过翰林学士的,她有什么问题非要写信去问张廷。
清婉疑心病重,感觉到了苏淮的忌惮和猜疑,接着便听他说道:“你们以后还是少以书信来往为好,免得落人口舌。”
清婉心里仿佛砸了一块石头似的,闷得很。苏淮在位期间,一向重武轻文,大力重用武官,朝中在短短十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手握兵权,持有军功,目中无物的大臣,文臣却被长年压制,就算是张廷这样的内阁首辅,在内阁中的话语权也不得不受靖远侯等人的干涉。
张廷愿意忍受他们,清婉可不愿意。
“臣女知道了。”清婉埋着头,闷声道。
*
沈嫣漫不经心地坐在医馆里分拣草药,时不时地向窗外张望。
已经快酉时了。
冬日的天暗的很快,莫长空正在门外点着灯笼,无意中瞧见窗边的沈嫣,她傻傻地望着对面的街道,手里的黄芪被她掰成了一小块一小块。
“沈姑娘。”
沈嫣骤然回神,“啊”了一声。
莫长空笑着说道:“你要是累了,就先回去休息吧,那些草药明天再弄。”
沈嫣应诺,收拾好桌面,想了又想,跟莫长空说道:“师父,我出去外头买点东西。”
莫长空点点头:“去吧。”
沈嫣净过手便出了门,往对面街角的惠风茶楼走去。
他大概已经走了吧......大概吧......
这家惠风茶楼,据说是东阁大学士兼任工部尚书文若虚开的,茶楼有一招牌,叫招摇玉露,产自西州的长龙雪山,每年仅有不到十斤的产量,西州总督每年进献一半到宫里,另一半则以高价卖给这家惠风茶楼。从而吸引了京中很多达官贵人竟相前来品鉴。
霍容安穿着那件宝蓝色的直裰,临窗而坐,指尖有一搭没一搭的在桌沿上扣着。
今天他特意早早出门,未到申时便等候在此,未曾想......看来,这东西是送不出去了,他叹了口气,拿过茶案上用布包着的一本厚厚的书,凝视了片刻,甫一起身,便见那瘦小的身影走了进来。
“这儿。”霍容安疲惫的脸上露出些许笑容,朝沈嫣招手道。
沈嫣走了过去,有些局促的站在距离他一米远的地方,便不再往前了。
霍容安笑着说:“不过来喝杯茶吗?”
沈嫣摆摆手,说:“不了,表嫂还在等我回去吃饭呢。”
霍容安便不再强求,往前走了两步,将手中的书递给她,“给你的。”
沈嫣疑惑地打开布包,居然是一本《思逸内经》。“你就想给我这个东西?”
霍容安浅笑着点点头,说:“你昨天不是说,你最近在学医术吗,我忽然想起,外曾祖父晚年时曾在家中专研医术,藏有许多医书,他故去后,家里的这些书也就没人看了,我便拿了一本来送给你。”
叶思逸是东越末期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夫,不过沈嫣接触医术的时间还不长,不知道叶思逸还写过医书,霍容安也没有告诉她,这本《思逸内经》其实已经绝版了,她手里的这本,还是他外曾祖父随梁太祖攻下皇城后,从东越宰相府里掠夺来的珍品。
沈嫣想着霍容安看上去也不像是会看这些书的人,想了想,便收下了。
晚间,沈嫣吃完饭,便靠着迎枕读书。这书足足有三寸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书的封页有些发黄,看上去有好些年头了。
这书中的知识对于沈嫣来说,还是晦涩难懂了些,她看了整整一个时辰,也不过翻动了二十来页。
叶思逸果真不愧为名医。
这一个时辰看下来,沈嫣便发觉自己先前所学的知识都过于浅显了,霍容安说的对,医术真的是一门很复杂的技术。
沈嫣看得太阳穴有些发胀,便放下书,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马氏拿着一盘糕点走了进来,瞧见桌上的医书,说:“沈姑娘这么晚了还在看书呢?”
沈嫣点点头,唤道:“表嫂。”
马氏将糕点放到桌上,“来,吃块点心。”她在桌旁坐下,随手拿起了《思逸内经》,愣了愣,“这不是叶思逸所作的医书吗?我听说这书的完本都已经绝迹了,长耀的师父手里都只有一些散乱的拓印稿,你是从何处得了此书的?”
沈嫣嘴里含着糕点,一愣,说:“是......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马氏顿时明白了,笑着说:“我就知道,是你那位贵人送的吧?难怪呢......”
沈嫣不知该如何和马氏解释霍容安的事,更没有想到这书竟然这么贵重,早知就不该收的。“嗯,对,是她。”
她表面上虽抗拒着,心里对霍容安又多了几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