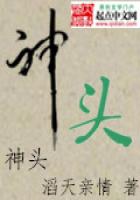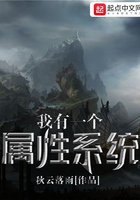骆清焉带着两名侍卫连夜奔波风雨兼程,临近沧河境界,雨势又开始加大,望着飘摇的雨丝,她只觉一颗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离家越近,越是情怯,深怕会有什么意想不到之事。
远远她就看到自家房屋零碎的坍塌成一堆废弃之物,她紧张地挑着车帘寻找家人的踪影。
强劲的雨势瞬间将她头脸全部打湿,坐在车里的小丁忍不住拉了她一把,小丁因惦记家人,特意要求随从一起而来。
驶至近前,骆清焉毫不迟疑跳下车,淌着积水,踏着泥泞,冒着倾盆大雨,嘶喊着家人。小丁手忙脚乱地拿出油布伞为她遮挡。
“姐姐……”一声清脆喜悦的应声从不远处传来,骆清焉听出是小语,忙顺着声音看去。
这才发现,在坍塌的房屋一旁,有几块木板拼搭的临时处所,她奔过去,眼泪顿时喷涌而出。
这是什么地方啊?低矮窄小,四处透风,在里面还要披着雨蓑,家中三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狼狈至极凄惨至极。
眼神过处,意外看到林志昙也挤在里面,他不是商家之子么?难道家里也遭了不测?念头只是一闪,便顾不上理会,疾步冲过去,紧紧搂住依然痴傻的娘亲,哭得泣不成声。
“清儿……。,莫哭,这是天灾,我们凡人有什么办法,等雨停了咱们就将房子修好,你上次留给你娘看病的钱,足够用了”骆明举经历了太多事,对这次意外显得很淡漠。
“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哪怕是城头那栋小庙也能挡风避雨啊?”骆清焉想着娘的身体,语气不由带了怨责。
“遇难的不是咱们一家啊,那儿早挤满了人”骆明举轻轻解释。
“志昙哥说可以去他家的,爹爹死活不去”语焉在一旁嘟着嘴小声埋怨。
“那为什么不去呢?面子重要还是娘亲的身体重要?这样大风大雨的,又冷又潮,娘的身体怎么受得了?病情若再加重该如何是好?”骆清焉听闻气不打一处来。
骆明举挑了挑了眉,阴沉着脸想要发火,看了看林志昙又瞄了一眼小丁,最后叹了一口气,终忍着没加理会。
“不想去别人家,那不会租间房子么?又不是没钱,给了钱却不花,还不如不给呢”骆清焉看着娘的脸又青又白,心疼得又是一顿牢骚。
“谁希罕你的臭钱,带着给我滚吧!”骆明举忽然一声暴吼,哆嗦着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袋子狠狠扔到骆清焉面前。
骆清焉一愣,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连夜赶回,却落得被爹斥骂,即委屈又气愤。
“清焉,别说了,伯父去找过的,没找到”林志昙眼看父女两人要开战,忙在一旁息事宁人。
骆清焉咬着下唇没再答腔,替娘擦了擦脸上的水气,然后站起身,一言不发向外走。
“姐,你刚来……就要走么?”语焉跳起来扯着她的胳膊,带着哭腔问。
“不是”骆清焉生硬地嘣出两个字,拨开妹妹的手,气横横地走了出去。
“小丁,走,咱们到街上转转,看看能否租套房子”骆清焉牢记着楚天狂的话“只要有钱,什么也不用担心”,她就不信,还有钱办不到的事情。
三人驾着车四处打听,一上午问到好几家空房,不过价钱贵得离谱,至此,骆清焉明白了爹爹没有租到房子的原因,以他节俭的性格怎会如此大手笔呢?
骆清焉找到一户离自己家距离较近的房子,直接跟房东说要将房子买下。房东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看样子家境比较富足,不信任地上下打量着骆清焉,“小姑娘,你家大人呢?买房可是大事啊?你能做得了主?”
“你只管说价钱就是”骆清焉一脸从容,她已打定主意,即使再回宫将自己的积蓄倾襄而尽,也绝不能再让娘受一点委屈。
那人被骆清焉的气势所迫,一时猜不透她是什么身份,狠了狠心,张口要价“一百两黄金”,其实若在平时,只有五十两足以。
“好,一言为定,你将房契地契一并拿上,与我们到官府过户”骆清焉见过爹爹买房时有这套手续,张口说出,显得很在行。
那男子一听果然更不敢对她轻视,吩咐内人依言取出,坐上骆清焉的马车向县衙而去。
谁知,到了县衙,那管事之人百般刁难,小丁看骆清焉一脸恼怒,不由加以提醒,告诉她那人不过是想要些好处费。
骆清焉性子中禀承了骆明举的正直,也或许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是皇上身边之人,语气无比强硬,执意要那人禀公办事。那人恼羞成怒,一怒之下喊来几名衙役要将她抓起。
小丁抓耳挠腮,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来得匆忙,腰牌丢在了宫里,只靠两片嘴说自己是宫中侍卫,估计行不通。
眼睁睁看着两个衙役拿着长长铁链向骆清焉走去,他只能挡在骆清焉面前,伸出双手说好话。
就在这时,忽然从衙门后院转出几个人,当先一人是沧河县令,后边一个白胖之人,骆清焉认出是曾帮自家与施家调解的师爷,再后面一人,骆清焉看着眼熟,却想不起是何人,她沉思地盯着那人,努力想在何处见过,她不是怕事,只是怕因自己被抓而不知何时能出来,耽误了买房的大事。
几人听到这边的嘈杂,都扭过头,骆清焉看到那人盯着自己有瞬间的怔神,心一跳,说不定,他认出了自己?她估计此人应该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所认识的官人都是在宫中所见,如果真如自己所料,没准会万事大吉。
衙役们看到大人们出来,也不敢再放肆,站在骆清焉身边等着新的指令。
“咦……。,你不是……。?”那人忽然伸手指着骆清焉,神情很惊异。
骆清焉大喜,看来他真的认得自己。微笑着回望着那人,脑子还在急速地打着转,绞尽脑汁想他是何人。
不容她多想,那人已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县令和师爷,快步走过来,一直走到她面前,神色威严的摒退一众衙役,才言语客气地与骆清焉打招呼“姑娘,是御书房的骆清焉吧?”
“嗯,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大人”骆清焉听他这样一说,确认他铁定是朝中大臣,没敢问人家官职,只含糊而言。
“姑娘来此何事?皇上……。?”那人将声音压得很低。
“我家是沧河的,来此有些私事,皇上还在宫中”提起楚天狂,骆清焉也不由将声音放轻。
“哦,有什么事尽管说,刘某奉旨在此办案,很乐意为姑娘效劳”骆清焉听他一提,灵光一闪,终于忆起这人原来是办案司的刘大人,陆太医死后,他曾问过自己,当时只见过一面,怪不得只觉眼熟却想不起来。
这位刘大人并没因皇上不在而神情怠慢,骆清焉暗自高兴,三言两语便将刚刚之事讲诉一遍。
刘大人越听脸色越难看,骆清焉话音未落,他已瞪着那位如坠迷雾,惊慌失措的县令“哼,还不将这恶徒锁起?你这官真是做到头了”
那位惹事之人眼见苗头不对,吓得连滚带爬趴在地上,转着圈地磕头“大人,饶命啊,小姐,饶命啊!”
骆清焉看他此时可怜得犹如丧家之犬,心一软,心里的气全没了“刘大了,算了,让他帮奴婢办完事就行了”
刘大人已在沧河呆了一段时日,县衙的人每天小心侍侯,他自然一一看在眼里,轻而易举也不想砸了那人的饭碗,既然骆清焉不计较,他又何苦做恶人?
那人有心讨好,将气全撒在卖房之人身上,连蒙带吓,竟然给骆清焉省出七十两来,骆清焉真是又惊又喜,看来,是福是祸不到最后绝不能下定论啊。
虽然已是午后,骆清焉顾不得饥肠辘辘,谢绝刘大人的婉言相留,催促马夫急速回家。
对于骆家来说,此次搬家最为省事,骆清焉只让人走,一件破家什也不让拿,为此,她跟爹又拌了几句口角,最后还是林志昙从中调和,才算做罢。
看着宽敞的新家,骆明举眼里闪过不安和隐忧。心知肚明,一定不会是个小数目,女儿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财呢?她自小好强好胜,常常为达目的使出非常手段,难道她做了什么不轨之事么?
他脸阴得就象屋外的暴风骤雨。
骆清焉哪里猜得到爹爹的心事,只管喜滋滋的安排着他们的住所,等一切安排停当,才感到已饿得前心贴后心。索性喊出小丁,递给他一锭十两的金锭,吩咐到酒坊整治一桌好酒好菜送到家中。
闻着香喷喷的饭菜,大家开怀畅饮,谁也没留意自始自终,骆明举一直沉默无语。
骆清焉长这么大第一次喝了酒,她为自己的付出欣慰,唉,总是有付出就会有所得。
人们散去,她走进属于自己的闺房,东摸西看,喜之不尽,有种苦尽甘来的感慨。
身后传来门响,她以为是妹妹,没有回身,笑着问“小语,高兴吗?姐姐一定会让家变得更好”
“清焉……。是爹”一声苍凉的声音,骆清焉猛地转回身,“咦,爹爹,折腾了几天,怎么不早些歇息呢?”
“爹有事问你,买房子的钱哪来的?”
骆清焉眨了一下眼没有立即回答,爹会问这个问题她不是没想到,只是她一直没想到该怎么回答,谎话毕竟是谎话,对这么重要的事情,一个小小的谎话根本没有说服力。
“你就别管了,女儿已长大,心中自有分寸”无奈,骆清焉只好死撑。
骆明举心一沉,女儿这样回答,已表明她做了不该做之事,涛天怒火顿是地在胸口燃烧,开口便想斥骂,却忽然想着这一切的起因皆来自自己,张了张嘴再也吐不出一个字,只觉万般痛苦一起在心中纠结,令他差点窒息。
骆清焉一直紧张地注意着爹的表情,看他脸一会涨得通红,一会憋得黑青,吓得赶紧拍打他后背,一边急切地问“爹,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给你喊医生去”
“不用了,爹这是心病,哪个医生也治不了的,你好自为之吧,爹老了,以后再不会管你”说完,蹒跚着脚步跨出门,那一刻,他苍老虚弱得犹如风烛残年的老人。
骆清焉听着爹爹灰暗了无生气的言语,心一阵悲恸,知道爹爹为何伤心,为何绝望,可是,她已是开弓之箭,只有勇往直前,再无退路。
躺在床上,细细思量,思来想去,觉得一切只是负了自己,伤了自己,不过,总算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值了。
悲伤的心情渐渐有些舒缓。
这场雨连下了三天还未见减弱,街上来往的人们神情逐渐变得慌乱。不时会听到有人在吵嚷城外流经几个郡的沙河快要决堤。
骆清焉望着这风雨飘摇的沧河小城,心情烦躁而慌乱。小丁来的当天已回家,再未露面,估计家中情况不容乐观。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她心头萦绕不去。
几天的相处,倒让她发现林志昙这个人还不错,不管对语焉对自己爹娘都很周到细心,她不觉放下一宗心事。
这晚,天空一直不断传出轰隆隆的雷声,骆清焉辗转反复无法入眠。她抓起一把雨伞走到院里,电闪雷鸣中,白哗哗的雨就象没有尽头的水链,从天空垂下。
她焦灼地在院中来回踱着,无形的恐惧笼罩了她整个身心。
“沙河决堤了,沙河决堤了”突然一声凄惨的尖叫划破长空。
骆清焉心一凛,扯着嗓子在院子里喊开。随着她的叫喊,宫里的侍卫、马夫,语焉、骆明举扶着左润芳相继冲出屋门,惊慌之下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打开院门,这一瞬间街上已挤满了逃难的人群。
“爹,不能坐在家等死啊,咱们也跑吧”骆清焉六神无主地望着爹爹。
“别慌,拿上值钱的东西,将门锁好,向城外的高地跑”骆明举显得很冷静,毕竟做过县令,经过一些场面。
骆清焉乖乖在听从爹爹的吩咐,麻利地准备好一切,然后一起汇入川流的人群。
本来几个人一起拉着手,但没多久,便被人潮挤散,骆清焉死死抱住娘的腰际,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死,也不能让娘一个人孤零零奔赴黄泉。
城外不大的高地,早被人挤得没一丝缝隙。她推着娘亲努力想要挤上去,可是人群就象一堵坚实的墙壁,任她怎样用力也是徒劳。她绝望地嚎啕大哭,可是没有人理会,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绝望,一样的泪流满面。
大雨依然哗哗地往下堆着,在神密的大自然面前,人渺小得甚至不如一粒黄沙。
“大家不要惊慌,大家不要惊慌”雨雾中突然传来一群齐齐整整的呐喊。
哭声减弱,人们都向着声音来处望去。
透过雨链除了能看到影影绰绰的大队人众,其他什么也不能辨别。
“皇上派的各地增援已经赶到,河边的缺口已堵死,大家不要惊慌,雨太大,都回家吧,小心生病”齐刷刷的喊声清晰的传入众人耳内。
人群立时象炸了锅一样,不住有人高呼“皇上万岁,皇上万岁”,骆清焉搂着娘,喜悦伴着甜蜜在心中欢快流淌,这个万人景仰的男人啊,自己怎能不爱?
官府的安抚虽然让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高地不敢冒然回城。只到天空发白,才三三两两结伴相扶着回去。
骆清焉四处找不着走散的家人,只好独自扶着娘亲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走去。
城里到处是积水,有的地方深到脚脖处,有的地方竟能淹没膝盖,骆清焉艰难的扶着娘亲,好容易走上那条门前的小路。
忽然看到,自家门前静静站立着几十个人众,一式的蓑衣,齐齐整整。她心一跳,第一念头就是难道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不觉搂着娘加快了脚步,走到近前,刚想开口询问,只见人群中一人用手慢慢挑起头上宽大的斗笠,露出一张从容淡漠的颜容。
熟悉的魅笑浅浅地挂在楚天狂嘴角“傻瓜,开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