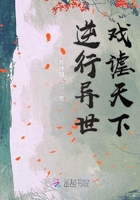月奴道:“是我有一次去买东西,看到张麟从她院子里出来。当时我还以为张麟是个好人,没有多想。先前我体谅她寡妇艰难,帮过她不少忙,与她有些交情来往。她自以为小心谨慎,却也被我看到过一回。”
那妇人彻底没了主意,此时一心只顾着撇清自己,哭道:“大人明鉴啊,我是被逼的。我一个妇道人家,死了男人,张大老爷说他会真心待我,做我的靠山,我我、我也是没办法呀…”
月奴红着眼眶道:“没办法你也不能害我呀,你这是要我死。”
“我错了我错了,妹子,我们以前关系也不错,你帮我说几句好话吧。”她哭得眼泪鼻涕一包糟,拉着月奴不停磕头。月奴本就强撑着跪在那里,被她一扯也歪倒在地。
谢大人挥手道:“先收监,回头再仔细审过。”捕快立即上来把她拖出去了。他此时笑意全无,看着张麟道,“张麟,还有何话说?”
“大人,不能听她一面之词啊.....”
“带上来。”不等他说完,谢大人便招呼衙役押上来一批人,正是清宁放倒的那些张麟爪牙,这位谢大人,手脚倒也不慢,他道,“的确不能听信她的一面之词,这些人,我会好好审问的。”
“大人。”张麟喊了一声,在跪下去的一刹那突然暴起,右手屈成鹰爪捏住了谢大人的喉咙,左手按在他的腰窝上,厉声喝道,“都退开,让条路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他。”
东宝眼见主子被擒,一时也慌了,忙呼喝着让众人让出一条路来。
张麟押着他往外走,眼见就要走出祠堂大门,脸上不禁露出喜色。突然膝盖弯处一麻,控制不住跪倒下去。他这一跪,旁边的捕快立即扑上来,将他绑了个结实。
”啊,你们放开我,你们....“东宝顺手一条破布,将他张大的嘴给堵上了。
谢大人觉得喉咙快要被他掐断了,此时忽然得救,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转头看见那位出手相助的清瘦少年,忙谢道:“多谢多谢。”
谢大人让人给范月奴松了绑,清宁这才看清她的长相,心脸杏眼,确是个难得的美人。只是受了折磨看起来十分憔悴,眼睛却明亮得似能一眼照到人的心里。她和清宁的目光对上,微笑着点了点头。
谢大人朗声道:“张麟作恶多端贪赃枉法,杀人谋财罪无可恕,家产尽数没收,贪污细节本官查清后会张贴出来。张范氏无罪,是被冤枉的,回家休养去吧。”
族中长老此时才来,听了前因后果,只叹着“造孽造孽”,和谢大人见了礼又安慰了月奴一番,步履蹒跚地又回去了。族人们见这结局,议论纷纷之余也就散了。
月奴让人把哑巴先抬回去救治,对谢大人郑重地行礼,道:“多谢青天大老爷为民妇申冤做主。”说完不顾阻拦又叩了三个头,这才起来,已是泪盈于睫,再是铁石心肠的人看她这个模样,也忍不住心酸心软。
谢大人有些不好意思,道:“夫人不必如此,查明真相为民申冤是本官的职责所在。”
她道:“话虽这么说,但大人此举对民妇恩同再造。大人若不嫌弃,便请与这位少侠到府中用饭歇息,让民妇聊表心意吧。”
先前行事潇洒的谢大人此时却犹疑起来,道:“这,不妥吧,怕会给夫人招来口舌是非。”
倒是月奴大方笑道:“身正不怕影子斜,看大人刚才行事也并非小气拘束之人,怎么一下像变了个人似的。”
她此时外形虽然狼狈,一笑开却别有一种朗朗风姿。清宁立即想到一个词——侠气,她没想到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妇人身上看到了。
清宁道:“大人,刚才我也前前后后听了。张麟说,张宅里有下人作证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和,张夫人私下诅咒夫君.....”
月奴变色道:“怎么?你们真的相信?”
清宁知道她误会了,摆手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张宅里有吃里爬外陷害主母的人,夫人可知给出这番证词的人是谁?“
月奴茫然摇头,不安地道:”我只当是张麟胡编的,张宅里虽然多有不服我的人,但是诬陷我谋害夫君.....不会吧。“
清宁笑向谢大人,道:”大人为民审冤,不想去一探究竟么?”
谢大人道:“好,咱们就去把这奸人给抓出来。”
清宁对他们颇有好感,自然没有不同意的。
一起去张宅的路上,几人互道了姓名来历。清宁此时男装打扮,心里早已决定,以后不再用白清宁这个名字,免得惹了祸归结到白家头上,便恢复本名陆如璋。这位谢大人名叫谢允中,取允执厥中之意,看他言行坦荡,倒也名副其实。月奴嫁进张府的确是为给张少爷冲喜的,对未来的日子她本不报期望,谁知两人性情相投,感情一日好过一日。好日子才开了个头,他就命归黄泉了,也只能叹这位张少爷实在是福薄得很。
张府中人早得了信,都到门口来迎接她,跨火盆放鞭炮,一时热闹非常。
月奴自然要先去梳洗换衣。允中和如璋在大厅等候,丫鬟们争相捧了茶水点心进来服侍,眼光偷偷地在两人身上来回打量,个个粉脸桃腮窃窃私笑。如璋确实有些饿了,那几样点心制作得精巧味美,她吃得津津有味,完全没注意到丫鬟们的小动作。
谢允中二十有二,见多识广,将丫鬟们的心思看在眼里却也不太在意。见如璋吃得认真,笑道:“陆兄是哪里人氏,这行色匆匆的是要到哪里去呢?”
她对东岛之外的地方并不熟悉,还好记了几个地名,道:“莲州人,我要到京城去办点事。”
“莲州?莲州宋家很有名,陆兄功夫了得,莫非是宋家的什么人?”
她摆手笑道:“不是不是,我这粗浅功夫,可别坏了宋家的名声。”
他笑道:“陆兄谦虚了。本来还想着你若能留下,帮帮我才好呢。”
她打趣道:“谢兄身边三百多个带刀护卫,还用得着我?”
他道:“阵仗唬人而已,真遇到高手他们都是小菜,再说我正要打发他们回去呢。”
“像我这种孤陋寡闻的人也知道幽云谢家的名号,若你想要,什么样的高手请不到。”
他笑道:“确实如此,可我想要的是伙伴是朋友,不是只保护我安全的随从。交朋友嘛,看的就是眼缘,陆兄你很合我的眼缘。不知,你愿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她笑道:“我要是不愿意,早就走了。”
他大笑,举茶道:“好好好,且以茶代酒敬陆兄一杯。”
“两位聊得好开心啊,不知是什么高兴事。”话音刚落,着月白衣裙的清瘦身影春风一般从厅外飘进来。月奴身在孝中,所以淡妆素衣,简单的发髻上只以米珠银钗装饰,看起来格外清丽亮眼,“久等了,我已命人备好酒菜,两位请。”
三人到饭厅,美酒佳肴摆了满满一桌。月奴执意请两人上座,坐定后又郑重地敬了一回酒,这才开席。
在一旁服侍的是个中年人,长得白白胖胖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据月奴的介绍,这是张宅的管家,唤张伯。他十分殷勤,不停地为众人布菜倒酒,如璋却不喜欢他,总觉得他眯缝着的笑眼中闪着精明和算计,这大概就是谢允中所说的不合眼缘吧。
酒过三旬,那张伯笑道:“府中有丫鬟略通音律,要不要请进来为两位贵客弹曲助兴?”
如璋的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月奴道:“不必了,服中怎可弹乐奏曲,不知道的还以为府里有多大喜事呢。张伯,这里有颦儿和笑儿在。你不必伺候了,歇息去吧。”
张伯笑着告退。他一走,其中一个丫鬟便轻声啐道:“少爷在时便什么都捏在手里,如今少爷走了,我看他越发把自己当主子了。”
月奴斥道:“颦儿,胡说什么。”微笑着向两人道,“平日里我也管不太住她们,叫两位见笑了。”
见那颦儿脸上仍有不忿之色,谢允中笑道:“颦儿笑儿,一颦一笑倒是有趣。”
月奴道:“她们是我嫁进来后相公新买进的人,名字也是他取的,只说…”她顿了一顿,一抹凄然的笑稍纵即逝,应是想起了夫妻恩爱的旧事,“只说是两个好名字。”
如璋怕她伤心,岔开话题道:“倒不怪颦儿,我看这张伯的确不好,有他在,只怕你以后不好掌家啊。”
几人虽是初识,但言语脾性相投,月奴也不掩藏自己心中的担忧,叹道:“何止张伯,这府里的下人有几个将我放在眼里当成主子的?”
如璋心念一转,道:“若想试探他们有无二心,我倒有个主意,你想不想试试?”她附在月奴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月奴一边听着,一边面露欣喜之色,谢允中听不分明,问道:“干嘛这么神秘呀,说出来让我也听听。”
月奴掩唇轻笑并不说话,如璋正色道:“小心隔墙有耳,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