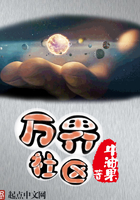顺毅侯府里韦长承叔侄三人正焦急等着韦长恩回来。他们清楚,这事做得是惊险至极,事发突然,既没有得到太后的首肯,也没有在朝堂上熟络各路关系,正是趁热打铁。如果成了,萧父必然是再无天日可见,可朝堂议政是瞬息万变的事情,韦氏叔侄知道,吴王本就是以萧父来掣肘韦氏,这次主动出击如果失败,说不定便是家族沦落的开始。叔侄三人先是在堂屋里喝茶等着韦长恩归来,久等不见,先是派了小厮去大门口张望,接着三人也陆续到堂屋门口期盼起来。
日头渐盛,等到日上三竿,秋日寒气渐渐散了,韦长恩才坐着马车慢慢悠赶回家。韦长承见兄长一副轻松活跃姿态,便知道一定是官场得意,他没等韦长恩坐稳,就拉着儿子急忙鞠躬作揖:“恭喜大哥旗开得胜,终于除掉眼中钉肉中刺!”
韦长恩没回应,只是叫小厮去传唤,赶紧上一壶茶润喉。
这样又叫叔侄三人不明白,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韦长承心里疑惑,可看着兄长铁青的脸庞,又不敢多问,便给韦应雄使眼色,示意他先试探试探。
“父亲是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吗?”
韦长恩仍然没有立刻回复,喝了一口温茶,才缓缓回道:“亦好亦不好。我今日尚未上朝,太后已经知道这事,没等我走进宣政殿,就让嬷嬷把我叫到寝宫,截了昨日递交的折子,让我放弃状告。”
韦氏叔侄三人一惊,他们知道韦太后向来是希望韦萧两族和睦,可如今大好的机会错过了可就没多少机会再来。
“下朝的路上,我遇到了在吏部的文安县侯,他倒是献上一条妙计。原本太后让我放弃状告萧县伯,还要提携他儿子做官,我当然心里不悦又不敢不从,文安县侯提议让萧家的儿子去做吏部的监察督办,萧家父子素来不和,可借他之手,挑拨父子关系,我们亦可继续谋划,岂不美哉?”
这样一套谋划确实是攻心之计,可韦应雄却仍有些忧虑:“我不怎么听父亲提起过文安县侯,他和我们府上并没有太多来往,会不会暗中给我们下圈套?”
“侄儿你可能不认识那个人,”韦长恩倒是一副很看得开的样子,“那个柯扶风是个墙头草,从来是见风使舵,如今韦氏如日中天,他那副哈巴狗样子就又显露出来。”
顺毅城侯其实也还没能完全相信柯扶风,在回来的路上他曾问:“如此计划,县侯刚刚在朝堂上怎么不说出来?”
柯扶风一阵憨笑:“其实刚刚朝堂上,我原本准备和众人一起,附和您,一把将萧县伯赶出官场。没想到城侯这样大度,在朝堂上一时竟忘了说出来。”
这样也好,萧晏诡计多端,如今这时候多一份势力就是多一份保障。韦长恩如今就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柯扶风。
“只是太后……现在越发不清晰了,”韦长承听了哥哥与柯扶风的一阵对话,隐隐约约感知到,韦长恩内心也逐渐流露出独当一面的心思,“太后大约是年纪大了,越发不敢闯荡,可哥哥您风头正盛,在朝堂上也是呼风唤雨,信众颇多,只要万象宫完全建成,到时候论功行赏,工部尚书对哥哥而言还不是唾手可得?萧县伯是绝对不能留的,有他在,咱们的事情一旦捅破了,可就功亏一篑了。哥哥务必还要早做打算啊!”
“也不知道这萧县伯给太后使了什么迷魂咒,竟就给他做了靠山。”
韦长恩听到侄子这样一说,原本还稍轻松的面庞上立刻就再次冷峻起来,狠狠盯向侄子,众人立刻安静下来。
韦氏自七国结盟前就是吴国的勋贵,祖上是将军出身,也是为国家开疆拓土的先驱。七国结盟,庞公变法,原先驻扎在国家边疆的将军们就成为圈养在京城的贵胄。虽然吴国先王们将各种特权分配给这些贬谪的公侯们,但韦氏的先祖们,早早就筹划起不能执掌军政后的打算,他们甚至只有把握权力,才是最稳重的财富。于是韦氏的姑娘们就进入了王室贵族的门庭。韦长恩的姑奶奶就已经是太后,而韦太后尚在闺阁中,就不和其他姑娘小姐专心琴棋书画,一心钻研些古籍兵策,颇有男儿风范。当年还是韦大小姐,就被自己的姑母相中,从太子妃一直到今日的太后。这其中不仅仅有家族的荣光,更有她自己的厉害。
“太后自有她的一番道理,此事暂且搁置,”韦长恩刚进门前的一番春风得意消磨得差不多,他不愿再听到谁提起太后,事情总归还是在掌握之中的。“最要紧的,务必在钦天阁重建之前,把从前安排下的事情全布置好!”
韦长恩深知太后是韦氏最大的保障,这不仅是她身居高位,和吴王母子情深,更在于,韦氏旁支们有不少仍然依附韦太后。如若和韦太后产生分歧,这位心思极为深厚的姑母不知道会使出什么手段。
当年萧父效仿庞公变法,欲以富强吴国,宋越巴辽四国联军兵临国都,萧晏又凭借自己智慧才能驱散四国联军,人称“小庞公”,风头一时无两。可太后深知变法不利于韦氏家族,竟以温柔刀、棉里针的手段,扭转乾坤。韦长恩心里一面佩服姑母心思深沉,手段狠辣,另一面对太后也是深深敬畏,如果不服,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行尸走肉吧。
一场大雨后,青城县的秋天越来越深,萧父也和秋日晴空般,越发深寂空洞。萧县伯软绵绵地踏上一阶阶石梯,双腿仿佛失去了骨骼的支撑,身体宛如病猫一般软塌。年轻时的他,还非常愿意登高,特别是秋高气爽,天朗气清的时候,登高让他放荡不羁的个性和广纳百川的志气有了短暂宣泄的机会。可现在物是人非,即使只是登上城墙都觉得力气不足,更何况去爬山远足?
一阵秋风吹过,只是在萧父的脸上轻轻刮过,连袖子都没能吹动,萧县伯不禁后退一步,打了个冷颤,扶住冰冷还带着点潮湿的墙垛,又觉得一股冷气顺着手臂钻进袖子,直逼躯干而来。柳叔赶紧递上披风,扶住虚弱的主人。
城外的芦篷瓦舍似乎远没有从前那么生气勃勃,炊烟和浣洗衣服的妇人远比从前稀疏,那些从前做工的放了假,这里原本应该更热闹才对,可原来还清晰听得到的孩子们的嬉戏打闹和女人们的骂街声都不见了。
萧父裹紧披风,望着城外绵延数里的芦篷瓦舍,叹了一口气,将满腔的无可奈何化作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陈白石心中不解,自己写的状词明明可以定萧父的罪,可事情已然过去三两天,却没有听到从腾城传出来消息。腾城去打探的门人回来通报顺毅城侯不仅没有弹劾萧父,还举荐萧源的消息,陈白石就开始魂不守舍。他幸而不和萧父在同一处共事,陈白石既不敢去请示韦长恩的意思,更连在街角看到萧父的马车也要提心吊胆许久。
威烈邑伯实在和他的封号名不符其实,他除了是个十足的酷吏,其实并没有能配上“威烈”之名的胆识。他是名门之后,可家族的荣光到他这里已经寻不到踪迹,年轻的时候因为得到韦氏的赏识谋得一个爵位,那时候韦长恩还时常称赞他雷厉风行。可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总觉得,像他这样虽然能干但没有家族势力的普通人,其实是走不通官运的。
“老爷不必这样惆怅,陶县伯虽然此刻一时没有发作,也许是城侯的缓兵之计,”威烈邑伯府里的门人典霍,人称典老虎,平时是陈白石最为信任的门人,他身材魁梧,体态略有些发胖,皮肤红里透黑,络腮胡子撑的脸凶神恶煞一般,“我看兴许是上次老爷提供的状词大多是咱们自己审出来的,那陶县伯一时狡辩,朝廷里才久久没有定罪。”
陈白石自然是知道这些,他真正担心的是,顺毅城侯自然是只占功劳不担罪责的,诬告之名最后当然还是落在他头上,即使朝廷不追究,可萧县伯也绝不是好惹的主。
“三天过去,府里也没收到任何指派,那一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都不在意。”
“最好是这样,”陈白石稍稍安心了一点,但终究是惊魂未定,“也算是逃过了一劫,你们再不要提起这件事!”
典老虎却环顾厅堂里的一众门人,大家都不言语,他眼珠一转,稍思考片刻,凑到陈白石跟前说道:“老爷,我有一事不知该不该讲……”
在获得陈白石的许可之后,典老虎缓缓说道:“那花坊的一众人等要怎么安排呢?从前送到贵客身边的乐伎可剩的不多了。”
“上次韦少爷说过,唱戏班子不必再操持了。她们原本就是‘死人’,没有户籍记载,死了就死了吧,如果你们有看上的,自带回家去,只是切记要收拾干净,别露了马脚。”
“钦天阁死伤的民工,按例是要补贴抚恤的。”
陈白石眉头一皱,原先被吓得煞白的脸上刚恢复了血色,这会儿又逐渐透出怒色,他现在但凡听到“钦天阁”三个字,总是心里一阵烦闷,“那就按照例法,你们拟好了帖子我递到户部就是了。这些事还要我教你们?”
陈白石的一阵怒喝吓退了一众门人,典老虎又说道:“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只怕这些刁民还没这么好糊弄,这外面就已经有乱民了,我怕…”
陈白石这一听才回味起来,原本他就是要提防着不能出了乱民,虽然想好了把屎盆子扣到萧县伯头上去,这会儿计划败露,可乱民还在,只怕还要想着法子去对付这件事。“你说得对,镇压乱民这件事还是要做,只是我一时也没有好的计划,容我再想想。”
“我有一计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