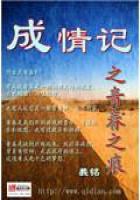最终他觉得必须作一些更加细致的调查,便冲姜平招招手说:“把尸体先抬到监区医院的停尸房,找外科的刘医生把铅笔取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姜平点点头,招呼着李铭一块准备去医院取尸袋和担架。临出监舍门的时候,他多嘴回头问了一句:“张头,要不要通知死者家属?”
“现在通知家属?”张海峰“嘿”地冷笑一声,“那我们三个人的警服都别想再穿了!”
姜平咂了咂舌,知道对方可不是在吓唬自己。监舍里发生犯人杀犯人的恶性案件,家属一旦闹将起来,从上到下的责任人都得脱一层皮!丢了工作还是小事,若以渎职罪追究的话,恐怕还得有牢狱之灾!
姜平等人早已见惯了监狱中的是是非非,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从管教身份沦为号子里的囚徒,这简直要令人不寒而栗。他扭头看看李铭,却见后者也是面如死灰,绝望得简直都快要哭出来了。
姜平比李铭年长几岁,见此情形自己反倒定了定神,拍拍对方肩头道:“没事,还有张头顶着呢。”
李铭略略一振,不过随即又苦着脸说道:“都这样了……张头能顶得住吗?”
“张头不是不让我们通知家属吗?那说明他还有办法。”姜平信誓旦旦地说道,既是在宽慰对方,也是在宽慰自己。
李铭听到这话,脸上的神色终于舒展开来。张海峰——这个在四监区混了十多年的老队长,现在已然成了这两个年轻人渡过险关的最后希望。
而张海峰此时仍在卫生间里看着小顺的尸体发呆。虽然刚刚在两个下属面前表现出了自己冷硬、坚强的一面,但他内心深处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正如张海峰此前对杭文治说过的,再有半年他就会被调到监狱管理局坐办公室,从此远离令人压抑不堪的监狱第一线。所以这半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所管辖的四监区决不能出一点乱子,否则他向往已久的安定生活就会从指缝中溜走。
上次车间内丢了铅笔,张海峰兴师动众,恨不能把整个监区都翻个底朝天,就是生怕那支铅笔会成为伤人的利器。不过和杭文治谈过话之后,他便把心放下来了。他相信那支铅笔就是小顺拿走的,并且已经随着货车被送到了监狱外。所以那潜在的威胁也就不存在了。他把黑子和小顺关了禁闭,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警告他们以后不要挑惹事端。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事端在两个人释放后的第一天就发生了,而且是如此地严重!
从亲眼见到小顺尸体的那一刻起,张海峰就悲伤地意识到:自己想要上调进管理局是不可能了。无论如何,在监区内部出现犯人的非正常死亡,身为中队长的他难辞其咎。现在他所忧虑的是自己还能不能从这场风波中全身而退。这十多年的日子都熬过来了,难道临到最后了却要跌个大跟头吗?
估摸着姜平和李铭已经走远,张海峰起身来到水池边。伫立片刻之后他打开水龙头将自己的脑袋凑了上去,凉水从他的发际漫过,浸湿头皮的同时也带来了冷冰冰的清凉感觉。
张海峰用双手在发丛中前后捋了两把,使得凉水能够浸漫到很多的地方。忽然间他的动作停住了——他把右手摊在眼前,愣愣地看着指缝之间的某样东西。
那是一根白发。
张海峰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白发,他难以抑制地感到一阵心酸。十多年了,在这座监狱里,他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成长为令最凶恶的犯人也会闻之色变的“鬼见愁”,有谁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又有谁知道他失去了什么?
这是出现在一个三十八岁中年人脑袋上的第一根白发,唯有他的主人能理解这白发中蕴藏着多少过往,又承载了多少希望。
良久之后,张海峰把右手伸到水龙头下方,水流立刻将那根白发从他的指缝中冲走。张海峰眼看着那根白发在水汪中漂流旋转,最后终于被冲入下水道,消失无踪了。这时他咬了咬牙,对自己说道:振作起来,这里是你的地盘,你还有机会!
姜平和李铭把小顺的尸体抬走之后,张海峰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估计那支铅笔从小顺眼眶里取出来还要一段时间,张海峰决定趁这段时间先抓一个424监舍的犯人过来审问审问。
这第一个审问的对象张海峰却没有选择号头平哥,他招来了杭文治。
在张海峰看来,杭文治是424监舍的一个另类,或者说,他是整个四监区的一个另类。他不像是一个奸诈凶恶的重刑犯,倒像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师。张海峰喜欢在这人面前抛却自己“鬼见愁”的外衣,而以一种更加接近正常人的方式进行沟通。
同时根据张海峰的判断:杭文治也是最无可能卷入监舍纷争的角色。因为他实在是太孱弱了,孱弱到难以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所以在这次事件中,杭文治多半会是个无辜的旁观者,而只有从旁观者口中你才能得到未经扭曲的真相。
杭文治被押进办公室之后,张海峰先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对方。杭文治被看得有些发毛,远远地低着头,神情略显紧张。
觉得给对方的压力差不多到位了,张海峰这才干咳一声,问道:“你说吧,怎么回事?”
杭文治惶然回答:“我……我不知道。”他这句话说得毫无底气,一听便是在敷衍撒谎。
“你不知道?”张海峰冷笑一声,“你是白痴吗?或者你觉得我是白痴?”
杭文治无言以对,只把脑袋埋得更深了。
张海峰知道对方既有顾虑,同时也存在着逃避责任的幻想。他决定先把对方的幻想击碎,于是便抓起桌上的一团东西,甩手一丢,扔在了杭文治的脚下,问:“这是什么你总该知道吧?”
杭文治看清那团东西正是平哥用来捆绑小顺的布条绳子,他的脸色蓦地变了,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张海峰。
“这是什么?!”张海峰加重语气再次问道,目光也变得更加锐利。
杭文治确实没想到张海峰这么快就把平哥藏匿的布条找出来了,他踌躇了片刻,知道有些事情瞒也瞒不住,只好老实说道:“这是平哥做的绳子……”
张海峰一拍桌子:“什么平哥?好好说话!谁做的?!”
杭文治连忙改口:“是沈建平,他昨天晚上用这根绳子绑小顺……”
张海峰“哼”一声,果然不出自己的预料,然后又问:“为什么要绑小顺?”
“沈建平认为小顺偷了黑子的铅笔,连累到整个监舍……还有他作为老大的面子,所以他要惩罚小顺,让小顺睡吊床。”
“这事都有谁参与了?”
杭文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吞吞吐吐的:“主要……主要是沈建平,还有黑子和阿山。”
“哦。”张海峰听出了话外之音,立刻追着问道,“那不主要的呢?还有谁啊?”
杭文治咽了口唾沫,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
张海峰心中暗暗好笑,心想:找这小子来审算是找对了——他真是一点应付问训的经验都没有,所有的心思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见对方还在磨叽犹豫,张海峰干脆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自己呢?有没有做什么?”
杭文治完全不会撒谎似的,苦着脸坦白道:“我往小顺嘴里塞了块抹布,不让他说话……”
张海峰冷言讥讽:“你可以啊!这才多长时间,也学会欺负人了?”
“我也是没办法。”杭文治为自己辩解,“小顺老向我求救,我不表个态度,沈建平他们会拿我一起开刀的……”
张海峰其实也知道监舍里的这些黑规矩:老大动手整人,大家都得跟着掺和两下,否则便会被疑为怀有二心。只是不知为何还有一个人杭文治一直没有提及,于是他又问道:“杜明强干什么了?”
这次杭文治回答得很痛快:“他什么都没干。”
“真的?”张海峰表示怀疑。虽然他也知道杜明强是个另类,但监舍里闹出了这么大的事,他真的可以独善其身吗?
“真的!”杭文治态度坚定,“他两边都没帮,我给小顺塞抹布的时候,他还拉着不让我去。”
“这才是聪明人啊!”张海峰用手指敲着桌子,感慨道,“你早该跟他好好学学!”
杭文治咧咧嘴,做出后悔不迭般的表情。
张海峰本还想多教育对方两句,但事分轻重,今天已无暇多说。眼看铺垫得差不多了,他面色一凛,开始把话题切入最核心的部分:“是谁把铅笔捅到小顺眼睛里的?”
杭文治一惊,随即一个劲摇着手:“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张海峰当然不能认同这样的回答,虎着脸驳斥:“你瞎了?”
“我睡着了。”杭文治解释道,“而且大家都睡着了,沈建平一早起来才发现小顺出事的。”
“是这样的?”张海峰对这个说法有些始料未及。他本以为是平哥和黑子等人纠结在一起残害小顺,中间不知如何矛盾激化,或者是哪个人失了手才导致小顺死亡。现在照杭文治所说,却是有人趁大家睡着后偷偷杀死了小顺。
“嗯。”杭文治又更加详细地说了一遍,“昨天晚上沈建平他们把小顺吊在卫生间里,然后大家就各自睡觉了。我睡得死,到清晨的时候被沈建平吵醒,看到他按着黑子在打,然后才知道小顺死在卫生间里了。
张海峰从杭文治的表情判断对方并没有说谎。监区生活起得早,生产任务也重,犯人们晚上普遍睡得很沉。而小顺双手被吊起,嘴里塞着抹布,已全无反抗、呼救的能力。这时若有人趁着半夜偷偷行凶,其他人虽然同处一个监舍也很难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