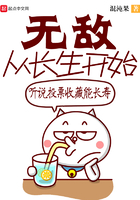半吊子水的太极拳响叮当,临场发挥却又还有几分样子,赵步笙心里难免一甜。
林客啻拳脚倒也硬,当赵步笙稍有怠慢时刻,来不及卸下的力道撞得手甚疼。想到此刻,赵步笙又伸展了一下手臂,揉了揉手腕。
将林客啻三人的惊异尽收眼底,想必自己也是不错的,走起路来也轻快不少。
嚯嚯,赵步笙向着空气挥出两拳,脚下一跳一跳的,脸上掩抑不住的笑容。
路上偶尔碰到一两个白鹤派的弟子,赵步笙便会放慢脚步,“无意”地将他们的话收入耳中。
偷听,这可是赵步笙练就的本事,当初上学的时候,宿舍聊天便是如此。
渐渐地,这座山被称作什么,弟子们大多在何处修炼,很多杂乱的事情也就被他牢记在心了。
据闻寻幽山的东面修建有一处崖间长廊,危石怪松掺杂,风吹摇摇欲坠,走起来很是刺激。
崖下乃是白色的波涛滚滚,其声惊响震天,在两山间回荡不绝。说这事的弟子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听这事的弟子满眼崇拜,赞不绝口。
去瞧瞧。
赵步笙原本对这两个家伙嗤之以鼻,觉得在这样的长廊上一游也并非大不了的事情,可是他错了。
站在此地,抚膺长叹。
这是美其名曰的长廊,不过是数尺之宽的木板插入崖间,其外还无护栏之类,大风刮过都在摇晃。
有一点倒是真的,崖下滚滚波涛,声浪如鼓锤心,砰砰地响,停不下来。
长廊之上无一人,赵步笙也不知白鹤派修建这长廊的意义何在,兴许是嫌弃养的闲人太多,想要暗中处理一些。
灵猴原是站在赵步笙的肩头,挺着身子,神气十足的模样。不过此刻,前方是悬崖千百丈,崖下声如雷霆,吓得那猴子挂在赵步笙后背,只露出了脑袋偷窥。
长廊之上无一人。
身后倒是有三两人交头接耳,对赵步笙指指点点,至于说些什么他可没心情去管。
“喂,小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这长廊可不是随便能走的,像你这样无异于寻死。”
全做未曾听见。
赵步笙向来是个胆子很大的家伙,有时不知天高地厚,只要自己愿意就向前行。譬如,现在。
长廊修了多少岁月,赵步笙可是不清楚,但他此刻便是愿意去走。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身居高崖之上的悸动,兴许害怕,恐怕更多的是活着的感觉。
再次向黑暗,陡峭的崖下望去,晃落的石头跌落白花花的水中没有半点回响,一切都被潮浪吞没。
恐怕无人知晓赵步笙为何踏出,只有他自己知晓,那便是从心。他若想起的事情便会去做,踏路何问终点?
脚踩在灰白木板上并不太稳,身子都在摇晃,仿佛浪潮中的一叶扁舟。
长廊在白鹤派之内还有其他的称谓——通天,通天派的通天。长廊盘踞如龙,乘龙一步登天路。
每个地方自有它的传说,或是美好,或是悲伤,都在人的心中。而这长廊恐怕也汇集了多少外门弟子的希望,一跃为龙的希望。
刚踏上一步,赵步笙便是退了回来,摸了摸鼻子,潇洒转身离去。
耳旁的讥讽笑意更盛,也再未有掩饰,也都是道赵歩笙装模作样,却又是胆小如鼠。赵歩笙顿下步伐,仰天一声哀叹。这些井底之蛙,又怎么知道鹏鹰的心思。
方才的那位聂长老可就在远处的树梢上负手而立,远远地观望着自己,莫要做太优越的事情。
聂长老以右手抚着长须,目光投过重重叠叠的树叶,落在了白衣少年身上,又或者是白衣少年肩上的那只凶猴。
满面肃穆而庄严,双目微虚,那只遒劲有力的右手“啪”一声拍在自己的屁股上,便是咬牙切齿道:“不知死活的虫子,堂堂聂长老的屁股也敢亲,简直找死。”
右手在自己的身上狠狠地擦拭一番,再次抚着长须,若有所思。遥想数年之前,寻幽山还是聂长老一手遮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哪知春光明媚的一日,自东方有白鹤飞来,很大一只白鹤,那是聂长老命运转折的一日。
白鹤白中透着一点红,直直向着白鹤派主峰而去,何其嚣张。聂长老虽说执掌外门,那可是严守白鹤派的重要力量,岂能让外人轻易入内?
一声怒呵直斥云霄,方圆十里莫不以为惊天雷响,令众外门弟子皆是抬头望天。
怎奈何外门弟子修为太浅,仰天却也见不得太多,也多亏如此。否则恐怕白鹤派内便早已经传遍了奇闻异事,诸如“外门聂长老一飞冲天,须臾之间重返外门”;若是修为再高深的弟子,那便是传出“聂长老一怒拦截外入者,灰猴儿一拳痛扁老头子”。
总之,大概,也许经过便是如此。
从天上下坠的那种感觉,可是很难说的。
每每回想到此处,总是老泪纵横两行,屁股不由一紧。那一日,要知道聂长老也算知道,屁股总归柔软,石头总归坚硬。
犯我屁股者,虽弱小,必诛之!聂长老目光如炬地盯着右手残存的血迹,在棕灰的树干上摩擦,发出沙沙声响。
徐红襄的来历挺神秘的,聂长老如是回想。
不过那白衣小子又是何人?灰猴儿在白鹤派内可是不受制于人,那是比太上长老还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家伙。
不服就硬干,打到人服为止。从未见过灰猴儿那般对人温柔,难道白衣小子与徐红襄同出一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当聂长老目光再次投射向长廊处,空无一人,人呐?猴呐?去了何处?
东张西望。
赵歩笙敢肯定,那老头子已经没在自己身旁了,虽不知他在何处。手中拿着一根弯曲的棍子,棍子的重量但也不轻,或者说是那只兔子很肥。
面前的火焰烧得正旺盛,噼里啪啦地冒着火星子,弥散的香味令猴子口水嘀嗒在地上。
灰猴子支支吾吾个不停,又是抓耳挠腮,又是上蹦下跳。赵歩笙虽将一切收入眼中,却是对它装作视而不见,口中哼着悠扬的小曲,怡然自得。
“黑黄的脚丫鞋外跑,左脚挠挠右脚挠,食指的脚香鼻尖绕,闷头深吸气一口,啊,神清又气爽;没毛的头顶仰天笑,哪顾苍天鼻涕掉…”
太庸俗了,也不知是哪个流浪大江南北的乞丐写的,不过赵歩笙觉得有趣,也就在沿途学了过来。不过那人但也积极乐观,这样的清贫日子,尽然还如此潇洒。
想想自己现在,独坐山野之中,随手逮着一只乖乖的兔子,把它架在火上烤,香气扑鼻,那简直不要太幸福了。
虽然自己不再需要凡尘俗世的五谷杂粮,可总归是人嘛,口腹之欲还是得满足,如若不然,长命千年万载,意义何在。
金光的油流得焦黄的皮上到处都是,也不知是火花的声响,还是脂肪炸裂的声响,总之清脆。
赵歩笙满意地瞧着自己的作品,迫不及待地撕下兔子屁股,笑嘻嘻地递给灰猴子。满心欢喜的灰猴儿的毛爪在空中凝固,却怎么也没借过那不能入口的玩意儿。
这东西能吃?成天瞎扯淡,它跟着徐红襄就从不瞧这东西上眼,喂狗都不能拿来喂猴子。
“这猴子还真是奇怪,不喜欢吃肉,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我当以为急不可耐。”赵歩笙将兔子屁股随手一扔,又是嘟囔,“这屁股是给人吃的?灰猴儿不吃,还当真有点可惜。”
嘴上虽然说着可惜,可赵歩笙扔掉它却也没有迟疑,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他将木棍收回,光溜溜一片,瞧这木棍多么精致,简直就是上天的杰作。
话说回来,木棍上的兔子肉倒是不翼而飞了!再转头一扫,凝固在那一处的灰猴儿也没了踪影。
去他香蕉加巴拉拉小魔仙的,这畜牲也太不是个人了,竟然卷起烤兔子走人。四周颇为安静,没有一只猴子在叫唤。
只有地上的一团火苗在窜动,变化出各种形态。赵歩笙还是平生第一次被一只猴子戏耍,多么大的耻辱啊。
愤愤不平地砸下手中木棍,嘴里骂骂咧咧,啐处一口清痰,砸在旺盛的火苗中。
不远处却是窸窸窣窣的声响,树影晃动,就好似被拨动。赵歩笙冷冽一笑,悄悄地向那深深的树丛走过去,缓缓而轻轻地拨开。
那是一张很青涩而充满愤怒的小脸,红中透着白,白中透着红。那一双眼睛由惊讶转为愤怒,惊天动地的声音仿佛要从那小嘴喷薄而出,却转而化为“呜呜”声。
赵歩笙死死地捂住小女孩的嘴,令她不能吐露半个字,纵然她在挣扎。也难怪赵歩笙觉得这个小女孩有些面熟,刚才抓走兔子时,就是这小女孩喊了几句。
至于喊了什么话,却没听清。总之,冤家路窄。不过还有一句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将这青衣小女孩夹在腋下,赵歩笙开始了对她的“谆谆教诲”。
“小姑娘,我们两个人之间恐怕是有些误会。误会呐,是需要解开的,需要我们静下来慢慢地说。你这样大吼大叫,是不对的…”赵歩笙语气轻缓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