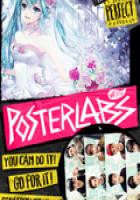我离开学校前往聚居区的那天,正巧迎来了这年的第一场冬雪。
我在操场溜达来溜达去,穿梭在落雪间,快快乐乐地任雪花落了满肩。
我最终选择遵从陆离的安排。他说得对,我一个人在这里没有办法活下去,没有别的原因,仅仅是孤独就能毁掉一个人。
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脆弱。
到头来,事情没有丝毫改变,我依然无处可逃,任性行事也没有益处,唯有顺从。
因为我没有勇气放弃生命,这一点,同样是人与生俱来的脆弱。
好吧,我屈服般地承认,不管我怎么下意识地拒绝这一点,我还是无法回避这个事实,不管是不是复制品,我就是一个人。
我躺在雪地里,看着极远处,一架直升机破风雪而来。
冰冷的雪地在带走我身上的温度,我咯咯笑着从口袋里拿出那半张纸片,读了又读,再把它塞回口袋。
那天,我关掉机器以后,像行尸走肉一样把记忆拷贝塞回文件袋里,却又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
是从笔记本里撕下的半张残页,布满娟秀的字迹。我草草读了,发现居然是一首短诗。
……
假以名之灵魂
方知肉体之脆弱 精神无从栖居
只有存在 方是永恒
周遭的人死去 而你们永生
这是你为之背负的罪过
你的命运将是孤独
我看到最后,几乎笑得不能自己,但下一刻忽然如箭穿心,痴痴地拿着这张纸,呆若木鸡。
仅仅是因为刚刚我想找人一起分享并嘲笑一下这首狗屁不通的诗,却发现这儿除了我一个人也没有。而且我不知道它是认真的,还只是悲观的预言。
回到聚居区之后,我做了全套的测试和检查。应该是事先被嘱咐过,所有的工作人员对我都很尊重客气,但眼神仿佛都在发射注意非我族类的警惕信号。
我乖乖地配合了,并在之后很快得到了自由。
后来他们告诉我,我的身体状况好得出奇,像一个十来岁的儿童一样充满活力。
我早就意识到了,我出乎寻常的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身体素质甚至敏感的五感。我比一般这个年纪的人类生理状态出色许多。这意味着,可能我会有超出正常值的寿命。
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是说,那又怎样呢?
我被安排住在一个算得上宽敞的个人公寓里,有独立合法的身份,每月账单都记在陆离或者周婉的名下,暂时无所事事,虚度享用大好年华。
时间在感官上顿时被拉长了几倍。在这堪称漫长的几个月里,我的记忆一点点恢复了。
是,准确地说是曾贝贝的记忆一点点恢复了。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起以前发生过的事,但是相当古怪的是我无法把她的记忆视作我的。曾贝贝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个陌生的异物,虽然存在,但不是我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古怪的体验。我“是”曾贝贝,我长得和她一模一样,每一个细胞都相同,我甚至有她全部的记忆,可是我仍然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孤立的个体。
显而易见,之前出现的种种奇怪的既视感,想必就是这些尚未浮现的记忆在作祟吧。想必它是存在于通过复制得来的相同的大脑里,随着时间流逝,才慢慢浮现。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毕竟多说无益,只会徒增烦恼。
唯一我可以证实的是,章教授的预感没有错,这个项目拥有命定的失败结局,它只会生产出像我这样畸形的果实。
事实上我和陆离也没再怎么见过面。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和周婉一块被关在特护病房,虚弱得要命,一天里没多长时间是清醒的。
周婉去世之后,他基本二十四小时都在昏迷。
我当然没去参加周婉的葬礼。
我知道陆离总有一天要死,挺不愿意看见他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样子,所以也很少去探望。上一次去看他还是两周前,我站在病房外面,隔着门上的玻璃看了一会,护士说他一天也见不得能醒一会,我想了想,也就一个人走了。
我倒是没想到,这会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今天晚上接到电话时,我正在喝闷酒,大提琴的声音在客厅里低沉地回旋往复。无所事事和孤独一样会蚕食生活,可我不知道要怎么医。
来电的是陆离的律师。接起这个电话,之前我酝酿起来的那点醉意都被吹跑了。
我站在窗前,夜里月色皎洁,刻骨冰凉。
陆离是傍晚七点去世的,正是晚饭的时间。我那时候在干嘛?我不记得了,可能在睡觉。无事的日子里,我一天睡十多个小时,昏昏沉沉,不知日月。
传导情绪的那根神经必然是被切断了。第一个涌上来的感觉不是悲伤,他迟早要死的,不必等到这个时候再来悲伤。我张了张嘴,只觉得很茫然。
过了一会,我忽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片人与人的汪洋中,再没有人能牵住我,固定住我。
我与这个世界的纽带被彻底斩断了。
“喂?曾小姐,您还在听吗?”电话里传来律师的声音。
“在。”我回答,沉默着听他复述陆离遗嘱的内容。
他的所有个人财产,被划到我名下,归我全部所有。听着律师念完那一串数字,我的喉咙像是被人塞了块石头。
电话里,他还在继续念除现金以外其他财产的清单。
“您有什么疑问吗?”
“哦。哦……”我如梦初醒,“没有。没有……”
“这里有些手续,需要和您面谈。”
“我知道了。”我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一味应承着,巴不得能早些挂了这个电话。
没想到,一夜之间,我竟然变成了一个富婆。
我挂了电话,对着自己在窗户上的模糊影子惨然一笑,一时竟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一出荒诞的剧目,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停止上演。但从今日七时起,幕后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人。
之前喝的那点酒这会又上了头。我浑浑噩噩地笑着,和着音响里隐隐约约传来的音乐声,稀里糊涂地唱起没谱的曲,唱得双眼模糊,口干舌燥。然后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客厅恭恭敬敬地鞠躬,宣告这一幕的结束。
虽不忍心,可我只能告诉亲爱的观众,接下来的都将是无趣的独角戏。
我给杯子再斟满焦黄的酒,在月色下它多了几分苍白。
我对着这弯新月高举酒杯,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复制人。
最终我独自一人,将这杯苦酒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