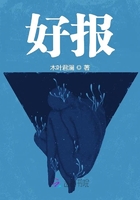穆晚晚摇头笑道:“再远些……再远些小妹便与大哥多说会儿话。”穆晚晚一边说一边亦脚下移动,那绸衫男子只顾盯着穆晚晚的俏脸看,连自己何时掉转了方向都不自知。
几步下来,已是穆晚晚背对着前溪的方向,与对面的男子相对,男子的后方是后溪的方向。
穆晚晚边退边继续搭讪:“大哥叫什么名字?”
听得小娘子主动问他姓名,绸衫男子心中仿似乐开了花,心想此事有望,不觉脚下一滞,双眼含春,又想起自己不同于常人的身份,不由傲然挺胸,道:“我乃里正之子,赵仁是也。”
赵仁说完正洋洋得意,却只看得眼前小娘子面目一变,满目惊恐望着自己的身后,仿似在他的身后看到了什么骇人的鬼怪妖魔。
自己心中也不由得一凛,扭头往身后瞧去。
一弯溪水,一路碎石,水平风静,鸟寂林默,看不出什么异象。
心下松弛,回过头来笑道:“小娘子花眼了吧……”
然正目一看,近前哪还有小娘子的半个影子,端着洗衣盆的美娇娘早已远在数十步开外,只望得一线倩影行步如飞,如穿云度月,远远离了去。有心继续追赶,怎奈自己腿脚不便,况如此距离,无论如何是再追赶不上的了,不由得狠狠踢起一窝碎石,恨得牙痒痒。
穆晚晚端着木盆行步如飞,待人群渐近,这才放缓步子,又恐人看出异样,经过桥头时特意回禀陈老太,忘了拿皂角,这才去了又回。陈老太不疑有它,只嘱咐穆晚晚家去好好休息,今日不必再浣洗。
穆晚晚回得家来,倚窗深思,倒不是后怕,此等小事还不需挂在心上,如今既已知了他姓名,哪日得了便利,设计处置便是。
此刻细细思量的是有水无鱼后山妖怪这两桩事或与里正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如果她推算得没错,这两桩怪事的背后推手,正是里正。
其一,桃村有水无鱼,算是有伤民生之事,作为里正,自是得禀报上峰,一则在上峰面前显得恪尽职守,二则也好与自身撇开关系——若哪日上峰于别处先听得了这风声,里正的罪过便不小。
其二,有水无鱼,算是一桩事,更有厉害关系的是后山的妖怪传说,此等祸乱民心的事件,更是得第一时间禀知上峰,设法解决。
穆晚晚之所以对这青蓝大陆的风俗人情悉数尽知,得益于原主秦月的生前所知。她虽对秦月本人的人生经历无半点自知,青蓝大陆的风俗人情却如教科书般悉数存于脑中,这也算是件奇事。
既深知风俗人情,自然对这里正的关系职责一清二楚。
有水无鱼,妖怪传说这两桩事,其实之前也是往里正处思想了的。
只是一则她伤好才愈,出来行走不过数天时间,对桃村的人物干系知之甚少,里正的为人处事更是一无所知,不敢冒下结论。二则深知乡野之处,虽然件件条条规定了里正的职责义务,但是执行到乡野便散漫许多,一些明文规定也做不得数。里正所执之责,全凭个人心念,往往出现人大于法的现象,规制上规定了出现有伤民生之事要上报,但若是里正自觉不是大事未报,村民也不会有疑它,一切唯里正马首是瞻,里正的话就远大于规制,几世几代都如此。所有这两桩事儿由于里正散漫或者自认小事而没得上报,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并未深疑里正。
如今既在溪边遇得了这里正之子赵仁,绸衣绸衫,华服玉冠,且品行不端。自她报出乃里正之子,穆晚晚心下便觉出所以然来。里正,绝非散漫渎职,极大可能是隐瞒不报,目的只有一个,用后山妖怪之说绊住村人脚步,令全溪之鱼皆拢于后山,尽归己有,所得之鱼,应自己悉数贩卖。所以其家才格外富贵于寻常人家,赵仁才有此不同于常的富贵打扮,要知道,里正的薪俸,一月不过一两银子,而赵仁头上的玉冠,少说也得几两银子,一家人不吃不喝,用几个月的薪俸买一顶玉冠,怎么也说不过去。
剥茧抽丝,牵绳动瓜,而今几乎可以确定,有水无鱼,后山妖怪传说,皆应出于里正之手。
后溪虽然无鱼,但是顺着源头摸去,那鱼定是被里正秘密隐藏了起来,或是改流到某处,或是隐藏于哪处山洞。日后细细探查,定能查出一二。
只是如何拨云见日,水里浮瓜,还得细细一番思量。她不愿做出头之鸟,却也不愿陈家二老日日恓惶度日,连吃鱼都是妄想。此事还得从长商量。
不觉日已正午,陈家二老归家,穆晚晚早已备好饭菜,陈家二老自是夸赞一番。又看得饭桌之上一颗滚圆的鸡蛋,穆晚晚禀明因由,陈家二老对花蕊自是一番感念。本欲让二老分吃了这鸡蛋,二老却坚决不吃,硬要她自个吃了。最后只得把鸡蛋分成三份,一人一份,陈家二老妥协,这才吃下,一家三口席间谈笑。
穆晚晚有意无意把话题引到里正之家,以便诸多了解,思量万全之策。恐二老忧思,一早遭遇里正之子之事自是隐去。
乡野农家,餐饭极其简单,午食不过几只红薯,两三只玉米面窝头,以及一碗山间寻来的野芹。
盐油自是金贵,大半海碗的野芹,不过飘着数点油花,陈家二老经年便是如此吃食,穆晚晚是这两天才是同陈家二老一样的吃食,虽清苦,倒觉得比油腻的鱼汤,更加香甜些。
其实依二老的意思,家里除了留作成亲之礼置办的银钱外,还余得十几文钱,完全还可以再买数天的鱼吃,奈何穆晚晚坚辞不愿,只好也便随了他们日日粗茶淡饭。
穆晚晚先吃完了饭,喝着一盏清茶。半老之人牙口不好,陈家二老还在细细吃着番薯,偶尔挑几根野芹送入口中。即便这野芹,往后也不容易得了的,野芹随春而生,随春而尽,眼看春尽,再寻得野芹,怕是不甚容易。
穆晚晚用茶盖掠去浮在盏中的几丝茶芽,桃村虽生活清苦,山中盛产的茶叶,却是一绝,即使只用家中井水泡了,亦觉醇厚轻浮,喝来两颊生香,自来到此处,穆晚晚便爱上了这清茶,每日饭后睡前,必得饮上一盏。
穆晚晚饮了一口,放下茶盏,答言:“如此,那里正之子原是如此十恶不赦之人。”
原来,刚刚陈家二老顺着有关里正的话题,里里外外将里正一家说了个明明白白。尤其又着重说了这里正之子,无赖至极的赵仁。
原来这赵仁之所以跛足,是因了有一日竟溜进了一家寡妇的屋中,却不想那寡妇是个刚烈有力的,硬是拿着切菜的刀把赵仁逼了出去,偌大的动静早已引得村民驻足观望,门口已七七八八站了些人。赵仁无法,只得爬上墙头,墙头外边长了一颗歪脖子树,他准备爬墙跳树而逃,却不想心中急躁,脚下一空,还没挨着树便直直从墙头上跌落了下去,摔断了一条腿。
而那寡妇看得赵仁落下墙头,生死未卜,想那里正定不会轻易放过她。又看门前乡邻悉悉碎语,指指点点,一时羞愤,竟回手一横,自个儿用那刀抹了脖子。
苦主已死,且膝下无子,叔伯兄弟又早已觊觎寡妇的房产,那寡妇生前又是个稀言寡语的,并无相交好的友邻相帮,赵仁又一再坚持只是看寡妇可怜,来送些银钱与她,却不想寡妇误会,执刀相砍,反差点伤了他赵仁性命,如今寡妇身死,也是她咎由自取。如此种种,人命一条,竟无人报官。
其实村人皆知此事有异,但奈何赵仁之父里正拿捏着本村数百户人家的身家性命,他若动动嘴,即使家里只得一个独子,恐也要披上战甲,舍父离母,应了徭役,去战场卖命。他若斜斜手,即使家里只得两亩薄田,恐那赋税簿上也得重重记上一笔。一边是手握生杀大权的里正,一边是孤苦无依的寡妇,孰轻孰重,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况这里正,并无实际诓害自家的错处,明眼里也都还过得去,于是自是都缄默不语。
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家檐上霜。人性凉薄也好,世道艰难也好,穷山僻壤之地,人人皆习得一手拂袖甩尘的好本事。
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寡妇,自己屋里惨死,一张草席裹着草草入葬了事。
“晚晚,若见到此人,必要远远避开为是,此等宵小之辈,我们不去沾染的好。”陈老太思及自家儿媳美貌,心中沉重,不由得放下碗筷,抚着穆晚晚的手,谆谆嘱托。
“里正家在村尾,隔着数百户人家,那赵仁又是个游手好闲的,日日在镇上晃荡,极少回村,也不会那么巧就遇上的。”陈老汉则不以为意。
看到陈老汉不以为意的姿态,陈老太登时心头火起,她这边忧思嘱托,他不但没事儿人一样,还来泄她的气。立马面目一板,出声呵斥:“小老儿懂什么!那赵仁无赖至极,咱晚晚如此人物,怎能让无赖脏了咱的眼!幸得今日谈及这无赖之子,正可告知晚晚提前防备一二,我这里正忧心嘱咐,你倒好,如此不放在心上,却倒吃得香甜!让你吃!”陈老太说着赌气起身,撤去饭食,临到门口,一只脚已然跨出了门槛,又意难平狠狠剜了一眼陈老汉。
陈老汉正欲夹菜,却盘去桌空,着实困窘,又细细一想,老婆子说的也甚有道理,是自己疏忽了。不觉面上腆然,轻咳一声背起手离了饭桌。
穆晚晚起身福礼,收拾完桌上的残渍,自去屋里小憩了。
春日易困,她好了的这几日,日日中午都要小憩一下。只是通常小憩前都会在房前院里闲走上几圈,以消午食。只是今日,不知为何,午食之后困倦得厉害,且陈家二老又闲拌了几句,伤了脾气。自己也不好再在他们眼前闲步。
倚在床榻上,只觉眼皮更加沉重,不消一会便沉沉入睡。只是这一觉并不安稳,许多景象如影画般在脑海中交替闪现。
金戈铁马,喊声震天,硝烟战旗,尸横遍野,狂风猎猎,鸦如黑云。渐渐地又听得琐碎的人声,嬉笑怒骂,激愤低沉。渐渐的一切又远去,只看到一座巍峨无比的宫殿,执着玉笏的群臣拾级而上,正中宝殿坐着一人,华衣宝冠,神采辉煌。仔细一看,竟是秦月的眉目。
虽是在梦中,穆晚晚却觉如亲身经历一般,一时觉得自己就是那宝殿正中坐着的人,一时又觉得自己只是漂浮在这巍峨画面外的一双眼睛——宝座上坐着的人是秦月,漂浮的眼睛是穆晚晚。当作为一双漂浮在画面外的眼神时,脑海中那个月下一袭红衣赤着双脚的秦月和眼前的这神采辉煌的秦月重叠在了一起,心里竟有一丝戚然,原来她生前为王之时,是如此气派威风,却不想天有不测,竟沦落成一个衣衫褴褛的孤魂野鬼,生死难归。
心中正凄然,却听左右群臣山呼万岁,声透屋宇,如回音般一遍遍响彻在雕着金龙的梁上。
穆晚晚只觉得耳膜欲裂,乍然睁开双眼,唤声仍不绝于耳,起身一望,却只见地上桌上甚至梁上,密密麻麻却又整齐有序,站满了拇指般大小的盔甲勇士,口中高呼国主万岁。
穆晚晚神思回转,心下清明,原来是拇指灵军觉醒。
昨晚之后,金铃一直没甚动静,她本就无心于此,也便没有在意,却不想拇指灵军此刻忽然出现。
穆晚晚眉心紧皱,只望着眼前密密麻麻拇指般大小的魂灵沉默不语。
山呼过后,这些拇指大小的灵魂仍单膝跪落在地,没有国主的允许,他们不能擅自起身,这是生前作为皇家死士弯刀武士的自觉。
静默在室内蔓延,许久之后,离穆晚晚最近,站在一列队形正中间的一个络腮胡子的武士抬起了头,望向靠在榻上,望着他们沉默不言的自家国主。
“国主,您……怎么了?”络腮武士试探着问道。
“你们就是拇指灵军?”穆晚晚幽幽开口。
闻国主如此一言,络腮武士心生疑问,国主这是怎么了,拇指灵军不是国主亲自炼制的吗?如今怎么却反倒问他?虽心有疑问,却仍殷切答言:“禀告国主,是的。”
穆晚晚收回视线,目光落在半拢着的粗布青帐上。
“我不是你们的国主,你们回去吧,或是回金铃之中,或是回地府入轮回转世,悉自听便。只是……不要再在我的面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