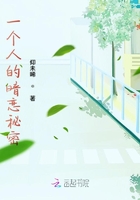(一)
一九七三年,香港,九龍城寨。
空氣中瀰漫着一股發霉混合煙草的氣味,天花板上的風扇有氣無力地扎扎轉動,醫生的聽筒被隨手丟在那張和世代一樣紛亂的書桌上,聽筒那圓圓的一方剛好垂到書桌旁那滿溢的垃圾桶內,發黃的醫生袍上點滴着幾處鼓油漬和麻醬,和醫生這個名字毫不相襯。六月天,幾隻蒼蠅在悶熱的空氣中嗡嗡打轉,彷彿在為一個快將來到世上的小生命而獻媚飛舞。
狹小的診所內半個助護也沒有,一個女人和醫生在對峙着,嘶叫聲響徹天地,醫生乾癟的雙手緊捏着女人的膝蓋,歪黃的牙齒差點把那支「紅雙囍」的濾嘴都咬破。他壓着聲音用不純正的廣東話,不停地跟女人說:「用力!用力!快出來了,再用點力!」
就在此時,診所大門響起一陣急速的敲門聲,醫生哪有閒暇理會。但敲聲不止,而且還越來越粗暴。
醫生忍不住也粗暴地大喝:「誰呀?」說話時仍咬着「紅雙囍」,煙灰奇蹟似的沒有掉下來,他那雙盯緊着陰道口的眼睛也沒有移開過,而那堵塞在陰道內的小頭也同樣頑強地不肯出來。
門外的人大力地拍着門,粗着嗓子道:「警察!開門呀!」
醫生喃喃詛咒着:「這個狗屁地方哪有警察?肯定是那班死飛仔在搗蛋!」
醫生努了努嘴,一臉不滿。他抿着唇深深吸了一口那支「紅雙囍」,怒唬:「生仔呀,沒有空!」
門外那班自稱為「警察」的人靜默了兩秒,又大呼道:「你再不開門我們就撞門了!」
收音機在迴繞着白光的《等着你回來》,為兩道空間之中倏然而至的死寂營造出一種異樣的氛圍。酷熱的天氣加上一個死堵在陰道裏不肯出來的嬰孩,這翳熱和無力的感覺,醫生覺得,就像便秘的人蹲在廁所內兩個半小時也拉不出一舊屎,頭昏腦脹得想吐。在三十三度的氣溫下,醫生的額角淌下斗大的汗,背上的汗水濕透了醫生袍,女人仍在床上呼叫,漸漸無力的聲音正好附和着天花上那疲憊地轉動着的風扇。
「終有一刻會停下來的。」醫生心想。
難產引致的汗水浸得被褥像大雨後霉爛的海綿,滲着一陣酸餿的氣味。由於沒有一隻空閒的手去為這個在生產時仍濃妝抺豔的女人拭汗,滿臉脂粉只能像一窩滾起的豬肉湯表面上的一層浮油,一泡泡地堆在臉上等待被清理。
醫生決定不去理會門外的那班人,他心想:「這個世界已經夠亂的了!管你是『英女皇』還是『雞』,我只知道面前有一條快死的『鹹魚』!」
這時門上傳來一陣強烈的碰撞聲,突然「碰!」的一聲,整道大門被狠狠地踢破,就是這一下巨響,把女人剛踏進鬼門關的前腿抽了回來,接着四五個武裝警察,提着槍魚貫而入。醫生刹那間嚇呆了,他從沒想過在九龍城寨會見到警察,他連賈炳達道都不敢去,就是怕碰上那些叫做「警察」的奇異人類。他爛口半張,那支「紅雙囍」和它那長長的煙灰仍奇蹟地黏着醫生那泛白的唇角沒有掉下來,女人也被嚇得不知從何而來的一股力氣,從尖叫聲中把半個小頭擠出了陰道。
至於那班破門而入的武裝警察,則張着大口,看着女人大腿間一片血淋淋,竟也嚇呆了。有個膽子較大的警察把頭伸到女人袴前,瞪着眼道:「天啊!真的在生仔!」
跟着這四五個警察就像在動物園般,毫不客氣地盯着女人坦露的陰部看着嬰兒出世,當中有一個警察還緊捉着女人的手,不停地跟她說:「用力!用力!」
當二十分鐘後醫生把嬰兒從女人的陰道拉出來,一身血淋淋被狠狠地打了幾下屁股,忍不住哇哇大哭的那一刻,那幾個警察一起鼓掌歡呼,據後來將這一幕重述給我的蔡醫生說——即那個幫我媽接生的醫生,警察當中有一兩個的眼角滲出了淚水、一個在祈禱、一個抱着他大叫大笑:「出世了!出世了!」一個則抱着我媽大哭起來。那個抱着我媽哭的警察還要求替嬰兒剪臍帶,後來這幾個警察都逐一抱過了初生嬰兒後才離開診所。
而那幾個警察原本衝入診所是為了甚麼?在當時竟然沒有人記得要問,而警察也好像忘記了要說。
這個故事,就是我那與眾不同的弟弟——李向善出生的故事。
由那天開始,我就知道自己比起弟弟渺小得多,因為當時的我其實也在現場——診所內另一個打開門的房間中舔着波板糖。然而,從阿媽叫得呼天搶地到警察衝入再到細佬(弟弟)呱呱落地,都沒有人留意到還有一個小女孩在現場一角吃着波板糖。
而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手上的那塊波板糖,是怎樣從一個個彩色的圓圈,在我口中溶化成隻剩下一支小白棍。
「細佬出世了,阿爸呢?」我記得自己穿着一件灰藍色的上衣,咬着那支光禿禿的波板糖棍問蔡醫生,當時的我大約七歲。
蔡醫生嘴角仍是咬着一支「紅雙囍」,自那天起,他抽煙抽得更凶了,他總覺得就是「紅雙囍」帶給他好運。
他說:「他去了追龍。」
我小小的雙眼在發亮。阿爸好威啊!去了追天空上的龍!
(二)
我弟弟李向善出生在一九七三年,他出世那天香港政府派了幾千個警察闖進九龍城寨剿滅黑幫,偏偏就在蔡醫生替我媽接生的那一刻,幾個警察踢破門闖進蔡醫生的非法診所,見證了細佬呱呱落地的歷史性一幕。
大家都說向善是「福星」,若不是他剛巧在此時出生,躲在蔡醫生宅後的那位撈家和他手下那班妓女和馬伕就恐怕難逃一劫。在向善滿百日時,撈家替他在城寨擺了數十圍「百日宴」,膽大一點的東西區居民都來了參加,城寨一向東西兩區分隔,西區是善良人家的居住地,東區是黃毒賭的溫床。平時兩區各不相干、各自修行,我想那晚應該是九龍城寨建立起來後,東西兩區最融洽的歷史性時刻。
但在那百日宴之後,本來在東區活躍的撈家和黑社會逐一遷出了九龍城寨。報紙說是警察成功剿滅了九龍城寨的黑幫,令其元氣大傷無法繼續經營;盲公陳說是細佬的皇氣太霸道,衝開了城寨中的滿天黑氣,令黑幫自行撤退;天后廟的廟祝則說由於細佬的陰氣太重,連黑道都容不下,將來肯定是個混世大魔王。眾說紛紜,在這個世界裏簡簡單單的一件事永遠有無數個說法,明明其實都不過是幾個形容詞和一堆廢話,但說的人卻要把它們說成是真理。而且,還要迫別人去相信他們口中所說的狗屁真理。
人年紀大了,就總是活在幻想出來的真理之中了。雨果說:「即使是一個智慧的地獄,也比一個愚昧的天堂好些。」然而人的心中,自己的真理就是天堂,別人的智慧就是地獄,雨果說這句話的時候,也同樣是活在自己的天堂之中吧。
細佬是一個傳奇的人物。他出世的過程已夠傳奇的了,而他生來也有一股與眾不同的氣質,最擅長擲聖杯的三姑和六婆說他有「陰陽眼」,即是說,他能見到我們見不到的東西——鬼。向善總是着空氣中的「東西」咯咯笑和說嬰兒話,但在我看來,嬰兒期的向善其實只是很有性格,比起看着大人們對他說「un咕」時一張張扭曲的臉容,他理所當然地會比較喜歡和空氣玩。
細佬出生的過程令我感慨良多,看着城寨的種種生活、種種衝突、種種悲歡離合,雖然只有七歲,但當時的我卻已參透人生跌宕乃家常便飯,圓滿只是一種心態,而不是傷春悲秋就能達到的一種境界。
(三)
當我十八歲時,向善十一歲。那年我經歷了人生中最傷痛的日子,很記得那時候向善跟我說:「如果福氣可以儲存,我寧願將我出生的福氣分給此生身邊不同的人,緩和一下他們痛苦的日子。只可惜那時才一堆肉塊的我甚麼都感受不到。」
他這句話,令我想起《塊肉餘生記》那個在痛苦中等待命運救援的大衛。
細佬的說話中,彷彿早參透了他的人生會很順遂,別人的人生卻波折重重。
然而,他難道就只有福氣沒有感到痛苦嗎?
一九七三年我弟弟李向善出生的那天,我們的母親就失蹤了。
一九七三年的香港彷彿特別動盪。恒生指數由七二年年尾的八百多點升到七三年三月的一千七百多點,當時有人每餐魚翅撈飯、用石斑製魚蛋、燒五百蚊紙來點煙,但同年恒生指數由高峰大跌超過九成,釀成香港歷史以來最大的股災,那些魚翅撈飯的人於是就跳樓自殺。那時人人都說香港人太自負,見好不懂收,結果輸得一敗塗地。其實,人,有甚麼時候不自負了?
細佬說過:「真不明白人為甚麼總喜歡以數字上的得失來論成敗。」
回想細佬出生的一九七三年,那年世界最轟動的新聞是死了個武術奇才李小龍和天才畫家畢加索,面對這種世界級的文武雙亡,香港股災又算得了是甚麼?
(四)
城寨是個「三不管」的地方,遍地黃、賭、毒,卻又處處溫情,是個黑暗、骯髒、詭異、妖媚,卻並不冷漠的地方。
那時香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九龍和新界都已歸了英國管,但偏偏處於香港內的城寨仍名義上屬於中國滿清,然而清政府山高皇帝遠,英國人雖表示已佔領了城寨,又要留一點紳士風度,清廷不管、香港政府及英國政府又不敢多管,於是便造就了一個「三不管」的畸態。
由於「無皇管」,城寨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罪惡的溫床,色情場所、賭場、無牌行醫等等,只要一想到「嫖賭飲蕩吹」,人們就定必想到「九龍城寨」。雖然人人都說城寨亂,但其實我們住在那裏又不怎麼覺得,反而街坊街裏都熱情得很,誰家有事、誰生病了、誰的孩子沒人照顧,大家都會主動去幫忙,阿媽每次煲湯總會刻意煲多一些,讓我送些給左鄰右里、蔡醫生或東區一些攤主,又或看看樓下有誰家的小孩在玩,叫他們上來喝湯。哪像得現在,煲湯就煲那小半鍋,喝剩了就全送給渠務處。
阿爸常說蔡醫生是我家的救命恩人,若不是他,向善和我媽早已一屍兩命。
可是我總覺得,救我家和我媽的人應該是那幫警察才對,尤其是那個捉住我媽手鼓勵她的警察叔叔。
(五)
蔡醫生的診所位於東區的某大廈二樓,很多妓女都會到那裏墮胎和醫花柳。每次去他診所的時候,都要經過一條漆黑的暗巷,白天沒有陽光照射,有時要亮着電筒才走得過。小巷的牆上掛着千百條電線,牆上不停有水滴下來,牆腳邊常常有老鼠和蟑螂在爬行。這種暗巷在城寨中見怪不怪,走過暗巷之後,會見到一個大廈入口,入口的牆上釘着許多西醫和牙醫的膠牌,然後爬上一條只容得下一個人走的樓梯,就能到達蔡醫生的診所。
在細佬出生之前,阿媽煲了湯常會叫我送些去給蔡醫生,她說蔡醫生是個好人,在那些年頭,願意照顧妓女的人簡直少之又少。但蔡醫生不止給她們藥,而且有時遇上又窮又病的妓女,還不收診金。
有次我拿湯去給蔡醫生時,看見他跟一個三十來歲,把一張臉塗白得像個女鬼的阿姨說:「一個禮拜內別接生意,回去吧,診金免了。」
那時我大約五歲,我問蔡醫生:「叔叔你為甚麼不收錢啊?」
蔡醫生邊低頭不知在寫甚麼,邊道:「人家一個禮拜不能接客都沒收入了,我還好意思收她的錢?她的姘頭來找我算帳那怎辦?這叫因小失大!你們這些小孩懂甚麼?」
我當時不懂得「姘頭」是甚麼意思,總之是個不好惹的人就是了。我也不知道甚麼是「因小失大」,我只記得蔡醫生那圍了黑邊的手指拼命地在翻一本寫滿簡體字的中文書。
後來有次我拿飯去給蔡醫生,跟他說:「阿媽說你常常不收錢會沒飯吃,所以叫我拿些飯來給你。」
蔡醫生說:「這叫積陰德,積多些陰德以後才會有好日子過的。」他摸了摸我的頭,隨手取去了飯壼。
當城寨拆了之後,他的資格因為香港不承認,所以拿不到牌行醫,也沒錢開診所,政府賠給他的錢聽說也拿了去幫一個欠債的妓女,自己弄得流落街頭行乞,最後在過馬路時被車撞死了。
(六)
城寨對我來說是一個安寧太平的地方,每當我以後遇上不開心的日子,就會想起這段歲月,總教我會心微笑。以前城寨外的人看城寨亂,但對住在裏面的人來說,這卻是心靈上的一個避風港。城寨亂也許是真的,但世道何時不亂?無論多亂,孩子們小小的眼睛還是能看見快樂。
我記得小時候,梯級邊常有些白色長長圓圓的東西,上面刻着一條條黑色的長短線,我起初還天真地以為是上課用的簡尺,於是便拿些粉筆用這些圓碌碌的簡尺在地上畫線,可是它們總滾來滾去害我畫不成直線。
過了幾天後,我和玩伴大牛提着水桶到樓下取水去,那時候整個城寨只有幾條街喉,每天只供水幾個小時。我們倆比賽跑樓梯誰最快到樓下,輸了的人就是烏龜。我其實最不喜歡和大牛比賽了,因為大牛比我大一歲,又胖又高大,每次都是他跑贏,我只有輸的份兒。
不過也多得大牛,我在往後的人生路上才不怕輸。輸得最慘、跌得最痛的人往往是贏得最多的人。「賭仔輸得一身債就是因為他們總是以為自己總有天會贏。」這句話是我五歲時送湯去給賭館看場的五哥時聽來的道理。
大牛以他自己號稱的、沒經過計算的「三秒九」時間跑到樓下,「砰」一聲跳立地上,大叫:「我贏了!我贏了!小倩是烏龜!小倩是烏龜!」
大牛大呼大叫之餘還把水桶蓋在頭上,扮怪獸(他說是英雄)。我不喜歡做烏龜,於是隨手就拾起地上的「簡尺」,往他的頭盔擲去。
大牛在桶內聽到「咚」的一聲,把水桶揭開,叉腰指着我罵道:「死烏龜!你拿東西擲我?」
我向大牛扮了一個鬼臉,隨手又拾起那「簡尺」,作勢向大牛擲去。
大牛「咦」的一聲,跑過來查看我手中的東西,問:「甚麼來的?」
我說:「這是簡尺來的。」心裏其實隱隱覺得有點理虧,因為我知道這些簡尺是劃不成直線的。
大牛卻大呼道:「這不是簡尺來的!你看,這裏有針的!」
我問:「那你說是甚麼?」
大牛鬼鬼竄竄地湊近我的耳朵:「這是飛鏢來的!」
我一聽見「飛鏢」這兩個字便兩眼發亮,我只在電視上看過別人玩飛鏢,飛鏢對小孩子來說是禁止的玩意,就如亞當夏娃看見禁果一樣,越被禁止的東西就總是越有吸引力。
於是我和大牛就低聲相約,取完水後便叫街童們一起去玩「擲飛鏢」,我們在大牛家中取來一張圖畫紙,在紙上用蠟筆劃上一個個歪歪斜斜的圓圈作標靶,然後取些牛皮膠紙把製成品貼在昏暗的樓梯口,然後就拿着拾回來的飛鏢,飛擲到那充滿童真的標靶上。
剛巧蔡醫生從樓下走上來,看見了就喝道:「喂!你們在幹甚麼?」
我和他最熟,於是便笑嘻嘻地說:「我們在玩飛鏢。」
平時平易近人的蔡醫生卻突然發怒:「飛鏢?你們知不知道那些是甚麼?」
他指着那些「飛鏢」,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我們都被嚇怕了,誰也不敢出聲。
蔡醫生向我們說:「你們知不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那個『龍紋大哥』的?」
「龍紋大哥」是城寨中最惡的撈家,城寨中無人不識,大家大聽到這些「飛鏢」都是「龍紋大哥」的東西,均嚇飛了魂魄。
蔡醫生一字一字頓出來,說:「這些東西是『龍紋大哥』給他手下做的記號,他如果知道這些記號被人移動過,一定會揪出這些人,把他們放到油鑊裏炸成油炸鬼,你們知不知道街上賣的油炸鬼都是這樣來的?」
那個時代的小孩很單純,大人說甚麼都當真,蔡醫生的話比任何大人說的道理都還要靈。以後就當然再沒有小孩玩飛鏢,而且在往後好幾年的小孩圈中,也就多了個油炸鬼的傳說。一直到了中學,我才知道那些「飛鏢」是道友用完丟棄的針筒,原來我們天天都在鬼門關門口走過也不自知,幸好有蔡醫生用油炸鬼來嚇我們,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除了「擲飛鏢」外,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一個遊戲就是「追飛機」。九龍城寨和啟德機場很近,每次有飛機經過,都能聽到「隆隆」巨響。當年乘飛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住在城寨中的全不是難民就是貧民,小孩們都對飛機仰慕得不得了,彷彿一隻飛機就如一個個偉大的夢想。
我小時候常常獨個兒跑到天台去看飛機,當飛機在頭頂上的高空飛過時,我就夢想自己能跳起來捉住飛機的一角,然後隨着它飛到一個千里之外不知名的國度。可是無論我跳得多高,飛機卻總是和我差了一大截的距離,每次我總是失望地望着它由一隻隻大鳥漸漸縮成一個黑點,直至消失在天邊,手心中只留下一個又一個失落的夢。
偶然回想,人生不也是由一個個失落的夢所組成的嗎?但夢失落了一個,至少在那些年頭,還有另一個和再另一個。
城寨的人口極度稠密,大廈又是隨意就建起來的,密密麻麻,天台和天台之間一步就可以跨過。
「追飛機」的遊戲是這樣的:我們先蹲在地上,做一個助跑的姿勢,一聽到飛機的隆隆響聲,便大叫:「跑呀!」然後幾個小孩從一棟大廈的天台跑到另一楝大廈的天台,跨過天台上滿佈的電線,用盡全力去跑。這是一個高難度的障礙賽,往往跑不了兩個天台,飛機已飛遠了,但我們還是繼續跑、繼續跨過一堆堆縱橫交錯的電線、繼續呼叫、繼續大笑,彷彿這樣美好的歲月就能一直跑下去,跑下去……
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