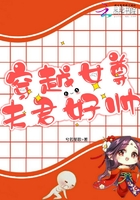段梦忽而想到方才德贵说广津候从江南给她带补品的事,这广津候进宫岂不是会与楚辞见面。
便问道:“广津候是何时进的宫?”
“一大早便进了,与官家淡了一天的公事,这会谈完后,才记起给娘娘带来的补品,那可是上好的补品啊,娘娘您可有口福了,德贵我也积娘娘的德,有口福了。”
段梦对于德贵的厚脸皮有些无奈,用食指戳着他的额头,道:“滚犊子,补胎药你也馋!”
德贵只嘿嘿一笑,便想到了方才见着楚辞母子三人,又想到方才段梦问他广津候河时进宫,想到了事情往后的发展,便说道:“方才好家见着了楚小姐,不,应是聂夫人……”
“本官方才也正想跟你说这事,若是他们二人见面,不知会擦出何火花来。”
德贵似想到了什么,说道:”娘娘您也不必燥心,方才奴家瞧见聂知州与她侍妾进宫来了,许是来接的聂夫人。”
段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但又想到了什么,又说道:“聂士诚的哪位侍妾?”
“是苏家那位。”
段梦走到门口停了下来,又反问道:“是苏盈,苏与绯?”
“正是。”
段梦素来就发觉聂家的那位苏姨娘,苏与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她也能时常瞧见苏与绯进宫来,与韶朝宫的封婕妤走的较近。
封婕妤是广津侯胞妹,自小在江南地带长大,就这年间刚来的建安城,久往在皇宫中是如何与长住在建安城中的苏与绯相识,还来往得如此密切。
这封婕妤生于江南,为人热切,与各宫中的妃嫔关系是极好的,与段梦的关系十分融洽,她这几个月以来,常吃封婕妤从江南托人带来的补品。
因着苏与绯与封婕妤来往密切的关系,段梦不免有些疑惑,便叫德贵将方才送来的补品与封建抒送给她的补品做个对比。
她想,既然是从江南带来的,想必也是同种补品。
这一对比,两种补品大致都一样,只是封婕妤送的补品多出了几样东西,分别是龙眼,枸杞、麝香等物。
段梦没看出什么,但一旁的德贵面色苍白,神色慌张,向段梦问道:“娘娘服这补品多久了?这龙眼与枸杞是大补之物,补品中有薄荷等物是性寒之物,怀孕之人不能食用,这虽副作用没多大,常人可以吃,可娘娘您肚中怀有龙种,可不是常人啊,更要命的是,麝香可是个催生的东西,这玩意虽好,可是您要忌食的啊。”
段梦心中一顿,也才后知后觉,怪不得近日胎动得历害,心中突然慌了起来,又引起了胎动,她轻叫一声,“哎哟!”
德贵突然慌了起来,想要叫人之时,段梦叫住了他:“你先去看看阿辞,这苏与绯与聂士诚进宫准没何好事,记住,定要回来禀报本宫。”
德贵也急了,这凤体有恙,他不能不管,但是皇后娘娘的旨意又不得违抗,他是进退两难。
段梦缓了一会儿后便好多了,她明白德贵的难处,便说道:“本宫暂且无事,若阿辞有事,本宫也便有事,你还不快去,若是迟了后果不堪设想。”
德贵虽忧段梦,但楚辞一直待他不错,这告了辞便去找楚辞。
这快要用晚膳之时,聂川已是在家中等候楚辞多时,他一早就明白楚辞进宫与段梦叙旧去,一余定会很久。但他因思妻思子心切,这一日不见,仿苦隔世,这时在书房中看文书已是看不下。
便在那时,官中来了一道口喻,说官家与皇后二人正与楚辞叙旧,也传他去宫中谈话,聊家常。但奇怪的是,竟要苏与绯前往,聂川也顾不得疑惑,既然是官家的旨意,遵守了便是。
聂川曾多次进宫,但这后宫却未曾踏过一回。一踏进后宫,多的是莺莺燕燕,路程弯弯绕绕,他也不得去记路,被前面的宫娥绕昏了头,才走到一座亭中,宫娥便叫他在那歇息片刻,过会官家与皇后要来。
聂川便开始起了疑,这可不是官家与皇后的待客之道,正想对一旁的苏与绯说出心中的疑惑之时,苏与绯倒了一杯茶,送到了聂川面前,道:“这绕了这么多路,想必郎君也渴了,喝杯茶,解解渴,散去些热气。”
聂川确实有些口干,苏与绯将茶水递过来之时,便饮完了。但却未有解口干之效,下着小雨的候本应是冷的,而他却倍感燥热,脑袋昏昏沉沉,两眼昏花,视线模糊,看不清物什。他意识到了不对劲,想要站起来时,却全身乏力,使不上劲,没一会便失去了意识,倒了下来。
他在倒下来前隐约能听到苏与绯与宫中某个妃嫔的对话,只是分不清到底是哪个人。
“车马本宫已备好,接下来便看你的了。”
说话的是一位穿着华丽的女子,头戴昂贵的珠宝首饰,雍容娇美,皮肤保养得极好,一看便是养尊处优的妃嫔。
楚辞离了凤梧宫后,便要出宫回府,回去的通道经过御花园,便遇到一位故人。
楚辞将抱着的聂永钰放下来,交给跟随的侍儿,让他们带着聂子琴与聂永钰到一旁玩去。
她呆呆地看着那位故人,双目未离半分,那人也与她一般。
这四日相对,是久别重逢的相遇,只可惜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样。
宁敏牵着自家儿子走了过来,对着封延说道:“附马,该启程回去了。”
这一声话语落入二人耳中,二人才回了神。
楚辞轻轻一笑,福下身子,向他们二人——行礼道:“附马爷,南阳公主。”她温柔贤良,委婉大方,藏下了所有。
封延双眸还未离开楚辞身上,即使他的夫人宁敏还在一旁,三年后的第一句话便是:“阿辞……”
终是习惯这样唤她,三年后的重逢,满眼皆是她,问候语太多,却一句都讲不出,只剩阿辞的前言。
三年未见,人已沧桑,她嫁作人妇,相夫教子,他另娶他人,举案齐眉。
楚辞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她很配服自己,再相遇还能一笑而过。
一旁的宁敏已在冷眼观看许久,她恨丈夫的不忠心,也恨楚辞出现在丈夫的面前,她虽觉得委屈,却莫名有些开心。她走到了楚辞面前,深吸了一口气,对着楚辞说道:“三年未见,楚璃月你倒是变了不少,老了。”
楚辞没有太多的神情,也没有太多情绪,都是笑面相对,一道:“自然是,公主你也一样。”
“你!”宁敏哑口无言,却不禁在心中感叹。
时隔三年,楚辞应是他们当年那堆年轻子弟中变化最大的一人,要知道,当年的楚辞,意气风发,潇潇洒洒,不受拘束,胆量极大,最痛恨的便是规矩礼仪,哪像今日这般规规矩矩,每每见到宁敏都相互炸起来,脾气大得很,性子又倔。
宁敏很想知道到底是何事,将楚辞变成了一个如此安静,规矩的人,但一转头看了封延一眼,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这一辈子,封延把最多的温柔都给了楚辞,若不然邂逅之时,眼中只有楚辞,眸中只剩温柔。
这一辈子,楚辞的潇洒只有封延明白,剩下最后的潇洒都是封延温柔的包容。
宁敏见封延的目光都在楚辞身上也无他法,瞧见了一旁的聂子琴与聂永钰,心想要移开封延的视线,便对着楚辞说道:“这三年间,原来你已出阁,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那小的性子,随你。”
她这话一出,封延也忍不住将视线往一旁的两个孩子身上移,双眸中的温柔夹杂着另一种情,有悔意,但当初也无他法,天命难违。
聂子琴也将目光往大人们身上引,看到封延时,便停住了移动的目光,直盯盯地看着他,当封延把目光放到她身上时,她忽地甜甜一笑。封延也觉得聂子琴有趣,一眼便欢喜她。
“公主不也是成了个母亲,只是这孩子像貌并不随公主,而是……”楚辞转头看着封延,一道,“而是更像附马,温顺,想来往后定是个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如你一般……”
“阿辞……”他不知再该作何言语。
正在这时,封呤璞挣开了宁敏的手,跑到聂子琴面前停住,毫不忌性地问道:“你是何人,长的真好看。”
稚嫩的童音是真好听,聂子琴被这无礼的封吟璞吓了一跳,只骂道:“登徒子!”
看着这两孩子的玩闹,像极了当年的楚辞与封延,当年封延对楚辞说的第一句话便是“登徒子。”
封延温润一笑,对着楚辞说道:“这两孩子像极了当初我们刚见面的模样。”
楚辞也一笑,道:“原来你都还记得。”
“自然,我看这两孩子挺登对的,不如给他们定下亲事,以防如我们一般......”
楚辞正想开口应下,宁敏插了一嘴:“定亲?封延,你可有想过门第之事?这事如何定下……”
“朕觉得广津候的提议很好。”宁演不知从何处出来。
众人见到后便一一行礼。
宁演又对着宁敏说道:“南阳,这事若看门第,岂不耽误了,你看朕与皇后,可有门第之分,若是如此,怎会有皇后与联的今日?”
“皇兄……”
宁演一罢手,制上了宁敏要说的话。
“朕为你们二人做主,这亲便结下了。”
话语一落后,宁演便走到楚辞面前,说道:“许久未见,联可记得你可是第一个敢骂联的人,想想当初你可真英勇。”
“臣妇不敢。”
“楚璃月,你变了。”
楚辞并未再作答,她也不知如何作答,她变了确实不假,可人都是会变的。
也正在这时,德贵便走了过来,一一行礼道:“奴家参见皇上,广津候,广津记,聂夫人。”“聂夫人”这三字如同砸入封延的耳中,他难以置难地睁大了双眼,一副惊讶地看着楚辞。
他惊讶她竟嫁给了最不可能之人,难怪成了今日这般模样。
聂家是书香门第之家,虽说里边城府不深,但规矩极严,楚辞此生最痛恨的便是规矩礼仪,她不喜规束。
封延正要开口问楚辞,刚张开口要问,德贵便道;“方才娘娘担心聂夫人与广津候见面之事,便叫奴家看瞧瞧。”
“他二人见面能有何事,是皇后多虑了。”
“可……”德贵再想多言语几句,可宁演便摆手让他停住。
“广津候,不是要去看看封婕妤吗,朕也陪你去瞧瞧。”
说完便甩袖而去,他明白宁敏的刁蛮,放着楚辞与封延在这定会闹出事来。
宁演都如此说了,封延也不好再作停留,深深地看了楚辞一眼便离去了。
这一眼,兴许是最后的别离,他眸中隐隐透出不舍。
这一眼,楚辞面色很平静,没有太多的情绪。
封吟璞被母亲拉走后,还依依不舍聂子琴,他第一次看到生得如此好看的女孩儿。
德贵跟着宁演去了韶朝宫,因一旁的封延在旁侧,他没得寻机会说与宁演方才在凤栖宫之事,这事关乎甚广,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还得慎言。
看着他们离去之后,楚辞感觉一旁突然安静,空荡荡的,却也没太多想法,抱起了聂永钰,带着聂子琴回府去。
临走前的聂子琴转头看了宁演他们离去的方向一眼。
德贵已离风栖宫很长一段时间,久久未回来禀报,段梦已是急得燥了,她这一急,心中恐慌,烦躁郁闷,不禁肚子疼了起来。
一旁的贴身侍女青萍瞧见后便来挽扶,安慰道:“娘娘您也不必太担心,他们不会有事的。”
段梦忍着痛楚,皱着眉说道:“你不懂,苏与绯与封晚凝来往密切,定是在筹谋什么,偏这时巧不巧广津候进宫,阿辞也进宫,更巧的是聂士诚与苏与绯进宫,出现在后宫中,臣子没有召令是不得踏入后宫半步,无人召他,他.........如何能出现在后宫中?且不说官家正与广津候谈事,我也未召他……”
“皇后姐姐说的对。”
封晚凝走进屋中来,面带笑容,向着段梦行礼,行完礼后,又开口说道:“妾身十分羡慕官家对皇后姐姐的宠爱,这不,从妾身家乡中带了些补品给皇后姐姐,沾些是后姐姐的光,想让官家多看妾身几眼。”
段梦一瞧见封晚凝,顿时心中来了气,她千防万防终是没防封晚凝,失算了一步。
封晚凝一步一步走近段梦,一字一句地对段梦解释道:“皇后姐姐是真聪明,只是失算了一步,妾身目标不是楚璃月,而是皇后姐姐。”而后又说道,“此时德贵公公与官家应是带着妾身哥哥前往韶朝宫,救不了皇后姐姐你了。”
段梦不明她话中何意,问道:“你是何意思。”
封晚凝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妾身没别的意思,皇后姐姐只需如晓,今后官家宠爱的便是妾身便成,皇后姐姐与肚中的孩子将不复存在。”
段梦才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性,还未再理清前后因果,肚子便剧烈地疼痛起来,似要了她的命般。她被一旁的青萍扶着,青萍将她找到了床塌上,只是屋中只有她们三人,其他人都在外边候着。
不知封晚凝使了何法子,里边段梦那么大动静也未见有一人进来,青萍叫了大半天也没动静。“娘娘您坚持住!外边都是死人吗?!”
封晚凝冷眼看着她们主仆二人,在一旁冷言冷语道:“段骛颜,你要明白,你只是一个怜女出身,光靠着皮囊与才艺是无用的,虽说你有些小聪明,终究斗不过整座后宫的人。”
聂川昏过去之后,苏与绯便把他带到封晚凝备的车马,那是封延的车马,封晚疑曾写信告与封延,她要回江南省亲,所以今日宁演才说要跟封延一同去看封晚凝。
这聂川与苏与绯一同坐广津候的车马出宫便无人怀疑,封晚凝只需再留封延在宫中一晚即可。
苏与绯将聂川带出宫后,并不是回的聂府,而是带他去的废弃小院,院中有几人把守,守着一位貌美的女子,她的穿着与妆扮,是个已出阁的女子,已嫁为人妇,她的眉目有几分像苏与绯。
苏与绯走了进来,看到了被捆绑在床榻上的苏木娇,苏木娇瞪大了双眸,她竟不知是她所谓的姐姐将她绑到这。
“妹妹,姐姐也并不想如此,只是你防碍了姐姐的路,你与你夫君谢知书次次防碍姐姐的事,这也无他法,只好将你绑来,帮姐姐个忙。”
苏木娇性子柔弱温顺,自始自终都将苏与绯视为己出,这时直到了她的真面目,是真难以置信。此时她已慌了神,眼泪和汗水混合成一体,口中被塞了布,说不出半个字,身子又动弹不了,她已是绝望极了,似乎已猜到下一步苏与绯想作何。
她越是慌张,苏与绯越是感到满意,又说道:“你只需让他满意了便可,我要的并不多,只是一个把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