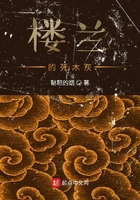酒红色的淡墨泼上天幕,被夜神用手指涂抹,晕染。
女孩右手反叉着腰,左手抓着门把手,气喘吁吁地用力拉开电话亭的沉重玻璃门,“抱歉酉星,我迟到了。”
林子夕这回学聪明了,知道Holasgow是冬天,穿得很暖和。只是跑起来有些不方便。
少年伸长脖子透过红色电话亭的玻璃窗望向广场中央掩映在紫罗兰色里的夜神雕像,皱了皱眉,“确实。”
“睡前跟外婆聊了聊,耽搁了。”
“今天新上任的时间判官似乎心情不佳。现在才下午三点。”少年眯着眼凝视门外渐渐晦暗的天,伸出插在黑色夹克口袋里的手,率先推开门,面色凝重,“看来……今晚……你得留在这里了……”
“我们去哪儿?”
“斯拉塞亚商店。”
“干嘛?”
“让你看起来不像个人。”
林子夕重重地拍了一下酉星的后背,“好好说话。”
酉星在面前的夜神拉维斯雕像前蹲下,掏出嵌在底座裂缝里的上的两张纸,递给林子夕。
“什么啊?”林子夕接过那张透明的,字迹闪着绿色光泽的光滑纸片。
“车票。”
跟着酉星上了车,司机一直盯着林子夕看,像在观赏什么动物。
林子夕打了个寒噤,缩缩脖子,扯着少年的袖子,“喂,他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你好看呗。”酉星扯了扯嘴角。
夜里虽然看不清表情,林子夕也能脑补出他那欠揍的讽刺神情。女孩白了他一眼,打算挑个窗边的位置坐下。
“坐最后。”少年轻轻拍了拍女孩的头,语气却是不容置喙的坚决。
“哦……坐最后就最后嘛,干嘛这么凶。”
“去最里面。”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林子夕还是乖乖坐了下来,因为陆陆续续上来的乘客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当猴看。
全然不同于华城的公交车,车厢里坐满了乘客还是一片死寂。听广播林子夕才知道,这是今天的末班车,Holasgow的人们都赶着回家。
夜里的Holasgow,街上人很少。昏黄的路灯透过落满雨点的玻璃在林子夕眼里闪烁,大巴摇摇晃晃的,昏昏欲睡的林子夕总是撞到窗子。她索性坐正了,贴紧座椅,不再头靠窗,偷偷用余光窥视着坐在身边的少年。
林子夕才不乐意承认,除了上课,这是她第一次同龄异性坐在一起。
灯光在少年脸上,还有白色的耳机线上斑驳,他的双手交叠置于膝上。脱下黑色夹克,高领白色羊毛衫穿在他身上很好看。他的鼻梁很高,乍一看有点像北欧人,白得并不女相,倒是英气。
“缄默是风度翩翩少年郎,开口便……唉……白瞎一张好脸……”林子夕万分惋惜地摇摇头,忿忿地嘀咕着。
“碰!”
刺耳的刹车声划拉着耳膜,林子夕不受控制地向前倾。
“完蛋了……”女孩紧闭双眼。
意料之内的疼痛并未如期而至,取而代之的,是额上温暖的触感。
她迟缓地睁眼,落回座位,少年的左手还在自己额上。
大抵是车上空调温度太高了,林子夕觉得自己双颊涌流的血液快烧开了。
少年皱了皱眉,解开自己的安全带,凑近林子夕,整个人几乎罩住她。
林子夕僵了一下,挺直了背一动不动。
“咔。”
安全带锁扣碰撞的声音。
“谢谢……”林子夕鼓起腮帮子,懊恼地抬起冰凉的双手敷上脸颊,“我刚刚都在想什么啊……”
“都别动!”
有人踹开了车门,对方说的,是林子夕完全没接触过的语言。
可奇怪的是,她不仅能听懂,而且对此有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
就像是对于父亲的家乡话,肆城话,她能听懂,就是不会说。
他们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大臂上的新月标志在黑暗里熠熠。
为首的高瘦恐怖分子举起枪瞄准了自己面前的乘客。
酉星立刻将林子夕的头按在自己肩上,用外套盖住她的头,隔着衣服贴着她的耳朵,用只有两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道:“别动,把手缩进袖子里,别出声也别把头探出来。”
“是塔库沙!”车上有人尖叫起来。
她咬住自己的袖口,尽量克制住自己因恐惧而生发的颤抖。少年大概是感受到了她的恐惧,安抚地隔着外套摸了摸她的头。
“给老子闭嘴!想活命就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每个人必须交够两千五,要是谁敢报警……”那个走在最前面的高个子动了动扳机,“我就立马送他去见主!”
为首的塔库沙看起来像是这队人马的头子。
他扫视过每一个人的脸,样子不像是在找什么值钱物什,倒像是……
鹰隼在觅食,有既定目标地搜寻。
脚步声愈来愈清晰。
林子夕连大气都不敢喘。
酉星将自己的钱包尽数奉上。
高个子塔库沙打开钱包,眼神攥着少年的眼睛“怎么才两千?”
“对……对对……怎怎么……才才……两千……头头……头儿……我看看……他他……他就就……就是……想赖账……”后面有个矮小的塔库沙附和道。
高个子塔库沙拿枪顶着林子夕的头,“她呢?”
林子夕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心脏快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那个,大哥,我女朋友前些天遇到了塞伦,现在石视呢……我们正要去威尔图灵医院。她现在意识都不是很清醒,这钱包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我们大学生也没什么钱,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少年赔着笑,眼底却没有丝毫温度。
女朋友……
林子夕偷偷地瞟着身边的少年,可她的视线被衣服遮着,任凭她望穿,映入眼帘的是黑色依旧。虽然知道酉星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她的心跳依然因为这一完全陌生的词汇不可抗地乱了节奏。
“没没没……没钱可可可……可可以微信支付……”那个结巴的塔库又在半路杀出来。
林子夕真想上前给那个结巴的塔库沙一脚,怎么事儿那么多?
少年左手环抱住女孩的肩,右臂遮住腰间的左轮手枪,与那高个子塔库沙对视,“大哥,您看这年头,谁有钱还坐公交去看病呢,是吧?”
高个子塔库沙睨了眼酉星的平价Adidas,得出他确乎是无油可榨的结论后冷哼一声,招呼其余的塔库沙打道回府,“我们走!”
半晌,车中仍惟余静谧静谧,如同塔库沙刚刚血洗了现场。
“酉星,我现在能出来了吗?”林子夕满额冷汗,意欲起身。
他没有回答,只是伸手把她的脑袋按到自己的肩上,又盖上衣服。外套被拨弄出一个可呼吸的小口。他将两只耳机轻轻塞进她的耳朵,又笨拙地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肩膀,“你困了就睡会儿。乖,到了叫你。”
冥界的街灯,跟人间的不一样。银色的光从外套的小口里洒进来,可能是因为塔库沙带来的余悸,林子夕突然觉得,觉得街灯的光也温柔地要命。
耳边还回荡着他刚刚的话语,他的声音像在封闭的大理石厅无数次碰撞又坠落,坠落又碰撞,莫名其妙的,林子夕突然就想起那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小时候跟姑姑出门乘车的时候,姑姑就是这么哄着他睡的,应该有安抚效果吧,少年默默祈祷着。
车身晃悠悠的,林子夕闭上了眼。
“女士们先生们,终点站柏拉棵粒广场到了……”
“林子夕,醒醒。我们到了。”
酉星搂着摇摇欲坠的“女朋友”在司机的“注目礼”下下了车。
Holasgow的冬夜,像俄国干硬结块的贫民的头发。
林子夕终于被风割清醒了。毫不夸张地说,她觉得夜风能把自己的鼻子冻掉。
是车发动引擎离开的声音,林子夕忙撤下外套要给酉星披上,无果。
他太高了,我跟他差了……林子夕目测着,“一点五个头。”她赶忙捂住自己的嘴,“该死的,我怎么说出来了。”
酉星将外套披回林子夕头上。
“会冷……”林子夕掀起外套盯着他,皱皱鼻子。
“披着,到了再拿下来,”酉星往前迈了几步,又转身走回林子夕身旁,左手搭在她左肩上握成拳,补了一句,“我不冷。”
“哦……”林子夕用外套盖住头,她觉得自己都快绕晕了。
这人不会要把自己卖了吧?
正是思绪纷飞的时候,身边的人突然停了。
“到了。”
“呼——”林子夕将外套扯了下来,跳起来披在少年身上。
眼前是一堵灰色石墙,在街灯下依稀可以判断,年代已久远。
“哟,温醒衔,你行啊你。”
另一个陌生的年轻声音在身后响起。
温醒衔?林子夕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很好听的名字。
听见她叫自己,酉星边将胳膊套进袖子里边望向林子夕。
“哪里来的女朋友,不介绍一下?”一个蓄着络腮胡的年轻男子打量着她,嘴角是无遮拦的戏谑。
林子夕下意识地抬头望向酉星——她在期待什么呢,刚刚那出戏,不过是因为塔库沙而已。
不得不承认,她该死的想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少年与女孩眸光交汇,挪了挪步子挡住了那道探究的视线。
“塔库沙给的。”不咸不淡的语气,像在咖啡馆里说出“五点六”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