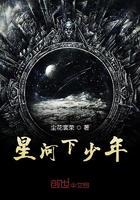电视台记者长毛是在那个冬日的下午看到那个唱着生活的男孩的。男孩坐在特制的轮椅上,一只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脚搭拉在地上。男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制服,头上是一顶同样深蓝色的阔檐帽。男孩的另一条腿和音箱被一块蓝色的布幔遮挡住了,音箱上面就是男孩讨生活的电子琴。猛一看男孩头戴的麦克风和男孩脸上从容、自信的表情,你看到的仿佛不是在大街上唱着讨生活的人,而是有一定台风的歌唱家哩。
长毛就是被男孩脸上自信的表情、灿烂的笑容震惊了。震惊了的长毛就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抓拍了好几张男孩醉心歌唱的特写。最让长毛感动的是,男孩自己根本动不了,轮椅是要人推着才能动的,而那个在男孩身后推着轮椅的人应该是男孩的母亲吧,朴素的家做袄上套一件很俗气的大花罩衣,领口处的扣子也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内衣。蓬乱的头发下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母亲的脸上永远是一副麻木的表情。也许是生活的重负太沉重了,母亲的心已经宠辱不惊了。但,只有母亲的爱才是孩子永远的支柱啊。
男孩的脸上没有乞求,也没有惯常讨生活人的可怜相,他就是用心在唱,用全部的感情在唱。街道两边门市部的人快步走到男孩面前,在他的电子琴上放上五元、两元。男孩说,谢谢、谢谢老板!祝您生意兴隆!路上的行人也住了足,脸上都是欣赏的表情。一个小姑娘,一个老太太从身上掏出一块、两块钱给男孩送去,男孩点头,说谢谢小妹妹、谢谢老大娘!男孩在说谢谢好心人的同时,脸上是虔诚的,是真心的。男孩的脸上始终是灿烂的笑容。
男孩在唱。男孩的音质好极了,男孩的台风也好极了。你根本注意不了他的下半身,他吸引你的是他从容、潇洒的上半身。男孩身上的自强不息、自信从容让你根本感觉不到他是一个高度残疾的人。有人从二层楼上的窗户给男孩仍下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沉沉的。男孩的母亲拣起来,里面是一张和小木块捆在一起的十元钱。男孩抬头看到的是同样一张善良的脸。男孩对这张脸说谢谢!谢谢!
长毛始终走在男孩的前面,他要抓拍几张最好的照片,拍一段最好的DV在电视台做节目。长毛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长毛这才发现他已经站在眼镜的门市部门前了。眼镜是长毛的高中同学。眼镜说,做节目啊?长毛说,职业习惯嘛。眼镜就说,给我和那个唱歌的小伙子来个特写好不好?我给他五十元。长毛就说,那敢情好啊!就退一步做好了拍照的准备。
这时候,男孩的母亲不知道干啥去了,男孩动不了,只能在眼镜面前的马路对面自顾自的纵情歌唱。眼镜就冲男孩招手,冲男孩喊,嗨,过来!嗨,过来!
男孩看了一眼眼镜,仍然在唱他的歌。马路边摆摊的小伙子给男孩送去五元钱,男孩仍然说谢谢、谢谢老板!祝您生意兴隆!
眼镜就对长毛说,小伙子的母亲怎么还不来,她不来,小伙子想来也动不了啊。
大概十多分钟吧,男孩的母亲终于来了。她推起男孩的轮椅掉转了头。眼镜就喊,嗨,过来!嗨,过来!眼镜在喊第二句时,就把手伸进腰间的钱包里,抽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晃了晃。
周围人的目光一下子都冲眼镜射过来。
奇怪的是,男孩的车子在他母亲的推动下,从眼镜的眼皮底下很从容的向前走了。母子俩看都没有看一眼眼镜,男孩很专著的唱着他的歌,母亲的脸上很平静,像风吹过的湖面很平静。
眼镜张大的口和扬在空中捏钱的手定格了。长毛握相机的手也定格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在一阵子的定默之后,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
河滨南路,绿柳树下,那个轮椅上的男孩在母亲的推动下,如醉如痴地唱着,他的歌在冬日的阳光里更显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