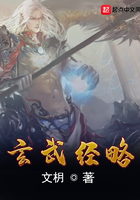不出教室门,放学走后门。
我被李东九烦得避之不及,别说请吃饭,看到他,我拔腿得逃。
他被学校公务缠身,脱不开身找我,常常匆匆打了个照面,请我放学一定等他,我没应他,理所当然随他空等。
我不想听见他问我有关于青子的任何事。
过一阵子,学校风气变好,一切渐渐平静,李东九终于空出时间找上了我。他放学在路上左右拦我,我虽低着头看路,其实已认出了那双洗得发白的鞋子。
他狠狠拍了一下我额头,没好气道:“我做了他们眼里的东厂厂公,你就不待见我了?一溜烟跑得比鲶鱼还快。”
“我最近学习,哪里是不待见你,等到初二成绩两极分化,就知道哭了,你下学期也初三了,忙着东厂的事,也别怠慢了学习。”我装疯卖傻得心应手。
他也装模作样,“你知道学习那就好,最近东厂外面得罪的人多,有些造反的刁民在路远的地方欺负本校学生,路上不算安全,我送你回家。”
我尽量扯话,不给他其余话语权。
“心情不好,有股气涨着。”
他关心道:“什么事啊?气什么都别气坏了自己,身体重要。”
“我跟我同学吵架了。”
“吵什么?厂公的妹子也敢得罪?不怕我捉拿他?”
我慢慢地讲:“你都快失民心了,还这么自信,我同学将鲁迅先生骂得很惨,我气不过,和他争辩,越说越气,他连先生的文都没有看完,没有仔细体会,就将先生说得体无完肤,你说,为什么呀?”
“他当年骂的那种人已经借尸还魂了。”
我一个放松笑起来,他趁此氛围随口提道:“徐知青也喜欢鲁迅吗?”
我要他知难而退,“她?她花心着叻,更看得起外国文豪,什么拜伦啊,莎士比亚啊,高尔基,雨果,列夫托尔斯泰都喜欢,将他们的名句倒背如流。”
却忘了李东九也喜欢看书,他为青子说话,“这不叫花心,叫开拓眼界,我也喜欢这些文豪。”
我漫不经心一提,“噢,我姐夫也喜欢看书,常常寄书给青子,家里那么多,有一半都是姐夫送的,我也才知道。”
李东九却不信,他兀自笑了,“你那张嘴,放羊的嘴。”
我继续为他介绍,“我姐夫叫谢良旌,人家上了九八五大学,家里条件又好,青子抓得可紧,一天到晚跑楼下去给人打电话,生怕自己地位被良旌大学里的那些女生比过去了。”
李东九见我说得详细,自欺欺人拍着我头顶说:“编得有鼻子有眼的,你真应该有木偶那样的鼻子,一说谎鼻子就变得长长的。”
我的巧舌如簧在掩耳盗铃者身上确实没用,他依然会问我关于青子的事,我一次次绕过去,他干脆不问我了,愚蠢的找上八喜进行探听。
八喜与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能回答他任何好话和真话,算是见了鬼。
最后,也不知他是不是鬼迷心窍,写了一封老掉牙的情书交给我,诚恳请我转交给青子。我将情书退还给他,很郑重地告诉他,喜欢谁都行,就是不能喜欢青子。
他不明白。
我也回答不上为什么。不过我说了一个像样的理由,彻底打断他想要给青子递情书一事。青子这人一旦知道你喜欢她,你们连朋友也做不成。
实际上,这话连我都不能辨别真假。
他不敢轻举妄动了,在青子那处安安静静单相思,在我这处问得事无巨细,直到这一学期结束,迎来寒假,我终于能彻彻底底避开单相思的九哥了。
我更抱着希望想,过了一个寒假,他这阉人会忘掉青子,重新拾起厂公的霸气,别再为儿女情长多愁善感,凄凄艾艾。
自上一回游戏厅与大堂哥碰见,我便隐隐知铁定要倒点儿霉。
过年,乡下里兄弟姊妹好不容易一聚,等大人们走开了,二哥将我拉到门槛上坐下似要叙叙旧,而我早已忘了半年前的谎话连篇。他摸着剃得近乎成光头的帅气逼人的寸头,嘴边挂起标准微笑,张嘴便问:“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去世了?”
“我怎么不知道我被刀捅死了?”
我一时大脑空白,连忙搜索久远记忆,恍然想起为了结识李东九撒谎那事,我干笑着打马虎,“谁说的啊,我怎么不知道。”
他又摸了摸反光的寸头,“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啊,我和爷爷在你作文里死了几次了?现在升华到逢人就说我死了,西西,你未来殡仪馆工作人员啊?你要不跟爷爷学一下跳大神,给我跳场萨满舞祭祀一下?”
小时候爷爷最常跳大神逗我笑,这是堂哥们都没有的殊荣。
大堂哥与我关系一向不和,他百分之百添油加醋说了。我舌灿莲花的解释,小堂哥也不信,最后没折儿了我才反行其道而为之,“这不是跟你关系好吗?大堂哥想去世我还不让他去世呢,我要让他在这世上痛苦的活着,永永远远,不死不灭。”
他往地上啐了一口,说反话,“别,谁跟你关系好谁倒霉,成为你嘴里去世的人,真是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
我讪讪,二哥也不是真气我,他自小嫉妒当家的宠我,虽不像大堂哥那么酸我,对我也是爱搭不理的。
我才对二哥抱有歉意,他接下来和大堂哥干得混账事,叫我不是滋味儿。
我从一间屋外路过,从风吹起的门帘缝隙里瞥见了不该看的事。
二哥干巴巴站在一旁,大堂哥蛮力将青子按到了床上去,他把比猪头还大的麻子脸凑过去,猥琐道:“今年长那么高,我们检查检查你是不是姑娘。”
他的厚嘴撅起想亲青子。
青子反抗不过来,那张气得通红的脸左右极力地偏,她挣脱之后也没去攻击他们,急慌慌地跑出来,必然在门口撞见了我。
她抬眼看了看人,两只眼睛红红的,含着点点晶莹,有些充血。
我目视前方说,不要脸。
青子的眼泪忽一下落下来了,她马上离开我的视线,跑得像是有恶徒在身后猛撵她一样,还险些被自己另只脚绊倒了,她踉踉跄跄扶一把墙,跑得更快,更远了。
我土匪头子似的一脚踹开老木门,不阴不阳直直地盯住两位堂哥。
二哥撇清说,不关他的事。
大堂哥鼻孔朝天地瞥了瞥我,他吹着口哨撞我肩膀一下,掀开门帘便若无其事跨门而出。
我捡了几块石头放在身后,不急不缓跟上去,平静地问:“你刚刚做什么了?”
大堂哥脚步顿住须臾,他懒得回头,将手插在裤兜里继续大步朝前,斜了头吊儿郎当说:“没有你的事,大人的事,你小屁孩管不着。”
我逐渐加快脚步,最后冲上去用手里的石头狠狠砸他的后脑勺,他顿时抱头怂大叫,色厉内荏地咒骂,也捏起拳来要打我。
我后退躲避,眼疾手快拿起墙边的钉耙与他对抗。我胡乱挥舞钉耙,不怕将他打死,他连连后腿,捂着渗血的头,又急又气地骂我是疯婆子,全世界男生死绝了也不会有人喜欢我!
二哥见场面劝不住也拉不住,像一只畏畏缩缩的耗子拔腿跑了,跑去找大人来震慑我们。
等大人来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凄凄惨惨大哭,先一步诬赖大堂哥骂我是没有娘的野孩子,我爸老实人活该,还是大娘私下说的。
他百口莫辩,也不好说自己欺负了青子。
大爹还算知道息事宁人,他不管堂哥的伤,不由分说开始揍一顿先,且骂道:“上次你就那么说你同学,现在连你妹妹都说,你是不是人!你这个臭小子!”他并凶巴巴地吼护子的大娘,“你看你教的好儿子!平常就知道护他!还净瞎说些什么话?叫你们不要惹西西,说多少遍了!我娶了你这喜欢论人长短的婆娘也是倒霉!就知道嘴碎!你儿子被打活该!再不好好教教,早晚在外面被人打死!”
大娘一张嘴吵不过长辈和丈夫,扯着嗓子干急叫。
在大人没看见的时候,我稍微勾嘴挑衅而笑,看着对方有冤不能伸,有苦说不出,我还想将他往死里整,便捂头喊疼,晕了过去。
不止大堂哥伤着了,我也有点受伤,额头也被他乱丢的石头割破了一个口子,女孩子皮肤到底嫩,一个小口流得血比他还要多。实际上,我知道砸他后脑勺那一下更疼,我只是看着可怖了一些。
这下还能逃窜的大堂哥被骂得更狗血喷头,所有人一齐指责他,骂他不让妹妹,没尽到大哥的责任;骂他嘴招,好的不学,学他母亲常论人长短;骂他招惹谁不好,招惹连老太君都得让着的小祖宗!
爷爷甚至捡起钉耙,气得用棍头大动作敲他的背,现场乱作一团,奶奶想主事第一次没人听她的。
连代娣也特别生气,破天荒得理不饶人,估计她以为丈夫的尊严被小孩子学样践踏,才气得慌。我绝不会以为她是为了我。
我险些演技失常笑出来,青子只静静地呆在我身边,捏起袖角小心翼翼给我擦头。
我被挪到屋里躺下后,他们商议着喊一辆面包车送我去医院,却被爷爷阻止了。爷爷说,现在送去,血都结痂了!赶紧喊村里那老大夫过来瞧瞧,先打盆温水来,我来给西西擦擦血!
一番齐心协力的急救以后,爷爷嫌人多嘈杂影响我休息,将他们都赶出去了,也不听大爹给我爹的赔不是。
活该我爸是老实人那句,杀伤力相当大。我大爹故意在爷爷面前放低姿态,博取原谅呢。我爹从来不多计较什么,也陪了个不是,在他眼里一家人和气最重要。
只是爹出门前,我莫名感受到他定定看了我一眼。
没晕多久,我虚弱睁了睁眼睛装苏醒,爷爷靠近悄悄问:“醒了?装得忒像,比小时候像那么回事。”
我们从前配合的时候多了,怕隔墙有耳,才警惕说话。我睚眦必报,记仇很,“哼,你刚刚打那个臭癞子,一点也不重,虚张声势而已,爷爷,你要重新给我报仇,他太讨厌了。”
臭癞子是我对大堂哥的贬称。
“好好好,以后慢慢收拾他。”爷爷怕我情绪激动,将血崩出来,先稳住了我。
可是我已没有幼时那么好哄,“你骗人,只知道答应。”
爷爷偏心也不是偏得没度,他板脸训我,“你以为大家心里都不知道你那小伎俩?只有你大爹家先惹了人,心里没底,才不敢验真假,不是有我这个老头子在,他们谁让你?别得理不饶人,气都出了,就算过去了,下一次他再乱说话,我第一个罚他!”
“他...他...。”我气得将额上的纱布扯掉,裹住被子以后便不言不语。
“他什么呀他?”
我仍旧不语,爷爷好话说了半天,渐渐少了话,气氛也宁静了,他喉咙里含混似有异物,缓慢而沙哑道:“西西,爷爷最多还能活个几十年,你每年暑假寒假都要回来一回,以后工作了大概就一年一回,这么算...爷爷还能见你...手指头都能数清的次数,下一回...,”他说到这儿有些停顿,上下移动着喉咙,似乎极力想要将喉结上的异物吞下去,他稳着情绪道:“真到了下一回,爷爷还做西西的爷爷。”
我忽然什么脾气也没了,也没话要说,只安安静静等他重新给我包扎伤口,这时,门口突然进来了一个人影,我急急将要躺下,她出声提醒,“是我,我妈喊我来看你。”
青子手里提了一小袋药,她走过来搁在床边,慢慢拆开药盒子,“她骑三轮车去镇上的药店里买了消炎的药回来,叫你内服。”
爷爷老脸和蔼地接过那几粒药,“你妈怎么不亲自来,每回派你。”
她端起桌柜上的半碗水,仔细交给爷爷,“我妈说,西西不喜欢看见她虚伪,说小孩子显真诚,所以叫我。”
“真是有心了,西西还不明白,我们几个老的大的都看在眼里,你妈妈贤惠,我儿子这回有眼光的叻。”爷爷从不会讲我不懂事,而是说孩子还没能明白,就得教她明白。他曾说,人活着活着,自然也是会明白的。
青子稍稍低头,笑容干净,有一些憨,有一些羞。“其实家里,爷爷最明事理,最好了,看着偏,其实都尽量悄悄地端平一碗水。”
......
我见不来两人互夸互捧,夺过碗利落吃了药,冷脸翻一个身躺下了。既然有放心的人守着,爷爷便脚步略急出了门,我心里明白他是要去看臭癞子。
等屋里只剩下我二人,青子坐在床边欲言又止,我我我...你你你...没说出个所以然。我心粗气浮,坐起来毒舌说:“还想不想要脸,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打他们?”
青子一下攥紧了衣服,手背骨清晰分明,她憋许久也没憋出一句话,我们大眼瞪小眼对视,她的眼眶渐渐微红,待委屈到极点她终于振振有词回应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跟我妈在你们眼里永远是外人,我必须得忍,最要忍的就是你!哪里像你这个小混蛋能为所欲为!”
我并非哑口无言,我只是不知该如何骂她,我为所欲为和大堂哥的为所欲为能一样吗??
静有分钟余,我在一片清冷中说道:“我顾忌的不多,就算所有人不爱我,就算我爹把我扔了,我也不怕,我自己爱自己就行了,人活在这世上,犯得着让自己不痛快吗?大不了你们就是走啊,这么死皮赖脸呆在我们家,就不要抱怨。”
“你根本不清楚我们的境地!你以为我跟我妈容易吗?!”她嘴巴呼哧呼哧向空气索要着什么,气氛这样僵,她干脆出去冷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