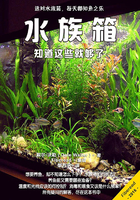十几岁时我也认为,黎明前的天是最黑的。
几十岁时我在日记本上写下,那天宛如垂暮年人历经多年世事而剩下的疮痍,却有不被磨灭的一丝白光。那是青年的尾端,也是老年的伊始。
滴答——滴答——
雨水声断断续续缭绕在耳,房檐上的雨滴得越来越慢,仿佛融入了平静的心脏深处,渐渐,一股嗡嗡的耳鸣刺入大脑。
神经疼痛之余,白光茫茫中,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现身于眼前冲我微笑。她说,我叫徐知青,我以后可不可以做你的姐姐?
眼尾悄然淌出一点凉意,缓缓冷到了我耳上。梦境在大脑中肆无忌惮晃着,我近年模糊的记忆急速倒退,随着梦回到了几十年前,远远的记忆反而愈加深刻与清晰。
那是一个阴雨常在的冬日,天总是如将死病人缓缓离去的日子那样阴郁。记忆里的当时多是灰暗色调,不清楚是天空压抑,还是年幼的我对于外界的通感而压抑。
正门口响起“嘚嘚”的敲门声,在草稿本上写鬼画符的我,大概料到是代娣阿姨来了。她最近是我家常客,总要来坐上一坐,并且每次都会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还会给我梳赏心悦目的小辫子。
我始龀时候,只晓得代娣阿姨和我眼中的“好东西”很挂边,其余人给我买礼物的话,我爹从来不是那么好说话的,总要我把礼物还给人家,不许要。即使是当着他的面收下,他也会严厉地朝我使眼色。
这件事上,他端的认真与严肃。
惟有代娣阿姨买给我的礼物,他会默认我收,有时候我紧紧地抱着礼物,小心抬头瞄他一眼,甚至能看见他在跟我点头。
因而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本能扔了手中的蜡笔,马上光着脚丫子跑去开门。厨房里做饭的当家人会提醒我说,开门前要看一看猫眼,别咋咋呼呼的,放个坏蛋进来。
我拉过小凳子,踩上去站稳,眯着一只眼睛看向猫眼。这个面相和善的女人不管有没有人在,都是一副温柔到微笑的样子。认真点来说,好像是她的眼睛在笑,眼睛本生得大,皮肤也黄皱,双眼一若有若无弯起来,明显,生动。
确认了有无危险,我才开了门。
门外的景象叫我微愣,何代娣身边站了个高我一头的女娇娃,她明媚的眼睛和代娣的一样很大,大到我第一眼看过去,只先看到了这双神.韵独特的眼睛,她眼距有点宽,显得上半张脸灵动纯气,煞是天真无害。我想起了不久前在动物园看到的鸵鸟的长睫毛眼。
灰蒙蒙的楼道里,那件深红的厚实小夹袄也算是一抹亮色了,那姑娘的嘴和鼻子缩在暗绿围巾里,被打湿的睫毛上沾着亮晶晶的水点,水珠从她眼睑上顺着通红脸颊滑落至围巾上浸湿。
她手里已收好的篮格子伞上也流着接连不断的水珠,在地上留下一滩奇形怪状的水泽,像我以前即兴创作的一幅画。
我看水泽的期间,何代娣与爹的寒暄声已响起。“呀,西西今天真乖,还会给我开门了,大的为我们做菜,小的给我们开门,真是好温馨呀。”
“她哪是乖,惦记你买的东西罢了,我还不知道她么。”我爹动作较快地递过去一张干帕子,分外关心道:“嗌,你和这丫头淋雨了还是咋地,伞没打好吗?衣服和脸都湿了,赶紧擦擦,别着凉了,都快进屋子里来。”
“外面雨飘得太大了。青子,快叫叔叔,他就是妈妈跟你说过的,很好的叔叔。”代娣给那姑娘粗粗擦脸,导致她亮闪的眼睛频繁一睁一眨,小脸也微微躲闪,她嘴巴很听话,清脆乖巧地喊:“叔叔好,妹妹好。”
爹推了推我窄瘦的背,“你看看人家嘴多甜,你还不叫人,快叫阿姨和姐姐。”
我很讨厌叫人,即使长辈的称呼从喉咙里艰辛挤上了舌尖,像仔细竭力挤着将要用完的牙膏,从来也难以冲破我紧闭的嘴唇,至少我出生以后就是这样。
我在叫人的坎上老样子木讷,爹也不太逼我。他只是向何代娣说我不懂事。他前些年在外地忙,和家里聚少离多,未将我教好云云。
厨房里煮着快好的肉食,炒菜陆陆续续上了桌,我爹与代娣一边上菜,一边压低声音聊着我听不太清的话,他们说几句话还要瞟一眼我的方向。
我仔细侧耳偷听,隐约听见他们说,一个人带孩子是不容易,咱俩什么什么,还有搭伙过日子之类的语句。
这时候,和我一同坐在沙发上的女娇娃绕到我视线前面来。她歪头微笑,嘴角斜上两公分处微凹,小酒窝在她脸颊上甜得让我莫名生厌。她小心翼翼看着我,朝我伸出小手,似乎是要握手的意思,“西西,我叫徐知青,我以后可不可以做你的姐姐。”
我一下子就好像听明白了她的意思,结合我爹和代娣的小话。
空气凝结几秒,在她对我说了那句话后,我毫不加以掩饰自己的嫌恶,上前重重推了她一把,大声说:“我的姐姐早死了,人流死的。”
无厘头说完这句话,我在爹哭笑不得的责备声里回房关门。何代娣善解人意说,她只是个孩子。
正因为那句,她只是个孩子,我年少时期才有恃无恐做了太多错事...
他们都在房间门外喊我出去吃饭,我固执己见地说,代娣和青子从我家离开,我才会出来吃饭。显然这没用,我爹还粗鲁地拍了好几下门说,你现在不吃,今晚也不许吃!你今天这个举动让我非常生气!出来给你阿姨和姐姐道歉!
我捏着蜡笔混乱地涂新画本,一板一眼回答,我没有阿姨!也没有姐姐!
我听见代娣推搡拉走他的声音,踉跄的脚步声在地板上响着。她和气地劝他,也温柔地劝我,西西,你出来吃饭好不好?
不好!
西西,饿肚子给别人看的人很笨,你现在这叫...亲者痛仇者快。这是青子的故作成熟。
青子,别说话!代娣认真责备了她。
我生气把画本和蜡笔都甩到了门板上,恼怒骂他们。你们才是笨蛋!傻爹笨蛋!代娣笨蛋!徐知青笨蛋!
西西!不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要叫阿姨和姐姐!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暴躁。
我有一瞬瑟缩,哇一下放声哭出来了。
之后,他就没有再对我说什么重话了,只有代娣的柔声诓哄。她耐心地说,西西,那等阿姨和青子吃完了饭离开,你再出来吃饭好不好呀?青子今天为了来见你,打扮了很久,早饭也没有吃,刚刚冒雨过来,她又冷又饿,阿姨不要紧,可青子是阿姨的宝贝,我舍不得让她饿着冷着,就像你爹对你一样。
她的一番话,叫我哭得愈沉迷,我忽然想起了那个不算疼爱我的母亲,以及此时此刻因为外人而冲我发火、今晚不许我吃饭的爹。
等我没了声音,门外也没了声音。我一边把棉衣撩起来擦咸眼泪和清鼻涕,一边安静走到门边上,犹犹豫豫着,悄悄地打开了一点门缝。
他们坐在油污黏黏的圆桌上和气吃馒头,嘴边都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边吃边笑边说话。
那两大一小的家庭标配忽然使年幼的我感到心慌气短。
平素五大三粗的爹,这时心细地分别给何代娣与青子布菜,他还伸手捏了捏青子瘦巴巴的脸,笑呵呵说道:“太瘦了,比我们西西还瘦,多吃些肉,到了叔这儿随便吃,想吃啥就说,叔给你买。”
“谢谢叔叔,以后我长大了,叔叔想吃什么,我也给您买。”青子的嘴从一开始就是那么甜,甜得像她脸上的小酒窝,对别人来说,那是甜美,对于我来说,那是腻歪。
代娣给我爹夹菜的时候,神情里夹杂了局促和腼腆,也微微低着头,又似乎掩饰什么一般给青子夹了更多的菜,并嘱咐:“你吃好了,给西西端饭去,你们年纪小,容易处。”
“甭管她,她就爱瞎闹,饿了她晓得吃,不能惯这...。”青子坐起来夹了一大块糖醋肉给我爹。他前面的话都没说完,就立马端稳了陶瓷碗,说其余的话,“唉哟...这闺女疼人呢,真懂事...。”
我死盯着外面的一切,慢慢合上了门。
这个每次来我家,都会给我带漂亮衣服和很多零食的女人,我对她固然有好感,但不代表容许她这么亲近我爹。
我内心极为抗拒。
我不确定她为什么带她女儿来跟我说这种话的企图,但我当时明明白白感觉到,她们和其他来做客的女人不一样。
我在屋里低头转了一圈,再次打开门偷看,一眼望过去...青子的头发在冬日中并不干燥,乌黑光洁,鬈曲柔软,两只羊角辫整齐地搭在肩上,头顶光滑得像抹了摩丝一样。
她捧起碗文静用饭,神清目明,没有洋娃娃的精致,没有一眼惊艳人的五官,虽小小年纪却有别样的美人神态。
她甚至一粒一粒地吃干净粘在碗底的饭,也不让人觉得她不雅......
那是我人生中对一切模糊到黑白不明时,在朦胧初冬里,初次遇见了她。
然而真是可惜,这么花容玉貌的姑娘注定要成为我大半生里讨厌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