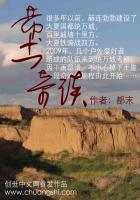杨广怒极,狠狠看一眼陈婤,喝道:
“带籁音!”
陈婤早已吓得跪倒在地,惶恐道:
“陛下,臣妾管教无方,那贱婢竟做出此等****后宫之事,臣妾甘愿受罚!”
杨广也不理会他,脸色难堪之极。我使个眼色,挽云赶紧上前,手捧一盏茶,递于杨广,盈盈笑道:
“陛下不必为这等下贱宫婢着恼,龙体要紧。籁音那小蹄子真是枉费德妃娘娘教导,竟背着娘娘做出此等事来。”
芬婕妤方才受了陈婤的喝斥,此刻巴不得落井下石,揶揄道:
“德妃娘娘为了陛下与太子,曾大义灭亲,何等的气节?令臣妾仰慕之至,不愧这个‘德’字。只不知怎的养出这么个不知廉耻的贱婢来。哦,臣妾想起来了,仿佛听人说,正是籁音举证,已故宣华娘娘所作的恶事才真相大白。啧啧,真不敢相信,竟是这样一个伤风败俗的女子,偏还装作一副忠心为主,大义凛然的模样,当初臣妾还一直教导身边的宫女,要以籁音为典范呢。”
芬婕妤这一番话,意在挖苦陈婤,却无意中戳到杨广的痛处。
对于死者,人总是会大度一些,或者心怀愧疚,杨广也不例外,宣华之事,或多或少都会令他有些心痛,毕竟,他们之间,曾经爱过。
杨广把挽云递来的茶盏重重往桌案上一掼,“砰”的一声,吓得众人再不敢吱声,永安宫正殿内,静得几乎连喘气声都没了。
我瞥一眼杨广,他盯着跪在地上的陈婤,眸中的狐疑一闪即逝。
籁音已被押至殿门口,我微微抚一下额头,面带倦意,言道:
“陛下,这些事本该臣妾料理,谁知臣妾这身子越来越不中用,现下又要头昏了,就只能劳烦陛下与德妃妹妹审理了,臣妾去寝殿小歇。”
杨广若念及宣华,必会疑心陈婤当初的举报,但也要顾忌到我,毕竟,宣华害的是太子,当初我亦是要置宣华于死地的。此刻,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躲避,我有皇儿在身,杨广断然不会惊动我,陈婤与宣华之间,虽为姑侄,但陈婤的情分较之宣华,却是差远了。
“爱后腹中有皇儿,也不便见这些****之人,先去歇下吧。”杨广体贴道。
当晚,盈袖来报,说杨广审问籁音,初时她不招,后来用了大刑,她受刑不过,只得承认,却又招不出与她通奸的男子,最后只胡乱供认是杨谅。
幸好有挽云在侧提醒,说籁音入宫不过一年时间,而杨谅已离宫多年,他们根本连面都未见过,加之籁音根本说不出杨谅的外貌,杨广一怒之下,将籁音活活杖毙。
陈婤因受其牵连,杨广便下旨将她禁足永福宫,并复降为嫔。
若只是教奴无方,杨广绝不会这般惩罚嫔妃,更何况陈婤又是他的宠妃。
至于原因,我心知肚明,杨广大概对婤举报宣华之事,仍是耿耿于怀吧。一个连自己亲姑姑都能出卖的人,他日若皇宫有事,恐怕她连杨广也会出卖。
“娘娘,奴婢不明白,为什么要先除籁音,若那肚兜是她主子的,岂不是可以一网打尽?”盈袖把外面的事跟我说完之后,不解的问道。
我默念几声佛号,心内难以平静,我的手上,又多了一条人命,籁音,终是我害死的,手上的鲜血又多了一层。
“她在宫中多年,行事谨慎,又岂是容易就范的?且不说别的,她的贴身之物必有专人仔细保管,你能取得籁音的东西,却难以动得她的东西。更何况——若是她的话,陛下定会一查到底,不只是会牵连甚广,更怕把她逼急了,她反咬一口。”
说到底,我是唯恐会连累到杨谅罢了,尽管杨谅已死,我也不愿他来背负这个****后宫的罪名。籁音进宫时日短,自然陷害不到杨谅头上,而如果逼陈婤过甚,深怕她一急之下,也如籁音一般,供认奸夫是杨谅。
投鼠忌器,不可操之过急。
盈袖点点头,仍有一丝担忧,言道:
“还是娘娘思虑周详,那宫的主子曾侍候娘娘多年,对娘娘必然了解,若是惹急了,难保不会两败俱伤。”
我不动声色,瞧着永福宫的方向,我深知陈婤绝不是个安分的,婆婆说得对,斩草不除根,必为祸患。只是如今我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比怀着昭儿时要赢弱许多,或许是那次出宫,身心交瘁,又在海上受了惊吓,伤了身子。
盈袖见我沉思不语良久,不由得问道:
“娘娘心里是否有了什么法子?她如今虽是禁足降了位分,却难保他日不会重新获宠,毕竟现在皇上只是在气头上,那人的姿色又是极出挑的,难保皇上不会念及旧情。”
“如今我暂时没什么法子,先由着她吧。如今她在禁足中,殿内局多是拜高踩低的,她的日子不会好过的。”
盈袖点点头,目中闪过一丝厉色,言道:
“奴婢自会去打点殿内局,这些年娘娘受了她多少委曲?岂可轻饶?”
我也不阻止,盈袖办事一向妥当,绝不会留下把柄。只敛神吩咐道:
“你得空查下苏嫔落水一事,本宫心里总觉不踏实,她未必就是真的失足,哪有那般巧合的事?更何况,那****去过沁凉斋,若是她见过那个合欢结,岂不是成了本宫的隐患?我须得知道她是否与陈婤同气。”
盈袖答应一声,服侍我安寝,临睡前我又吩咐道:
“本宫身子最近很是不舒服,宫中的人也未必都忠于本宫,若是再出一个芹儿可如何是好?你便辛苦些,从明日起,我所有饮食都由你亲自负责,除了婆婆与狗儿,其他人都不能信,直至本宫顺利产下皇儿。”
即便是杨广指来的团儿圆儿,我也不能深信,毕竟事关腹中孩儿,须得处处谨慎。
一连数日,宫中渐趋平静,合欢结之事也慢慢的被人遗忘,陈婤禁足在永福宫,自然门可罗雀,苏可儿调养身子,我则养胎待产,都不方便侍寝,后宫再无专宠之人,杨广雨露平分,宫中姿色不错的妃嫔均有些恩宠,尤以挽云与芬婕妤得宠最甚。
日子就这样平静的滑过,转眼已到夏日,杨广每日都会来看昭儿与晗儿,并留在永安宫用膳,然后再回仁寿宫,召幸妃嫔。
我的肚子也渐渐大了起来,行动有些困难,离临盆的日子屈指可数。
这一日,我懒怠动,正吩咐人多加些冰块,在殿内美人榻上小歇。眯眼看着一块块冰块慢慢化成水,心里也缓缓沉静下来。
“娘娘,云婕妤求见!”狗儿言道,“若是娘娘身子不便,奴才就去回了,让她回去罢?”
我摆摆手,言道:
“不必,叫她进来吧。”
挽云面色嫣红如霞,眉目之间尽是难抑的喜气,有些激动,浅施一礼,言道:
“臣妾见过娘娘。”
“不必多礼,挽云来得正好,本宫正闲得难受,想找人说会子话,可外面天气委实太热,所以便躲懒赖在殿内。”我懒散道。
挽云微微一笑,言道:
“娘娘不是躲懒,娘娘是在为腹中的小皇子着想,刚才臣妾问过稳婆,说娘娘也就这半个月的事了,自然不能太累着。”
见她言语之间带着欣喜,时不时羡慕的盯着我高高隆起的小腹,心里微微疑惑,打量她一眼,心下已有了些底,于是笑道:
“本宫瞧着,你今个儿倒是有什么话要说呢,瞧把你乐得,有了好事还不快些与本宫说说,也叫本宫乐乐。”
挽云羞赧的垂下头,咬了咬唇,低声言道:
“臣妾,臣妾已有了两个多月了。”
“真的?”我心内虽有些失落,却也是一闪即逝,面上挂着喜色,起身道,“果然是大喜事呢,陛下可曾知道?”
挽云脸色微红,言道:
“臣妾刚刚身子不舒服,请了御医才知道的,并不曾告诉陛下,先急着来告诉娘娘了。”
我呵呵笑道:“是紧着先来本宫这讨赏吧?”
挽云嗔笑道:“皇后娘娘这般打趣臣妾,可不怕腹中的小皇子笑话么?”
一时间闲谈半日,吩咐圆儿取了各色珍宝赐予挽云,待到天色渐暗,方吩咐人仔细扶了挽云回宫。
宫中的孩子不易活,须得处处谨慎。不过还好,陈婤已被禁足两个多月,这段时间宫内一直风平浪静。我遥望着永福宫的方向,心内仍是担忧,陈婤留在这宫中,终究是一份危险,如今我临盆在际,分不出身来对付她,若她能一直安稳下去,我也不愿多造杀孽。
但宫中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静,苏可儿身子养好,已能承宠,杨广更加怜爱,她失足落水一事始终是个谜,任盈袖如何打探,也只是查到那一日苏嫔去沁凉斋赏景,出来时走路十分急,不小心踩到那块桥木,跌落水中,而孩子也因此而夭折。
后宫嫔妃谁受宠,谁争风吃醋,于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原也算不得什么事,至少没人会对我形成威胁。
然后,我的威胁却又来了,在我腾不出手了结祸患之时。
挽云怀孕的次日,我便听得杨广解了陈婤的禁足,细一打听,竟是陈婤已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
几乎要悔青了肠子,直恨自己为何一时心慈手软,只以为她会一直幽禁,直至终老,毕竟后宫佳丽众多,杨广新欢在怀,对于一个失了宠的旧人不会再有所停留。
大错特错,杨广知道陈婤怀孕,龙颜大悦,不仅解其禁足,更是赏赐不断,甚至已远远超过挽云。
我恨声道:“她不是在禁足么?陛下又如何能得知她怀孕的消息?”
狗儿恨得双目通红,握紧了拳头,回道:
“奴才买通了永福宫两个小太监,他们说是那主子日夜弹琴,直至累倒在琴台上,是宫里的婢女拼死逃出永福宫,去向皇上禀报,皇上一时怜悯,就派了御医去,结果御医回来便报,就是那主子怀上了。
皇上一时高兴,便去看望,却见她倒在琴台上,哭得昏天暗地,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皇上又在她寝殿内发现了许多诗书,均是写给皇上的,皇上大为感动,立刻解其足禁,并陪了她整整一个下午。”
狗儿说完,仍是气愤不止。
我却觉一阵头晕,陈婤竟也学我当初一般以怜邀宠,她本就模样娇俏,若再刻意装出几丝憔悴,定然是楚楚可怜之极,再加上那些表白“心迹”的诗书,杨广焉能不动心?
“去帮我查查那名御医的底细。”心中总是不信,哪有这般凑巧之事?恰好禁足之后怀孕。
我恨得牙根直痒,陈婤复宠,必是我的劲敌,更是后宫之祸,在杨广颁布旨意,复陈婤德妃之位时,我终于忍不住倒了下来,小腹阵阵抽痛,疼得我咬牙难忍,在众人的呼唤声中,昏厥过去。
漫长的梦魇过去之后,我醒来时,浑身虚弱之极,几乎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动不动的躺着,我的孩儿,提前半月生产。
然后,便有无数笑脸纷涌而至,纷纷恭贺我产下二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