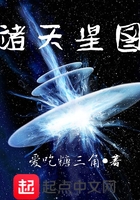“你这是要随我一起回齐坤宫?”
从议事殿出来,马三安就一路紧跟着,一副跟定他的样子。
“陛下。”
这时,江敖出现在几人面前。马三安看到他后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你知不知道今日在街上陛下被行刺了!”
听到这话,江敖一把推开马三安,无比紧张地看向木沉白。
“是我吩咐他把街上的禁军都撤了。”
木沉白将手放在马三安的肩上,浅声道:
“你们各有任务在身,我也有自保能力,不必介怀。”
“陛下,你明知道那些人留不得。”
马三安抱拳跪在地上,一直沉默在旁的裴元也跪在他旁边,闭眼颤声道:
“臣附议。陛下,微臣恳求您,即便留他们的命,也不能再任之由之。”
听到这话,江敖也跪了下来。
“陛下,以他们现今的势力,根本不可能得知您的行踪。除非他们借……”
“都起来罢。”
木沉白背过身去,一双黑眸映着夜色里的几点萤火,“把他们身后的人揪出来便可。还有,今日之事谁若传到了丞相耳中,我便送谁回老家看牛。”
跪在地上的三人皆红着一双眼望着地面,忽然马三安起身,又跟上已经走远的那人。
“江统领,你去哪?”
看到江敖转身离去,裴元慌忙起身,因为过急还踉跄了一下。
“我不会去找丞相的。”
江敖回头盯着他,“但若被我发现他们还有动静,到时裴大人就去替您的几位故友收尸罢。”
江敖说完大步离开,裴元仰头望着上空原地慢慢旋转一圈,哀叹道:
“其实只要转身,皎月就在身后啊!”
为何他们还不懂呢?
月明星也灿。
一个黑影踏墙飞入高院之内,竟连刚刚在此巡视的护卫也没发觉。
几经兜转,黑影进入一个内院中。
恰时,一位穿着青色睡衫的男子将手中的一碗水泼在地上。
两人对视,那睡衫男子脸上晃过一抹惊色后,转身准备回屋。
“今日之事你参与了?”
听到这话,那人重新转身,对着他轻笑道:
“江统领深夜而来,是找小人求医?”
“我再问你,今日的事你有没有参与!”
这时院外传声响,江敖侧身,看到一位两鬓斑白,样貌却不算苍老的男子朝他们急步走来。
“江统领口中的是何事?”
中年男子问道,看到江敖不出声,他不禁后退一步,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盯住屋门口的年轻男子。
“轩儿,江统领口中的事你有没有做?”
“没有。”
睡衫男子开口,听到这句江敖将手握成了拳。
“那你知不知道?”
“知道。”
好一个知道。
江敖低声一笑,“你知道。今日遇上我时却一声不提。孙瑾轩,从此刻起,我们之间再无情份,哪怕等元阳王醒来你知晓一切,也休想再靠近沉白一步。”
“你真的觉得他还能醒来吗?”
孙瑾轩喊住那个背影,却只听到他扔下无比冰冷的一句,“他是伤,你是医,如何来问我们。”
看到他翻墙而去,孙瑾轩对着那个方向大喊道:
“我是问你们,他还能醒来吗?”
他是医,自然知道他能不能醒!
“轩儿!”
一声怒吼将他的目光拉扯回来,望着对面人悲恸的神情,孙瑾轩缓缓走下台阶。
“父亲,我没做错。”
他没有参与,他没有!
“你错了!你怎么还不明白,你错了!”
“我没有。”
孙瑾轩右手用力握住那只碗。
“为父也错了,为父当年也错了。”
孙修逸双手握住面前人的手臂缓缓摇头,“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些年来是他们在力挽狂澜,是他们在苦心支撑,北朝没有他们,四年前与北辽的战争便输了,山河一破,焉有完卵?”
“是。当年是他们骁勇,我从未抹杀过他们的功绩。可与北辽一战,是元阳王出谋划策,他也浴血沙场,这功绩有他,王位是他,如今在宫里的,应该是元阳王!”
“你还要固执到什么时候!”
孙修逸颤声道,“你与他们在嘉州那么多年,你觉得陛下是为了皇位能对亲叔叔痛下杀手的人?”
“王权富贵,自古以来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的还少么?再说,他木沉白哪有承继大统的资格,父亲您知道,哪怕不是元阳王,也轮不到他。”
他就是一路攀附着元阳王,次次揽功,才得丞相的另眼相看!
“你糊涂啊!”
孙修逸狠狠推了他一把。
“你怎么就不想想,元阳王不省人事,你口中有资格继承大统的是哪些人?若是他们上位,如今的北朝又是何面目?”
孙修逸颤抖着双唇继续道:
“你从小就说,南丞相是国之重臣,是社稷之福,可你怎么就不想想,先皇在世时他南北篱也是丞相,百姓也拥戴他敬爱他,可是当时南北篱如何?他每每呈上的折子都被驳回,每每在朝堂同那些乌合之众奋力争辩,他口中利国利民的举措,没有一次被先皇实行过!可如今呢?如今他可有一次因为朝堂之事而心有余力不足?他哪一次真正惠民利民的举措没有落实过啊?”
孙修逸缓缓闭上眼,等睁开时他凄苦一笑,“你如今只是专门为元阳王而存在的御医,所以你不知。你不知道国库在两北之战时就已所剩无几,连正在浴血奋战的将士都发不出饷银。战争结束,马革裹尸,不说棺材,连活人都没有一口饭吃……”
“你除了家和元阳王府,连锦城都没好好看过。这四年间边疆的战士为何能有比先帝在时更丰厚的饷银?为何百姓的赋税相比从前能减免至此?为何从南到北坊间谈起新帝时都津津乐道无不动容赞赏?为父的答案,是辞官行走的这些年得到的。轩儿,你的答案呢?困于偏见与执念,困于小小一方的你,答案从何而来?”
孙瑾轩抿唇不语,这些他没有深思过,却有浮现过。
“轩儿,为何反抗的都是一些元阳王的旧部?为何偌大的北朝没有百姓站出来?因为百姓们是最真实活着的,茶盐油米住行衣,都要靠他们的双手去挣!他们根本不在乎朝政几派,也不在乎究竟谁有资格继承正统,他们只在乎这个世道能否给予他们安平,能否让他们在安平中靠自己的双手争取他们想要的。而你们却以‘忠’为借口,以‘忠’为高尚,好似高人一筹,实则将千千万万百姓的安平往深渊推去,失了大义。”
孙修逸拿起对面人手中的碗,随后松手,碎了一地瓷白。
“才经历战争不久,你们便要忘记这‘安平’有多娇贵么?只要你一不留神,只要你稍稍松手,便满地疮痍。非重头从粘土再来,回炉历经火焰灼烧不可塑。可即便再出来,它也未必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到时,又再破再重来?你是医者,该明白万千生命不是粘土,烧一次便死绝一回。”
万千生命不是粘土,烧一回,便死绝一回。
“那,该如何?”孙瑾轩颤声问道。
“白瓷之中锦上添花,不更好?你是医者,你曾说过,你不如元阳王睿智,不如宁王骁勇,可你有医术,能用医术救智者医勇者。你有你的长处,不该只困于元阳王府之中啊……”
“轩儿,若今日陛下真被重伤,争权夺势的人再涌,邻国趁机再乱,你的医术,能救下因为动乱而失了安平的万千性命么?轩儿,万莫在政见上清高桎梏啊。你想要答案,便亲自去寻,不要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