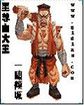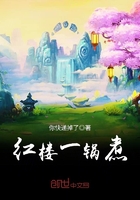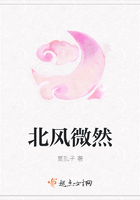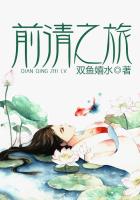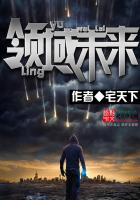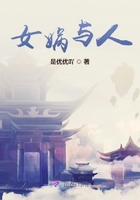此时,涑水乡中,司马光正摸着花白的胡子,站在田间地头,望着这片广袤的大地而感慨着。
“想我于宝元年中举入仕,到了现在,也已经有四十年整了。”
天禧三年,司马光出生于父亲所任职的光山县,光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六岁时父亲司马池便教他读书认字,所以他幼时便聪明过人。最著名的,莫过于“砸缸救友”这件事情了,至今还在东京城内传颂,成为了家家户户教育小孩子的典范。
司马家族毕竟也是官宦世家,对司马光的培养也不算少,故而司马光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更加聪慧乖巧,时有“凛然如成人”的说法,正是对司马光的褒扬。司马池曾辗转多地任官,带着司马光及家人游历了大好河山,故而司马光自小便眼界开阔,更是知识广博。
宝元元年,司马光二十岁,参加会试便一举高中,在任职时年轻的司马光不愿在京任职,而是远赴他乡,他选择了十分穷苦的华州(今陕西境内),因为他曾听父亲对他讲过关中大地那些悲惨的百姓境遇,还有那些神秘的民间故事,凡此种种都决定他要去偏远的华州来作为自己的第一个任官地。
好在华州离当时父亲的任职地不愿,司马光也能尽到自己的一片孝心,一家子生活倒也融洽和谐。只是好景不长,在辗转多地的途中,父母接连离世,正在仕途蒸蒸日上的司马光必须要守丧三年以尽自己的一番孝心。
这几年,他除了服丧之外,便是细细研读书籍,将悲痛化为自己奋进的动力。不仅如此,司马光还深入到百姓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生活,也正是这些年,司马光才了解到百姓生活的不易,从而更坚定了自己入朝做官,造福百姓的愿望。
庆历四年,他结束了自己的守丧,处处任职,每过一处,便尽心竭力,最终算是政绩赫然,一直到庆历六年,中央任命他进京任职,同僚们虽是不舍,但毕竟是好事,于是设宴送行。
司马光深切地记得那一日的场景,于驿站内,诸位设酒作宴,欢送司马光,只是那日,更是不舍多于相送。
“司马知县此去一别,可是前路浩瀚坦荡,只怕来日你我相见,你已经成了朝廷大官,而我却还是县里小小一个判官罢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言语中多是不舍,有感慨司马光在任功绩斐然的,有赞叹司马光政治清明的......一片叫好。
“诸位莫要挽留司马知县了,他本是那鲲鹏一般的大人物,怎么能拘泥于我们丰城县这一方小小地界呢?”人群中一个较老的官员站出来,沙哑着声音说道。
“正是,老人家说得对啊。”几位官员纷纷附和着。
“君实你尽管去吧,到属于你的天地,完成属于你的丰功伟业,只是莫要忘了我们这一方水土,莫要忘了这些可怜的百姓们啊。”老人又开口道。
司马光站了起来,自己倒了一杯浑酒:“这酒虽浑,乃是百姓们赠予大家的,想我刚任职时,百姓们穷困不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何来饮酒一说啊?几年光景到了现在,已经能饮上浑酒了,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努力,早晚有一天,所有的百姓们都能摆脱贫困,从浊酒饮上清酒!”
这一番话虽然朴实,但却点燃了在场所有官员的心。众人纷纷喝彩,为司马光的雄心壮志而呐喊,司马光内心也有一股难以遏制的激动。
酒过三巡,司马光端着酒杯站了起来:“诸位,今日我便要到京任职,请诸位放心,我司马光对着这杯酒发誓,进京必要完成一番大事业,让百姓们都能够安居乐业,最终再现我大宋荣光!”
而后,司马光向左右讨出纸笔来,借着酒势,醉成诗一篇。
“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
众人也潸然泪下,虽有万千不舍,但毕竟时辰已到,司马光只能在众人的不舍下离开这里,向着他毕生的梦想而前进。
到了京城,他结识了王介甫,梅圣俞,欧阳修等人,几人常常来往,意趣相投,文人交往,多是诗歌来往,也常常尽兴到大醉而归。
后来,面对朝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几个人也出现了不一样的争歧,王介甫主张效仿卫鞅改秦一般推行新政,而司马光主张总结古代经验而治理,二人因政治矛盾久争不下,最后还是王介甫亲自设宴,二人才避免了一场“战争”。
虽然事情已经久远,但司马光还记得王介甫所说的话。
“司马公,你我二人皆是为国寻出路,你愿仿古,我意革新,虽然路途不同,但结果确是如一,或者说,你我殊途同归罢了。”
是啊...殊途同归。
于是自那时起,司马光不多过问政事,而是潜心于研究古代经典,想要从其中找到些方法,而这时王介甫说服了新任皇帝,也就是现在的宋神宗,开始了自己轰轰烈烈的改革。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司马光仍然好斗,联合多人共同抗争新政,不出所料,王介甫的第一次新政以失败告终,司马光也坐到了朝廷的高位。
当然,身居高位少不了的就是推翻新政,司马光在推翻新政的时候也不免对新政有所研究,最后突然发现,王介甫的新政条条剑指朝廷弊端,这时司马光对新政产生了一些兴趣,但因为自己曾公开反对新政,不好出面,所以只讲这事放在脑后。
没曾想,今年初,元老重臣曾明仲方去世不久,皇帝就急急召王介甫回朝,这一切都打乱了司马光的部署,更没让司马光想到的是,只是换了个年号,这个朝廷却像是新朝一般。尤其是几出意外事件的发生,让司马光越来越难以支撑高位。
想来想去,司马光最终决定告老还乡,潜心于《通鉴》的编纂——这是他寻求救国的道路,如今王介甫已经风风光光大刀阔斧开始改革,而他司马光却还是整日居于书房内编纂史书。
临走的时候,他去找布衣谈了很多。
最终,布衣让他给苏子瞻——他最喜爱的门生——写一封书信,告诉他今后的道路。
“朝中凶险,你这个门生早晚要在朝中吃亏,所以在下建议,司马学士应该为你这位门生指明一条道路。”
司马光当时也有这个想法,二人一思索,司马光立即得出了办法。
“范先生,在我看来,与其苦苦坚守旧制度,不如让王介甫搞一搞,我和他也相识甚久,我相信他的本领。”
司马光说完一脸镇定,但布衣的表情却颇有意思。
“朝中上下哪个不知道你司马光带头反对新政,如今却说支持新政,说出去岂不是被天下士人耻笑么?依我看,你不必直言告诉你的门生应该支持新政,而是看他怎么办,换言之,你只需要告诉他如今的朝局,在下相信,司马学士钦点的门生,应该不会愚笨至极他应该能分辨有何可为,有何不为。”
于是,司马光给苏子瞻留了一封信,之后想了想,又题了一句诗,想要提醒苏子瞻。
司马光想到这儿,不禁又想起了苏子瞻。
“只是不知你苏子瞻,将来还要遇到多少考验啊。”
另一旁,当时看到书信的苏子瞻也是聪慧,读到老师模棱两可的话语,便大致知道了司马光的意思。
“老师经年与史书打交道,言语必然严谨,书信突然如今日般暧昧,只怕老师的意思是让我自己权衡吧。只是老师常年反对新政,也许是让我对新政再次观望吧。”
苏子瞻之前就曾反对过新政,但那是跟着司马光的意思,如今司马光也已林朝,今后的路还需要他自己来走啊,苏子瞻不由得一阵叹息,感慨前路阻长。
苏子瞻不知的是,就连自己最信任的老师司马光,此时也在忧虑中。
回到祖籍家乡的司马光并未有过多的喜悦,相反更是眉头紧皱,看着同县百姓们仍然一贫如洗的生活,仿佛和自己刚任职在丰城县一样。
又是一阵叹息。
“王介甫,老朽相信你的实力,若是新政推行,能让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便依你的来,但若是推行不成,等老朽史书大成,便是新政覆灭之时。”司马光暗暗发誓道,这与他一贯的温良谦和不同,似乎多了些杀气。
王介甫怎么能知道这些?他现在只是忙得焦头烂额,一直在为新政推行而努力,生怕哪里出现差错,最终导致新政像上次一样以失败告终,他知道,以他的年龄,没有再迂回和重来的机会了,这一次,便是最后一搏。
正在此时,李定来拜访王介甫,告诉他司马光离朝的消息,又引起了王介甫的一阵慨叹:“那司马光与我早就相识,如今离朝,怎不是为了让我更好推行新政啊?”
与李定心不在焉聊了几句之后,王介甫便匆匆打发走了李定,之后王介甫对着书案上即将编纂完成的新政,自言自语道:“若是天下,连你我都难以改变,那么这个国家还有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