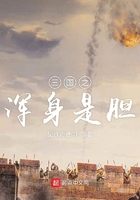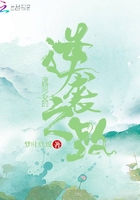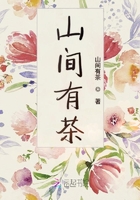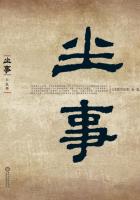王介甫本就赞赏叶元清,有想要将其纳入身边的意思,听到叶元清这么说,内心自然喜不自胜,只是没有流于表面:“叶先生可要想好,变法革新一事非是常人可为,若要变法,需不畏人言方可,叶先生可想好了么?”
叶元清沉声道:“屈原在变法时曾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下不才,难与屈原相提并论,只愿效仿古仁人之心,为国效力,共筑盛世,在下愿意从介甫公。”
介甫听完,激动地双手抖动,但还是为叶元清斟了一杯茶:“你我皆为文人,今日不便饮酒,不然此些时日,我必是要酌三大白的,那今日你我以茶代酒,如何?”叶元清也有些激动:“在下本是一士子,先前蒙皇帝大恩,中了状元,后又与太子共学,今日又承蒙介甫公关照,可谓荣幸至极,在下必尽此生所学,不负诸位大恩!”说罢一饮而尽。
“好啊。”太子赵熙也高兴,“叶先生和介甫公都是我所倾佩之人,今日二人联合,来日必然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做二人的见证人,待来日,你我三人必然共同见证一个盛世的再次兴起!”三人以茶代酒,碰杯而饮,倒也有些不属于文人的豪迈气概。
另一边,皇宫内。
离开的苏子瞻又被皇帝召回,此刻正跪在殿中,等待皇帝的命令。
“子瞻啊,你是不是认为朕会治你的罪啊?”皇帝看着他,语气中有些轻飘飘。
“回陛下,罪臣自知那日朝堂之上过于莽撞,惹了龙颜大怒,罪臣已知罪,望陛下宽恕罪臣,罪臣定牵马执镫,为陛下谢罪。”苏子瞻不敢抬头。
“其实朕并未动怒,爱卿那日所言不无道理,起身吧,朕召你是有别的事情。”
“陛下不说赦罪,罪臣不敢起身。”苏子瞻仍然跪在地上。
“苏学士请起吧,陛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呢。”李宪在一旁说道,苏子瞻没奈何,直起身子来,但还是低着头。
“抬头看着朕!”皇帝加大了声音。
苏子瞻不敢再低着头,缓缓抬起头来,正巧与皇帝四目相对,四人眼神交汇了好一会,刹那间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不知过了多久,皇帝大笑道:“果然,刚入朝时候的眼神都是一样,一样纯澈干净啊,这在朝廷这群老家伙的眼神中已经很少见了啊。”
“苏子瞻,方才王介甫的字字你应该也听得详细,不知你对新政有什么高见啊?”
苏子瞻揣测着皇帝问这个问题的用意,又想到之前章惇所说的话,没敢回答,皇帝像是看透了一样:“苏子瞻你刚入朝不久,怎么也想那群老家伙一样唯唯诺诺?有什么就大胆说,在朕这里,没有所谓对错,只有所谓利弊。”
“喏,”苏子瞻缓缓开口,“回陛下,就介甫公方才所言,臣以为字字珠玑,只是过于乐观了些。”
“乐观?”皇帝面露微笑,对苏子瞻的发言很满意,示意他继续。
“陛下也听到介甫公的计划了,但是臣在介甫公新政的计划中只听到了介甫公如何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而没有面对新政推行阻碍地措施。自古到今,历代变法怎么可能毫无阻拦?新政的推行不在于速度,而在于稳固,若是新政本身有利,并且能够早日扎根于百姓心中,臣相信,那新政的推行自然势如破竹。”
皇帝笑了笑:“这个想法也是有趣,那子瞻想了这么多,相信也有自己的看法了吧,不妨说说自己的法子。”子瞻从容道:“回陛下,方才介甫公曾说让各州派遣专人负责,臣以为各州疆域过大,新政施行中遇到的问题难以及时处理,久而久之可能会导致新政瞬时间崩塌,臣以为应精细到每县,每县安排两人,一人负责施行新政,一人负责监督新政实施,每县二人与各州新政官员在中央接受介甫公的教育,从而减少一律,各县在推行新政的途中遇到问题,可以向各州的官员上报,若是各州都难以解决,则层层上报,直至中央。”
“也好,但每县安排两人,只怕官员冗杂,众口难调啊。”
面对皇帝这个疑问,子瞻也早胸有成竹:“陛下莫要担心,就将中央的官员安排到地方,将各自的职责纳入官员考核,按照这样的考核,也有助于朝中甄选出能力出众者,同时将那些进士们也安排到地方,让他们了解百姓疾苦,从而更好做官,不知陛下意见如何?”
说完,苏子瞻看着皇帝,眼神中自然少了些恐惧,而多了些自信从容。
“子瞻所言,不无道理,这些等王介甫把新政具体下来再商议,只是朕今天要说的还有别的事情。”说完,皇帝向李宪挥了挥手:“据说你曾经与王和甫有来往,可有此事么?”
“回陛下,臣与王和甫相识于科举场上,平日里稍有书信往来,多是些文章之类。”
苏子瞻也纳闷,皇帝问这些难道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皇帝仿佛看出了他的疑惑:“前些日子里王介甫入南衙大牢的事情你应该也有所耳闻,当时朕的李公公带队抄家的时候,发现了王和甫给你写的信,只是皱巴巴的,所以朕想问问你。”
苏子瞻更疑惑了:“陛下可确定么?臣已经小半年未与王和甫有来往了,陛下说是王和甫给臣的书信,只恐是他人所仿制。”
李宪从皇帝手上接过去,递到了苏子瞻面前:“苏学士辨认一下,可是王和甫的笔迹?”苏子瞻接过纸,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只是书信内容越看越熟悉。
“回陛下,确实是王和甫的字迹,只是这书信的内容,和半年前他送来的信无二。”苏子瞻将书信递还给李宪,而后回答道。
“苏子瞻可知道司马公向朕告老还乡的事情么?”皇帝手上拿着书信,突兀问道。
“这...”苏子瞻想起来前几天章惇曾经找过他告诉他的事情。“回陛下,臣不知。”
皇帝明显察觉出了迟疑:“苏学士吞吞吐吐,莫不是隐瞒了些什么?”
听到这句话,苏子瞻慌忙跪下:“回陛下,臣不敢。”
“方才朕问你新政,你似乎并不拒绝,但是司马公在的时候,极力阻止朕实行新政啊。不知司马公可曾向你提到新政么?”
苏子瞻又愣了一下:“回陛下,臣长久居于眉山,少与司马公来往,未曾听司马公提及。”皇帝又笑道:“少有来往?谁不知你苏子瞻尊师重道?倒是那司马光,对王介甫本人赞叹有加啊,多次告诉朕要善用此人,说他身上有一股异于常人的精魄。好了苏子瞻,无事了,你先回去吧。”
“臣告退。”苏子瞻缓缓走出门去,心里还在不停揣测皇帝的意思。
司马先生的意思,究竟是支持新政还是反对新政呢?若是反对新政,不应在这个节骨眼上告老还乡,但若是支持新政,不应该让我之前在地方任官的时候与新政作斗争啊。但是司马先生又对王介甫赞叹有加......
苏子瞻捉摸不透前后司马光的意思,决定亲自到司马府上问问老师。
到了司马府上,还是那个熟悉的门童,只是今日换了个说法。
“主人带着家当先行出发回乡下了,他说让我在这里等一个叫苏子瞻的人来,并让我交给他两样东西。”
苏子瞻听完,有些失落:“老师果然还是回乡了。在下便是苏子瞻。”
门童听完,掏出两样东西交给苏子瞻,而后没有多说,闭上了大门。
苏子瞻接过来一看,是一面铜镜和一个锦囊,锦囊里装着两张纸,打开一看,一个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而另一个字迹十分稀疏。
苏子瞻揣测那个密密麻麻的是书信,另一个可能是题字,于是带着东西回到家中去了。
苏子瞻居所离司马府不算远,倒是有些僻静。苏子瞻出大殿时,天还晴朗,等到苏子瞻回家时,天已经灰蒙蒙的,仿佛稍后就有一场大雨。
夏日的天气总是多变,晴天时偶然一声惊雷,便可能就会带来几日阴雨连绵,而在阴云密布时,一束阳光就有可能拨云开雾。
苏子瞻坐在书案前,点了盏灯,准备开始细细品读司马光的书信时,猛地听到外面一声炸雷,等到苏子瞻站立正堂前时,暴雨已然如倾盆般落下,冲刷着京城的每一个角落,给难以忍受酷暑的人们带来凉爽的甘霖。
看着这场大雨,苏子瞻想到了司马光,雨天道路泥泞难行,想必行路人都会厌恶雨天吧。
是啊,当行路人们怒骂大雨滂沱之时,也许正有几家农户感谢上苍带来的甘霖,正在滋润着他们因天干而龟裂的土地,因为农户们知道,这场雨带给他们的是生活甚至是生存的希望。
当时民户常说:“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确实,农户们在夏旱之下期待这场雨太久了。想到这儿,苏子瞻又想起了王介甫的豪言壮志,嘴边升起了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