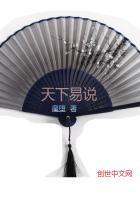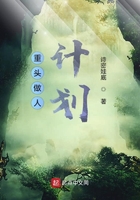门房听到后,笑嘻嘻拍了拍胸脯,“此物是一个爱慕小姐的浪荡子送来的,我看他一身布衣送的东西又是这等破烂之物,定不是什么和小姐门当户对的公子,定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街头浪子,便替小姐把它丢到了一旁。”
“浪荡子?破烂之物?丢到一旁?”严可儿眼中怒火中烧,“那您老人家便归家吧!”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带着那支竹节离开了门房的小屋子,只剩下了刚刚起身便无力地倒在摇椅上的门房。
归家?祭酒府的门房不仅是闲职,更是这京城中的香饽饽,说出去也是顶有面子的事情,若是被辞退,想到这里他想都不敢继续想下去,躺在摇椅上发起了呆,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这么舒适地发呆了吧。
孙小姐的话一向比大少爷更有分量。
还有几天,科举的金榜便要张贴在皇城大门前了。许多觉得自己无望的读书人已经早早离开了这中原大地最为繁华的大城。有些是带着无憾的微笑,还有些带着些懊恼和遗憾,更有些充满不甘。虽不知道还未看到金榜便毅然放弃的他们到底是有多没有勇气去面对结果,但这份无能已经注定他们能够金榜题名才是天大的笑话。
离去的士子们仿佛带走了京城的喧嚣,长安湖边的最后一场吟诗作赋大概便是前几日艳惊江南的名妓凌仙儿为大家表演霓裳羽衣舞的时候,那一曲那一舞让在座成千上万学子们口中的赞美都变得那么理所应当。此时的长安湖又恢复了数月前的冷清,此刻还在湖上的游船画舫应该便是真正的文人雅士了吧,当然也有苦苦追寻凌仙儿的浪荡公子哥。
可那日彩带飘扬锦缎连纵灯火通明的画舫竟是再也寻不到。
此刻素缟装饰的游船上,凌虚周看着白纱遮面远眺湖面的凌仙儿,微笑道:“你是要在这满湖的追寻者中选婿吗?”
凌仙儿吃吃笑道:“一群凡夫俗子罢了,他们的眼太脏。”
“京城的地址选好了?”凌虚周边询问边摩挲着腰间的木质令牌,“选址问题很重要,你可别不放心上。”
“我们拿了人家的‘忘尘符’真的还要在京城驻扎?”凌仙儿眉头微皱。
凌虚周微笑摇头,“那是我凌家的‘忘尘符’,不是人家的。”
“可宋家、平湖百晓生还有势力和实力都极为雄厚的天机宫都在虎视眈眈呀!”凌仙儿的眉头皱的更紧了些。
“那我便等他们来抢好了,若是我都不能收服八门,景月便更加不可能。”
“景月的身边现在有我们的七星,他一定想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囫囵之局。”凌仙儿淡淡道。
“宋老的作用应该已经发挥出来了,我们等着笑看朝廷大乱吧!到时候我也该进入这朝堂做点事情了,当年的周明党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揪出来,问问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哥,你确定这样不会弄倒大明的根基吗?”
“放心好了。”凌虚周胸有成竹地拿起茶杯在鼻子下面嗅了嗅,“大厦将倾,吾将出山,扶之。”说着,他望向天空,“你们在那边好好看着吧,我凌家儿郎总要向天下讨一个说法,你们不会白死的。”
凌仙儿似乎想起了什么,眼角的泪珠悄然滑落。
皇城一侧的观星监,国师宋珧经历上次开上楚贡品“云木端”盒子遭受反噬后,极少进行推演,此刻他忽然睁开双眼,望着南方又望了望北方,伸了个懒腰。
“童子,把我的天算盘拿来。”童子应声,手捧金银交错中有镂空布满天纹的盘子呈上前。
宋珧摸着天算盘,忽然双眸精光爆射,双手结下繁奥手印,天算盘上仿佛也有光波印文与之辉映流转。
“龙气入京?”宋珧双手缓缓放在了膝盖上。
他长呼出一口浊气,这一刻寒秋已至,中秋之时尚存的孱弱暑气彻底消散。
镇北军边塞,大明的版图上迎来了第一场小雪,虽然才是九月初,但这场小雪仿佛在预示来年是丰年。镇北军将领王炳真,昔日镇北军主帅大帅王毅德之孙,眺望着更北的北面,露出欣然笑意。
“爷爷,你和父亲还有叔叔们的在天之灵可一定要保佑孩儿。孩儿只想好好守着北疆,不想和郭一羡谢天狼之流去争什么北帅。”说着,他轻轻拍了拍身边高大的枣红马,“儿郎们,走,回家。”
说完,他翻身上马,一列数十骑的马队马蹄飞扬。在缓缓落下的小雪中返回营地,地上的青草有些已经泛着青黄。小雪虽然在飘,但天空却依旧是湛蓝,透着天空的明净。只是这片看似安乐的土地上,这片镇北军守护三十余年的土地上,自大帅王毅德死后,至今日仍旧无帅,之前朝廷为镇北军选的帅皆因不能服众仓皇而逃,甚至客死他乡。
昔日大明第一雄军镇远军,今日连个像样的名号都没,只能以镇守北方的名义称之“镇北军”。王炳真每每想到此处都不由得叹一口气。他今时今日仍能在镇北军中有一席之地,靠的不过是上一辈的遗泽,那些老将只愿意认他这位昔日大帅王毅德的孙子是镇北军正宗。
可这些老将靠的是名气和威望,镇北军最大的山头仍旧是拥有三千铁狼卫掌管上万兵马的儒将郭一羡,和手握三万骑兵,其中更是有一千镇北军重骑号称“战场屠刀”的血浮屠的老将谢天狼。
这两位的势力庞大,将掌管不足万人兵马的王炳真生生赶到了北疆最北处,整日都要与昔日占据中原大地的大楚王朝余孽——如今仅占领三郡之地的上楚遥相对视。
王炳真时长常问自己,“谁会是下一任镇北军大帅,上楚又会不会反呢?今时今日的镇北军积弱多年真的挡得住上楚的反扑和始终虎视眈眈的金帐王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