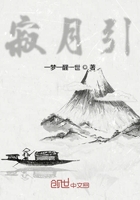尼烈就着油灯,在绢布上画了一女子,那女子蹙眉低头,举绫于胸前,虽笔法寥寥,但一宛若神女之样的女子已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樊石匠和下人既为画中的女子容颜倾倒,又为尼烈的画技折服,一时神情激动、赞叹不已:“这女子曲眉丰颊,衣裳简劲、神形妙兼,官人神笔,不在唐人周仲朗之下。”周仲朗是唐时大家,以画仕女著名,画刻一家,那樊石匠也对画作颇有精研,是以一见之下,对尼烈画功大加赞服。
尼烈哈哈一笑,将笔扔掉。他自幼聪敏好学,能诗善文,能言善辩,生性风流倜傥、志大才高,时人赞他“一吟一咏,冠绝当时”,“诗词雄浑遒劲,气象恢弘高古,画作也能咫尺而生千里趣”,遂道:“你连夜开工,为我凿出五个石像来,然后去附近镖局中雇请他们将这五个石像分别运往两湖和江、浙、闽、川五个不同的方向去,一路上大张旗鼓,说是神女白娘娘,半年后才许掉头回来。”
樊石匠打了一揖道:“官人吩咐自当遵办,只是……这一路花费的银子可不少啊。”
尼烈从破鞋里倒出了一颗宝珠,莹莹的闪着光气。那石匠等人万料不到这个满身污秽、衣衫褴褛的叫化子身上竟然还藏有一颗稀世珍物,瞪大了眼睛。尼烈道:“这个可够了么?”
樊石匠忙道:“够了,够了。”尼烈道:“你们连夜开工,凿好一尊后,便请人五日内送到襄阳去,若有闪失,我要拆了你这铺子。”一提掌,将一尊石狮像击得塌了半个角儿。
众石匠吓得大惊失色,半晌挠舌不下。尼烈这才跃了出去,回了客栈中。他深夜本想去闹场,却办成了这一桩事,心里喜滋滋地,直睡到日出三竿才醒。此后赵信和岳银瓶等人便大遭其苦头了,东奔西跑,走南闯北,历尽了数月艰辛和屈辱。
岳银瓶万料不到这一切是尼烈所为,又气又怒:“想不到你是这般的坏。”尼烈任她骂,笑嘻嘻的并不生气。
岳银瓶想到什么,道:“尼烈,你不是说只吩咐凿五尊石像而已么?怎地江湖上有这许多尊石像?”
尼烈怒道:“是啊,我只叫那樊石匠凿五尊石像而已,怎地后来有十多尊石像冒出来?此事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这樊石匠觉得我的珍珠大颗,凿五尊有些对不住我,怕我回去找他要找补么?他奶奶的樊石匠,凿了那许多石像,还叫那些镖师送得恁般远,害老子一路上吃了大堆的苦头。”其实这一路上尼烈已在对樊石匠暗中大骂了,那次他在低骂,正是怪樊石匠找的镖师脚力太好,送得太远,让自己走了这大老远的路,受了无尽的劳累,恰好被赵信听见,他打哈哈掩饰带过。
岳银瓶道:“你可以不跟我们去寻白姐姐啊。”尼烈眼中又露出淫光,馋涎欲滴道:“可是我舍不得你这只小羊羔呢。”又要对岳银瓶动手。岳银瓶忙又将他身子撑住,道:“不对,这些多出来的石像不似是樊老匠所凿的。”尼烈一诧道:“除了我想害这姓赵的,还有谁也想害他?你怎么知道不是那樊石匠凿的?”
岳银瓶道:“不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两三尊石像吗?如果是樊石匠凿的,他定不会一个地方送几尊啊,定是有人也让人这般送石像,只是不知那人是模仿你呢还是刚好与你不谋而合。”
尼烈一拍大腿道:“照啊,小姑娘就是聪明,我怎地想不到?不过咱们不用去想是模仿我呢还是与我不谋而合啦,也不用去想到底是谁也在害赵信啦,先让你尼烈大哥吃上几口再说。”一下抱住岳银瓶又乱亲乱嗅起来,岳银瓶吓得又尖声惊呼:”你好坏,你是个坏人……”
尼烈正在欲念大发忘情之际,忽然一声风响,身后似是甚物事打至,吓得急忙身子往侧一滚,一根棍子刚好从他头顶掠过,险些脑袋开花,吓得颤颤慄慄,抬头看去时,却见是赵信,更加惊心不已。
原来尼烈在计策得售大喜不已热血喷涌之时,赵信正好赶回到此,他哪里料得到赵信去而复回?幸而赵信也看不见他,怕误伤了岳银瓶,这一招便没有用上多大的力道,招式去势也缓,不然尼烈在忘情之际如何能避得开去?
岳银瓶见了赵信回至,一把爬起奔到了赵信跟前,扑倒在他怀里大哭:“赵大哥,你回来啦,呜呜,有人欺负我……”
赵信轻轻拥住她,道:“是谁欺负你?”岳银瓶道:“是尼烈大……是尼烈欺负我……”赵信大怒,抬棍指着尼烈,道:“想不到你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当下挥着手中长棍,推着付人婴向尼烈刺了过去。
尼烈见已占不得岳银瓶便宜,忙将衣衫穿好,从怀里摸出了两把匕首,格开赵信的棍击,然后着地一滚,攻向赵信下盘。赵信伸棍往下一劈,尼烈又向付人婴攻去,暗想:“你没有了这姓付的,还能这般利索么?”
付人婴被点了穴道,只能迈步走路,半点抵御不得,赵信一纵身将付人婴提起,长棍往下划成个棍圈将尼烈罩住。
尼烈惊挥匕首护住头顶,欲要将赵信的长棍削断,但无论如何削不到,只得哀叹一声,伏在地上就死,头顶上的棍风忽寂然不闻了。
尼烈大是奇怪,抬头一看,只见赵信手中执棍,凝神倾听,棍头在距他头顶尺余处停住,显是不知道他在何处。尼烈又惊又喜:“原来他瞧不见我啊。”提起匕首,猛向赵信下腹刺去。
岳银瓶忙叫道:“赵大哥,小心,他在你棍端下。”
赵信闻得风响,小腹往里一收,匕首距他身体尚余寸许没有伤着。尼烈一咬牙,要再将匕首向赵信腹中推去,赵信往后一点,挥棍而击,正中其臂。
尼烈断臂刚愈,中棍之下即又折断,痛哼一声。赵信长棍又斜挑过去,登时将尼烈挑摔了出去,重重的落在一堆荆棘丛中。尼烈被勾刺得皮开肉绽,爬将出来再也不敢恋战,将匕首向赵信一掷,滚下斜坡,奔逃而去。
赵信侧头避过,听得他已逃远了,自知要驱付人婴追赶已不及,悻悻不已。
岳银瓶惊魂得定,嘤嘤啜泣。赵信走来安慰道:“那恶贼没伤害到你么?”岳银瓶已将破衣处拉遮住,摇头道:“幸好赵大哥你救了我。”
赵信歉仄道:“赵大哥没照顾好你,差点让你误落贼手。真是对你不住。”岳银瓶低泣道:“本来是我要来照顾赵大哥你的,现下反而变成赵大哥照顾我啦,我真是没用,赵大哥你会不会嫌弃我给你添了麻烦啊?”
赵信微微一笑,道:“怎么会?你在赵大哥身边,也给我解了许多闷儿呢。”
岳银瓶化泪为笑,道:“真的吗?那我以后还是跟着赵大哥罢。”赵信笑着点了点头。她自识得赵信以来,赵信从没笑过,现下见赵信笑了两次,欢喜之极,浑忘了适才所遭之辱,又紧紧的拉着赵信的手臂,道:“赵大哥,我们快去找赵大嫂和张觉罢。”赵信又和她往前而去。
尼烈被赵信打了一顿后,负伤而逃,满腹怒气,路上遇着了几名村民多看他一眼,便被他拳打脚踢一番。
这一日,他肚子大饿,找不到充饥之物,便窜到山上一庙宇去,看是否有些供仪。正往神台上瞧去时,外面脚步声响,有人要来,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躲到了神像之后。
探头往外看时,进来的是一红衣和一紫衣女子。那红衣女子两眸清汪似寒渊,隐隐还带着一丝幽怨之色,那紫衣女子像是个丫环,手中还拿着一把碎花油纸伞。
尼烈眼前一亮,连日来的恁气烟消云散,暗喜道:“这是哪家的小姐和丫环?可比那个岳银瓶更有韵味多了。”
这两女子正是张红拂和小蕊。岳银瓶虽清纯可爱,让人一见即生喜意,然尚未长大,身形尚是个孩子,张红拂和小蕊则添了许多成熟韵味,气华诱人。尼烈一见之下,登时忘了岳银瓶。
张红拂和小蕊是进来拜神像的,拜过后,小蕊道:“小姐,我们已命人模仿那白狐女的雕像凿出十几座雕像,让人四处拉走啦。想必那太子,不,那赵信现下又在四处追寻那些石像了。”
张红拂道:“嗯,我就是要这姓赵的身败名裂,让举国上下都知道他为了那姓白的女子如丧家之犬一般四处奔波劳累,丢尽他赵氏祖宗的脸面。”
尼烈吓了一跳:“原来是这张俊之女在害赵信啊。听说赵构赐婚于她和赵信,赵信抛弃了她,怪不得她这般恨赵信了。”
小蕊道:“不知是谁想到了用石像这个法子害赵信,看来除我们外还有人想害他。”张红拂道:“不管是谁想害他,只要那姓赵的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就好。”
尼烈差点脱口道:“哈,那便是我啊。原来是你们学着我的法子让人凿的石像害那姓赵的小子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随之一想,又连连暗道:“不同,不同,我是先智,你们是遇到了我让那樊石匠雕的石像后,才学着让人一连气凿了十多尊的,虽然比我凿的多,最多算是后智。不过,我这样做是想借机害赵信的性命,你们这样做更多是想让赵信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同样是死,你们用心之毒则在我之上。”
他见了二女进来的身形步法,已知二女武功不足恃,若出奇不意,扑上后一举点了二女之穴,二女非束手就擒不可。想到这儿,浑身欲火难耐,便想现身擒下二女,忽听得一声音道:“小宝贝,姓赵的小子不要你,我要你如何?”
二女一惊,握紧了手中之剑,回身看去,只见庙门处已站着了一人,扃塌鼻梁,肥头大耳,满脸油光,认得是冷魂四煞中的冷无休。
尼烈一见之下又恼又恨,此人生性好色,不知有多少女子辱于其手。且现下自己有伤在身,武功在其之下,他这一来,二女便和他尼烈没有什么份了。
张红拂和小蕊拔出剑,小蕊挡在了张红拂跟前,道:“休伤我家小姐。”冷无休一步步逼近,满眼邪意。小蕊一剑从旁向他斜攻了过去,冷无休一闪身,伸指在她剑刃上一弹,“嗡”的声响,小蕊持剑不稳,脱手飞了出去。冷无休笑道:“小丫头,你急什么?待会再轮到你。”
小蕊娇叱一声:“淫贼。”赤手空拳而上,被他一掌击在当胸处,身子飞起,头部撞在柱子上,昏死了过去。
张红拂吃了一惊,趁冷无休不备,蓦地挺剑刺向他头颈。冷无休身形一晃,欺到她跟前一把搂住了她腰身,张红拂又气又羞,反手一掌打出,冷无休轻轻一推,张红拂身子荡开,这一掌便落了空。
张红拂自知远非其敌手,急向门口抢去,却一下撞在了他怀里,冷无休满脸涎意的道:“小美人要到哪儿去?”伸手在她脸上摸了一下。张红拂差点昏过去,一剑搠向他当胸,冷无休在她腰间“巨阙穴”和“气海穴”、“神阙穴”上一捏,张红拂手中长剑掉落在地,身子顿即软倒,动弹不得。
冷无休两眼放光,抱她躺下,脱她衣衫,张红拂脑中一片空白,眼角两颗泪珠滚下,欲要咬舌自绝。忽一人冲进来,大叫道:“淫贼,吃我一剑。”一道白光卷向冷无休。冷无休一惊,从张红拂身上翻了出去。
来人是一俊俏少年,约二十岁上下年纪,虽正气凛然,剑尖却有些微微发抖。冷无休一眼瞧出他是初出江湖,并无临敌经验,心下登时宽了大半,只是顾忌他刚才的剑法太过精妙,遂打了一个哈哈,道:“你是谁家的公子?这女子是我纳的妾,因跟了一个小白脸跑了,我一路才追寻到这儿,你来多管什么闲事?”
那少年看看张红拂,又看了看小蕊,二人已被点了穴道,动弹不得,一时不知真假,犹豫不决。
冷无休悄悄欺近他身边,突然双掌向他腰间横拍过去,指缝间赫然夹着两枚银镖。那少年猝不及防,低呼一声往斜刺里窜出,虽避开了这致命之击,左腰间仍是被银镖划中,鲜血淋漓。
那少年大怒,“唰唰”两剑刺了过去。冷无休身法一变,疾如闪电在那少年身边急转起来,出招老到狠辣。斗了二三十招后,那少年被他晃得有些晕头转向,惊慌之下一连刺出数剑均落了空,更加大惊,随后屡屡落入冷无休的套中,连遇了几个险。
张红拂忙叫道:“你快靠到墙根去。”一语点醒梦中人,那少年往墙根抢去。冷无休大怒,纵到了张红拂身边,伸指在张红拂身上一点,张红拂嘴角处即涌出了一道鲜血。
那少年惊叫道:“你休伤这位姑娘。”冷无休哈哈一笑,道:“我为何不伤她?”足尖对准了张红拂头顶。
那少年向张红拂看去,只见张红拂一双满是哀求的眼睛也正向自己瞧来,浑身一颤,不敢与之对视,将目光移了开去。冷无休暗道:“难道这小子也看上了她?”又在张红拂身上补加一指,张红拂受他指力刺穴,气息一窒,又即吐血。
那少年脸色大变,道:“你别伤这位姑娘,有话慢慢好说。”冷无休本是对张红拂出声救他而略加惩戒,岂知发觉这小子似是看上了张红拂,仿佛可以要挟于他,登时暗喜,面上不动声色,道:“你坏了你爷爷的好事,还有什么慢慢好说?”那少年手足无措道:“这个,这个总能有解决之法。”
冷无休喜极暗笑道:“难道这是个未经世面的傻子?”道:“小子,你认得张红拂么?”那少年道:“谁是张红拂?晚辈不认识。”冷无休见他眼神不时向张红拂瞧来,满是关心之意,心想:“难道这傻小子是打出娘胎以来第一次看见女子么?一看见这姓张的女子便为之神魂颠倒了?”又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那少年道:“我,我叫蒲失崖。”冷无休一凛,道:“你爹是谁?”蒲失崖道:“我爹叫蒲燕阳。”
冷无休暗抽了一口凉气,当年他们冷魂四煞受林灵素以“天子之剑”相雇,前往折梅派杀蒲燕阳,正是他演出了苦肉计刺伤了蒲燕阳,想不到蒲燕阳的儿子现就在眼前,岂能留下这个后患?暗暗运气于臂,将手拢于袖内,欲要一击取蒲失崖性命,道:“小子,你是不是看上了这个女子?”
蒲失崖脸一红,道:“我,我……”冷无休大笑道:“小子,你看上了她,是不是?你定是肯为她丢了性命也不要的,是不是?”突然弯下腰,一掌击向张红拂。
蒲失崖惊呼了一声:“不可。”挺剑向冷无休取去。冷无休蓦地抓住张红拂,迎向了他剑尖,蒲失崖急忙收剑,冷无休袖底已一掌发出,“啵”的击在了蒲失崖当胸,冷笑道:“小子,你还……”但只说得四字,身子已往后飞起倒撞出去。
只听豁刺刺声响,冷无休身子撞在了神龛神架上,一时酒水杯盏乱坠,“啪啪”的摔碎一地,蒲失崖则只往后连退了数步。
冷无休倒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又惊又怒,道:“臭小子,你使的是什么武功?”蒲失崖一怔,才醒悟道:“晚辈刚才运的好像是五岳独尊神功。”
冷无休暗骂了一声“龟孙子”,情知敌不过“五岳独尊神功”,抓起地上之物一古脑儿向蒲失崖掷打过去。
蒲失崖舞剑挡架来物,冷无休猛地挥出笼子向他当头罩下,蒲失崖只见头顶白光飞炫,忙向斜刺里一滚,然后抓起一尊泥像向冷无休掷了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冷无休的铁笼子将那泥像的头部绞断,套在了笼子中。蒲失崖见状,疾忙剑光一闪向冷无休头顶递至。
冷无休笼子中套着一个泥头颅,颇是沉重运使不便,被蒲失崖“嗤”的削下了一块头皮,怪叫一声,再不敢恋战,从窗户处跃出,疾逃了去。
蒲失崖欲要追赶,看见张红拂躺在地上,忙回头要将她扶起,张红拂脸红道:“你先解开我穴道。”
蒲失崖道:“是。”挥指点开了她被封之穴,面上已是一片大红,问道:“姑娘没受伤么?”
张红拂将衣衫穿好,垂下头,道:“多谢公子相救。”蒲失崖道:“不知姑娘芳名如何称呼?是何门何派的?”张红拂道:“小女子张红拂,无门无派。”蒲失崖道:“原来那位恶人刚才提到的便是张姑娘。”张红拂点点头。
这时小蕊才醒转过来,从地上爬起,一脸懵然,见了张红拂和一年轻男子在一起,道:“这位公子是谁?”张红拂道:“这位是黄教的蒲公子,是他打跑了冷无休,救了我们。”小蕊忙向蒲失崖行礼道谢。
张红拂看小蕊受了伤,欲进神像后给她疗伤,尼烈无法再躲藏,哈哈一笑走出。
三人吃了一惊。张红拂道:“你是谁?为何躲在这儿?”拔出了剑。尼烈笑道:“在下尼烈,并未有害姑娘之意。”张红拂道:“那你为何躲在庙中窥我们?”尼烈道:“姑娘此言差矣,是在下先到这庙中的,姑娘后来才至,在下无处可去,不躲在后面能到得哪儿去?”
三人觉得他说的也有理,但此人刚才已将张红拂险些遭污之事看在眼里,万不可让他传出去,且此人身在丐帮,丐弟弟子遍布天下,经此人口中一说,不出几天,即传得举世皆知了,张红拂立有杀人灭口之心,向蒲失崖看去,道:“蒲公子,你能否为我留得清白?”
尼烈听出了张红拂之意,哈哈一笑道:“姑娘迭遇危难,在下本来也想在紧急关头出手相救的,后来来了这位蒲少教主,我才没有出手。其实说起来,在下与姑娘还是同道中人。”
张红拂道:“什么同道中人?”
尼烈笑道:“那些石像一开始是我让人凿的,后来被张姑娘遇到了,又请人依样刻凿了去,并依法四处传播。”
张红拂一震,道:“那些石像是你让人刻的?”尼烈道:“正是在下的计策,在下也想害了这个赵信。”小蕊道:“你为什么也想害他?”尼烈笑道:“哈哈,凭什么他身边的都是如花女眷,我尼烈便是孤身寡人?”
张红拂等人登知他是嫉妒之意,心想此人也是好色之徒。小蕊道:“公子是哪里人?令尊或师父如何称呼?”尼烈道:“这些便不足为两位姑娘道了,不过,在下却有一事想告知姑娘。”
张红拂道:“什么事?”尼烈道:“我有赵信的下落。”张红拂浑身一震,道:“他在哪里?”尼烈道:“姑娘若要见他跟我来就是。”心想有这几人尤其是蒲失崖相助,不怕杀不了赵信那瞎子,正要带张红拂等人去找赵信,庙外一声音响起:“银瓶姑娘,这些天让你照顾我,真不知怎生感激你。”另一声音道:“赵大哥,你说这些话干什么?我出来找你,就是想照顾你啊,我现在开心得很呢。你若是要我一辈子照顾,我也愿意照顾你一辈子呢。”说到最后,声音渐低了下去,显是少女之心在表白,说到最后已不好意思。
尼烈不用看,也知道是赵信和岳银瓶到了,顿时妒心大发。张红拂不识岳银瓶,但也听出了赵信的声音,浑身一震:“他,他不是心里只有那个白狐女么?难道又和另一个相好上了?而我张红拂如终难入他法眼,成了亲也要离去?”心里之妒恨也猛地如火焰般腾起。
赵信心下感动,道:“银瓶姑娘,你在家也是这般干活么?”岳银瓶嫣然一笑,道:“是啊,我爹爹不许我们有人侍候,须自已洗衣做饭,两三个仆人做的仅是粗重之活。我们全家穿粗布衣衫,我妈妈有一次穿了件绸衣,我爹看见了,便说:‘皇后与众王妃在北方过得很苦,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就不要穿这么好的衣服了。’我妈便将那件绸衣送人,此后再也不着绫罗了。”
赵信不由心下感动,道:“岳伯伯真是深明事理。”跟着又黯然道:“我父皇母后等人在漠北真的过得很苦么?我去了一趟漠北,却连他们一鳞半爪的消息也没有打听到,更不要奢谈看上他们一面了,我真是个不孝子。”
岳银瓶登知不小心说漏了嘴,忙道:“赵大哥,也许我爹也不知道只是乱说的呢,你不要担心了。我们先找到赵大嫂,然后再想法迎回太上皇等人好了。”赵信“嗯”了一声。
不多时,三人的脚步声已到庙门前。张红拂满腔大怒,叱了一声:“赵信!”当真如惊涛拍岸一般。
赵信身子一震,道:“张姑娘,是你么?”张红拂怒道:“不错,是我,你毁了婚约,毁了我张红拂,今日你还想走么?”赵信道:“昔日之事,是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张红拂道:“我爹为你大宋江山出生入死,你这般轻描淡写的一句对不起,便想揭得过去吗?”
赵信一阵默然不语。蒲失崖则吓了一跳,想不到此人是大宋太子。
张红拂自赵信抗旨拒婚后,忽忽已有三年没有见过赵信,见他双目虽睁开,然光而无神,知他已是瞎了,心下才有一丝快慰,冷笑了几声,道:“真是上天有眼,让你这没有良心的瞎了双眼,哈哈,哈哈。堂堂一国太子,却瞎了眼四处去追一尊尊石像,受尽天下人耻笑,这般滋味不好受罢?”
赵信心下一震,道:“莫非这些石像都是你布下的?”
张红拂道:“我怎画得出你的美貌妻子?又怎会想得到这法儿?不过我身边却有一丹青妙士,对你的美貌妻子念念于心,过目不忘。我后来只是依瓢画葫芦罢了。”赵信问道:“是谁?”张红拂道:“你问他罢。”
岳银瓶瞧见了尼烈,惊道:“尼烈?你也在这儿?”对赵信道:“赵大哥,我忘记告诉你了,其实那些石像均是这尼烈捣的鬼,是他在石匠镇找人刻了赵大嫂的石像,然后让镖局的人押向四处骗你的。”
赵信这才知道中了别人的圈套:“原来这数月来的奔波劳累全都是这尼烈和张红拂一手所为,他们用狐儿来骗我,是为让天下人知道我这个大宋太子是如何丢尽了祖宗的脸面……”想到这儿,心下一阵悲怒,失神呆住。
张红拂大声道:“我便是要让你在天下人面前丢尽脸面,大大折辱你一番,当日你令我和我爹在天下人面前丢尽了脸面,现下一报还一报,也不算为过。”
赵信想到白狐女仍然毫无音讯,黯然道:“嗯,也不算为过,咱们就此别过罢。”
张红拂看赵信又要离开,如当晚他绝情负义离去一般,气恨交加,喝道:“姓赵的,今日我要你纳命来,我要杀了你。”拔出剑欲要将赵信刺数个透明窟隆,但她被冷无休封了穴道,虽然得解内息仍未畅,一口血涌上,险些跌倒。
蒲失崖忙上前扶住道:“张姑娘,你不可心急。”赵信虽瞧不见蒲失崖形貌,也从他的话声中听出了对张红拂的关怀爱慕之意,心想她得成佳偶最好了,遂不停步。
张红拂吸了一口气后,又大叫一声自后扑上,“唰”的一剑直取赵信脑后。赵信挥棍回挡,张红拂的软剑如绳子一般向那长棍卷去。赵信忙用力一抖,张红拂只觉一股大力撞到,软剑险些脱手,心下暗怒:“难道他瞎了眼睛,又只以一棍和我相斗,我仍不是他对手么?”又猱身再进,一把软剑使得如银蛇一般。小蕊见状,也来助张红拂,向赵信下盘卷去。
赵信不想伤二人,不住退闪,然后长棍下击,将二人逼退,叫上岳银瓶,推着付人婴便奔。
张红拂怒道:“你还想逃吗?”又赶上前。这次她攻的是付人婴,心道:“射人先射马,我先杀了你这双眼睛,看你还如何逃法?”招招往付人婴递去。如此一来,赵信不易给付人婴招架抵挡,有些手忙脚乱。
三人忽忽间拆了十余招,尼烈见状,也来助张红拂。他武功博杂,兵刃也时常变换,这时使的是从庙里神像上取下的一对判官笔,招招点向了赵信的腰间。赵信和他拆了数招后,道:“尼烈,我妻子是在漠北和亲时才伤了气脉的,并未到中原来过,你如何知道我狐儿双足气凝不能动了?”
尼烈生怕被揭穿身份,打了个哈哈,笑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又向赵信急攻了两招,岳银瓶见赵信遇险,吓得不时惊呼。
赵信挡拆开来招,心想此人能画我狐儿的画像,定是个丹青妙手,但寻常江湖武人只爱刀枪,极少有好文墨的,当真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此人是谁来。
尼烈攻了两招被赵信挡开后,也向付人婴招呼去,赵信顿时应顾不及。付人婴被削割得发丝和衣衫簌簌而落,吓得面如土色,生怕赵信一个救援不及,自己一条小命不保。但他被赵信点了穴道,丝毫自救不得,突然身子一飘,向半空飞出,吓得他魂飞魄散,心想此番性命休矣,不想稳稳的落在十余丈开外,原来是赵信将他掷了出去。
赵信挥棒横扫,逼开尼烈和张红拂、小蕊三人后,纵身落到了付人婴身旁,推着付人婴又往前急奔。
眼看赵信要走脱,张红拂叫道:“蒲公子,请你替我杀了他。”蒲失崖一怔,他正对张红拂倾慕,当下拔出剑,身子一纵,挡在了赵信跟前,“铮”的一剑向赵信刺去,喝道:“看招。”
赵信回棍格挡,险些被他剑尖所伤,知这蒲失崖武功要在尼烈和张红拂主仆之上,忙对岳银瓶低声道:“银瓶姑娘,你自己先快逃走。”岳银瓶道:“不,赵大哥,我不能丢下你。”
赵信道:“待会他们起心杀你便逃不脱了。”岳银瓶仍是不肯,道:“要死,我和你死在一块。”赵信摇头道:“不可,赵大哥岂能累你伤了性命?你快逃去罢,赵大哥还能支撑得一时三刻,你逃去了,也可找人来帮我,岂不是好?”
岳银瓶听了,这才肯离去,道:“好,赵大哥,你要坚持住,我去找人来救你。”赵信点了点头,道:“嗯,你快去罢。”岳银瓶拔足往前奔去。
张红拂和小蕊赶至,叫道:“不可让那个小妮子逃去了。”蒲失崖欲去追岳银瓶,赵信伸棍递出将他缠住。蒲失崖回剑削去,剑棍相交,赵信的棍头登时断为三截,原来蒲失崖一招间已然削了两剑,端得剑法非同小可。
赵信不敢再以棍相斗,从背上拔出剑器,一招“神女渡河”刺向蒲失崖。蒲失崖竖剑直封,还了一记“封禅掌”。二人斗了两招,各自忌惮,再不出招。不多时,岳银瓶逃去不见。
张红拂见岳银瓶逃了,又气又急,生怕她会找来帮手,更不稍歇,又“唰唰”两剑攻向赵信,余人也各自攻上。赵信以一敌四,又要护住付人婴,如何抵挡得住?以棍搭在付人婴肩上又疾推而去。但他去势虽疾,无奈押着一人仍是难以逃脱,被四人一路追着围斗。
四人各出妙招,时而声东击西,时而急如骤雨,时而悄无声息,凌厉之极,赵信武功虽妙,终究吃了目不能视之亏,只听嗤嗤两声,背后和右腿上立时中了两剑。
他知再也不能护得付人婴,解开了他穴位,道:“你自行逃生去罢。”松开了他肩头之棍。付人婴穴道得解,便想逃走,但他满身是伤,萎顿不堪,已不成人样,哪里有力气杀得出去?尼烈迎面一笔刺向他咽喉,他闪头躲避,仍“噗”的一声被插中了肩头。
张红拂赶上两步,“唰唰”两剑将他两条手臂卸下。付人婴长声惨呼。
赵信知无法上前救得他,发足疾奔,情知一奔走,张红拂等四人必定追赶,到时即可救得他性命了。果然张红拂等人见他逃走,便舍了付人婴追来。
赵信无人带路,只能以一棍点地探索而奔,奔逃一阵后忽足下一滑,跟着有石头簌簌而落,许久不闻回音,大吃了一惊,情知已逃到了悬崖边,欲折向逃时,四人已将他围住。
张红拂恶狠狠的道:“赵信,看你还能逃到哪儿去?”率先攻上,尼烈和蒲失崖分从左右疾攻。赵信目不能视,拆了数招后,想从圈中跃出,蒲失崖已抢先击出一掌,正中赵信后心。
赵信惊呼一声,棍剑乱舞,向山崖下跌坠了去,转眼间不见影踪。
张红拂赶到崖边,向下瞧了一阵,下面云锁雾绕,不知有几十百丈深,知这次赵信终于死定了,心中恨怒方稍消,向蒲失崖道:“多谢公子替我报了大仇。”
蒲失崖初出江湖,从没杀过人,心下也有些惊慌,强自镇定后,道:“没什么,他,他得罪了张姑娘,我自是要为姑娘出手,只是……不知他如何得罪了张姑娘?”
张红拂不愿提赵信毁婚之事,道:“蒲公子不必多问了。”当下和小蕊转身欲行。
蒲失崖略一踌躇,跟了上去,道:“姑娘要到哪儿去?”张红拂摇了摇头:“我也不知到何处去。”一时怅然若失。蒲失崖道:“姑娘若无去处,便跟蒲某上玉皇顶如何?”张红拂道:“上玉皇顶干什么?”随之想起他姓蒲,道:“莫非你是蒲大侠的公子?”
蒲失崖道:“先父正是蒲燕阳。”张红拂道:“你是不是想和我在一起?”蒲失崖顿时一颗心狂跳,面红了几下,有些害羞不敢应答。
张红拂道:“你要和我在一起也不难,只是我要做天下的皇后,你做得到么?”这几个字说得也不大声,蒲失崖却如闻惊雷,吓了一跳,道:“张姑娘不是已杀赵信了吗?如何还要夺他的江山?”张红拂并不回答,和小蕊转身去了。
蒲失崖知说话惹得她不高兴了,怔立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两人寻至,叫道:“少教主怎地到这儿来了?我们去追张南使时,萧东使不是让少教主在三十里外的王庄等我们的么?”却是包世屠和何愁人,何愁人腰间系着一个大酒壶。尼烈一见,急忙悄悄退隐了去。
蒲失崖嗫嚅道:“我也想帮众位叔叔找到张叔叔,是以一个人在这附近寻开了。”
包世屠道:“天下间不知有多少人想找他,他不认识你,你又哪里寻得到他?我们带你来找他,实是冒了极大的危险,若不是想你大了,迟早要登教主之位,这位张叔叔又藏着一本秘笈,我们也不会带你上玉皇顶来。此后你在江湖上行事,万不可多抛头露面,须事事低调。”蒲失崖应道:“是。”
何愁人道:“好啦,这次总算找到少教主了,以后不许胡乱走了,走罢。”蒲失崖道:“我们找到张叔叔了么?”何愁人道:“快要找到了。”
蒲失崖一喜,迈步欲去,忽又停住,道:“我刚才打一个人下崖去了。”包世屠道:“打谁?”
蒲失崖道:“是个瞎了眼睛的,拄着两根棍子,听张姑娘叫他赵信。”包、何二人吓了一跳:“你打死的是大宋的太子。”忙问端倪。
蒲失崖大惊失色,生怕被责备,便搪塞道:“我半路遇上他,他骂我们黄教是反贼,早该诛灭,我气不过,才和他相斗,将他打下断崖了。”只字不敢提爱慕张红拂之事。
包、何二人倒抽了一口凉气,此事毕竟太过重大,朝廷若不理会便罢,若追究起来,黄教实是闯了一个大祸,当下道:“嗯,他这般骂我们,你这样对他也没什么不当,我们先去找到萧、许两位叔叔再商量罢。”领着蒲失崖匆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