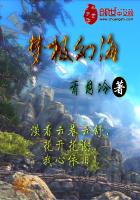马车跑了十日才到京城,宋雍之站在京外眺望着京城,懒洋洋地伸了伸腰,徐徐抽出剑,直指京城。
泰和四十四年,青桑二皇子宋雍和,三皇子宋雍平,五皇子宋雍元谋逆,毒杀泰和帝于养心殿,宋雍和持圣旨继位。
无人想得到他们如此大胆,宋雍和暗中联络依附三人的朝臣,收集其余朝臣的污点,以此为要挟,控制朝堂。
更是私自放出了被关押在天牢的宋雍平和宋雍元,还有顾北望,借亲子之情和苦肉计软化泰和帝,求泰和帝见宋雍元一面。
泰和帝在养心殿见了宋雍元,宋雍元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儿臣不孝,是儿臣一时糊涂,但究根结底是父皇偏心!”
“儿臣自认为不比宋雍之差,凭什么父皇如此偏心!宋雍之能做到的,儿臣也能,凭什么是宋雍之!凭什么!”
他吼得撕心裂肺,委屈得福年都不忍再看,偏了偏头。
“看什么看!本殿再如何,轮不到你一个奴才耻笑!”
泰和帝看着他凄惨的模样,叹了口气:“都下去吧。”
福年刚关上养心殿的门就听里头传来声响,夹着瓷器碎裂的声音,不放心地开了条缝,顿时吓得跌倒在地。
宋雍元一改刚刚的惨样,笑得越来越疯狂,手里握着明黄的圣旨。
泰和帝双目瞪圆,口溢白沫,歪倒在龙椅上,死不瞑目。
“父皇旧疾复发,驾崩了,传位宋雍和,圣旨在此!”
福年还未反应过来,宋雍和就携众臣而来,宋雍平当场指控宋雍元谋逆,宋雍元毫不抵抗认了罪。
“本殿不该谋逆?父皇不公!但圣旨在此,字字乃父皇所写,皇位哈哈哈哈!绝不会是宋雍之的!”
他似乎是疯了,眼里含了泪,“皇位是谁的,都不会是宋雍之的!哈哈哈哈哈宋雍之算什么东西!不是他的!不是他的……”
他忽然抢过一个侍卫的刀,自刎而亡,“不是宋雍之……”
宋雍和静静地看着,直至朝臣们齐齐跪下才有所反应。
“臣等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雍和接过宋雍平递过来的圣旨,示意福年宣旨。
福年如何不知道这是场惊天阴谋,他瘫在地上,魂都飞了,皇上……
宋雍平一剑钉在他身前,“福公公是聪明人,知道该做什么。”
福年嘴唇哆嗦:“太子……厉将军……你们……”
“宋雍之?他能活着进京再说,至于厉止戈,厉家不造反就不错了,父皇做的那些事当真以为没人知道?”
要不是他们不想节外生枝,尽可能堵住悠悠之口,福年杀了也就杀了。
福年脸色灰败,颤巍巍站起来,凄凄地宣了旨,“奴才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雍和一步一步走向龙椅,“众卿平身。”
他松了口气看向边境的方向,残忍地笑了。
宋雍之……还得感谢你啊,要不是你疯了,朝臣们哪会这么听话?
倘若宋雍之没有离京,他不会走到这一步,但宋雍之竟然那么轻易地走了,那就怪不了他了。
即便是父皇也想不到他们会谋逆两次,还是如此迅速。如果宋雍之回来了,不止是皇位,他们的命也没了。
从前他还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宋雍之在边境的作为让他心悸,那绝对是个疯子。
宋雍之杀的那些人是各家的中坚力量,一下子被斩断羽翼,谁知道宋雍之登基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赌。
宋雍淮死前给他送了封信,信上是厉剑霄的死因,再加上此次厉止戈的事,很快就会传遍天下,到时军中还会有人帮宋雍之?
失了臣心,失了军心,没有民心,父皇驾崩,厉止戈命不久矣,谁还能助宋雍之?
……
厉止戈莫名其妙就醒了,浑身不对劲,自嘲地扯了扯唇角,下了马车。
“将军。”
“京中有变?”
“属下不知,太子让属下在此等候。”
厉止戈凛了眼神,气势霎时变了,冷冷地看着余霍。
余霍额上渗出了冷汗,“将军……”
“我一介草民,担当不起。”
“请将军恕罪,三王谋逆,皇上驾崩,二皇子登基,太子……太子率北阳郡守军攻城了,厉家军不参与党争,谁为新帝我等就听命于谁。”
厉止戈很快就理清了思绪,说不清是什么感觉,看了眼京城的方向,上了马车。
如果她现在走了,他估计会疯,后果她承受不起,他无非是仗着这点才敢留她一个人。
厉止戈昏昏沉沉了一日,“余霍,带人攻城。”
“将军!”
“去吧。”
“那将军和老将军的仇就这么算了?恕属下难能从命。”
“他们一而再谋逆,弑父夺位,太子败了,下一个就该清算厉家军了,厉家军会让他们寝食难安。太子念及旧情,不会如何,至于厉家,我和父亲都不悔,能守青桑安宁,有众兄弟相陪,足矣,还是说你们要谋反?”
“将军……我等是将军一手带出来的,断不会让将军蒙羞,只是……”
“你既还认我这个将军,服从军令。”
“属下……遵命!”
厉止戈轻轻咳了声,手心染了血点,厉家拿血肉守下的江山,不会交给小人。
……
北阳郡守军统领庞运为人圆滑,遇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金银也不知道宋雍之是怎么想到他的。
宋雍之拿着圣旨施施然坐在庞运对面,“庞将军。”
“东贤王。”
宋雍之眼睛睁开条缝,“父皇驾崩,皇位只能是本宫的,传位的圣旨本宫想找能找出一摞。”
“那又如何?”
“父皇给庞将军的密令是保护本宫吧。”
“圣旨新帝也有,朝臣臣服,军中无反对之声,百姓亦无怨言,东贤王凭什么要皇位?”
“凭本宫不会弑父。”
“东贤王的杀戮天下尽知,世间都传如若东贤王登基,必是暴君。”
“他们该死。”
“今日臣不助东贤王,东贤王又当如何?”
“本宫此次回京带了两万厉家军,庞将军不助,本宫只好拉下脸皮了。”
“厉家的境遇寒了多少将士的心,何况是厉家军,就算东贤王杀了帮凶,主凶可是皇室。”
“厉家守下的江山不会交到弑父之人手里,厉家忠君,但不愚忠,他们忠的是百姓和自身的信仰。即使父皇做了再多错事,罪不及百姓,本宫深陷囹圄,厉家军必会攻城。”
但他不想走到这一步,他想证明他有能力保护她,厉家军是为了让父皇忌惮,不敢再伤她才悄悄带回京的,不是为了他。
庞运是泰和帝留给宋雍之的人,也就是试探一番,拿出份圣旨,“先帝也曾交给臣一份,臣参见皇上。”
宋雍之搓了搓手,叹了口气,一旦进了京城,就再也回不去了,但是他心甘情愿,他已经迫不及待坐上那个位置了,止戈……
宋雍和策反了掌管五万兵马的远征将军邵衷,大军驻扎在京城后方,明晃晃地等宋雍之进京。
庞运掌管三万兵马,和邵衷一个驻守北境,一个驻守南境,前些日子邵衷率人赶往京城,庞运得到消息便也来了,还是晚了一步。
邵衷到京城的那日,正是泰和帝驾崩那日,庞运比他还晚一日到京城,佯装答应不管此事,等新帝登基大典自会跪拜。
宋雍和威逼利诱,一直防着他。北阳守军刚刚拔营,宋雍和就得到了消息,双方一守一攻,僵持了两日。
第三日两万厉家军从后赶来,直接无视了宋雍之,摧枯拉朽破了城门,攻入皇宫。
宋雍之眼框发热,仰面吸了口气,骑马进了皇宫。
宋雍和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不能置信。
“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懂她。”
“朕是不懂,大哥以色侍人的本事是和谁学的?厉止戈不顾血海深仇,不顾厉家的祖训也要助你。”
宋雍之舔了舔唇,“无师自通。”
“呵,厉止戈今日能为你覆灭朕,他日也能灭了你,两万厉家军可当十万雄师,你放得了心?”宋雍和话是对宋雍之说的,却是看着余霍。
“父皇容不下厉家,朕容不下,青桑历代皇帝有几个容得下的,你就容得下?可惜厉止戈本该留名青史,却因被你迷惑,里子面子荡然无存!”
“与你何干。”宋雍之嗤笑,抬步走向龙椅,一剑横在宋雍和脖子上,“赶着求死?”
“成王败寇。”
“止戈不插手,本宫就杀不进来了?还当本宫是滩烂泥?本宫想要的,从未失手。”
“你赢了,随你怎么说,早知厉止戈有龙阳之好,朕……”
宋雍之慢条斯理地刺了他一剑,血溅在衣上,“倘若只有本宫一人,你不必死,过些年本宫就带她去云游四海。”
“历朝历代为了皇位弑父者比比皆是,父皇虽对本宫千般宠爱,但本宫向来自私,总不会杀了你,将自己困在京城孤独终老。”
“你不该对止戈动心思,本宫的人,父皇也碰不得。”
宋雍之平静地搅碎了宋雍和的伤口,看着他瘫倒在地,蹙眉将他踢了下去。
“本宫欠你一个人情,父皇对厉家太狠,本宫着实不知道怎么和止戈交代,本宫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多亏你,人死了有些事也就散了。”
“作为谢礼,本宫留你全尸。”
父皇对他是真的宠,掏心掏肺,没有底线,把一腔抱负都寄托在他身上,父皇没了,他岂会不伤心。
男儿有泪不轻弹,他自诩没心没肺,终究是因为太顺了,人非顽石,哪能真的没有心。
他不会在外人面前露出脆弱,也不会在她面前因父皇哭泣,他庆幸她昏睡着,让他不必寻个角落,自舔伤口。
哭完了也就完了,他没有资格消沉,是不是从前活得太恣意了,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悲伤之余又有几分窃喜,父皇走了,他不必夹在止戈和父皇中间,他和止戈之间的鸿沟是不是能稍微浅一些?他果然不是个东西。
宋雍之自嘲地笑笑,“其余的交给你们了,只要是活口,一个不能放过,明日游街,斩首示众,抛尸荒野。”
他急匆匆去了城外,远远看着马车,心狂跳不止,亲手触碰到厉止戈,剧烈的心跳才渐渐和缓。
宋雍之缠住厉止戈,眼睛一寸一寸描摹她,怎么都看不够,眸里的悲伤悄悄隐匿,只余细碎的笑。
“祖宗,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