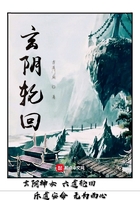一
――这是什么地方?
她醒来的时候,既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
她的眼睛很大,眼仁很亮,亮的就像天上最大的那一颗星。
如星般闪亮的眼睛,此刻正茫然的看着四周,小心翼翼的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可惜她什么都看不到。
无论她的眼睛睁的多大,眼珠鼓的多圆,她所能看见的东西都和闭着眼睛时毫无区别。
她能看到的只有“黑”。
――黑。
――漆黑。
――死一般沉寂的漆黑。
她是不是已经死了?
死人未必就知道自己死了,活人也未必就知道自己还活着。
一阵彻骨的疼痛从左边手臂上传来,痛得她几乎都要叫出声。
――她柔软的右手,此刻正狠狠地掐在她左边的手臂上。
眼泪还在她眼眶中打着转,但她的嘴角却已经忍不住翘了起来。
死人有没有痛觉她并不知晓,但既然能感觉到疼痛,那么她现在就一定还没有死。
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她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有?
――如果她已经死了,那么这里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阎王殿?
――如果她没有死,那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二
夜。
秋夜。
月亮早已沉没,太阳还未升起,只剩下了一片乌蓝的天,笼罩着沉闷的大地。
除了夜游的东西,万物都早已睡着。
这是一间小小的茅屋,黄土夯成的墙体早已开裂,一株株杂草便肆意的从墙缝中钻出,在秋风中不住的摇摆着。
屋顶上的茅草已有多年未曾更换,原本金黄的稻草早已被晒成了灰白色。有些地方的稻草早已不见,只剩下腐烂干裂的屋梁暴露在外面。
万籁俱寂。
傅驴蛋忽的起身,掏出了早已磨到光滑的火石,点燃了遍身油腻的灯盏。
火石划过,灯盏亮起,原本暗沉的茅屋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你就去吗?”
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声音衰老而油腻,好似桌上破旧灯盏里的腥臭灯油。
傅驴蛋点头,看了眼隔壁的房间:“是。”
“这回……”
傅驴蛋一边扣上衣服,一边压低声音道:
“幺婶给相的,没问题。”
“你莫要忘了上回……”
傅驴蛋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颤抖着道:“给我罢。”
那女人伸手到枕头下面,摸索良久,终于摸出了一个陈旧的布包。
布包陈旧,早已洗的看不出什么颜色。
傅驴蛋伸手接过那女人手上的布包,轻轻的拉开了系在上面的细绳,露出了里面的物件。
――铜板,大小不一,年代也不一的铜板。有些已经泛起了青绿的铜锈,其余的也早已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包浆。
傅驴蛋将铜钱细细的数了一遍,数完一遍之后,便又从头开始,再一次重复这同样的步骤。
重复了五次之后,他终于已经数清:五百七十六枚铜钱。三百枚大钱,二百七十六枚小钱。
于是他便将那些铜板再一次装回布包,又把布包仔细的收入怀中。
铜板冰凉,冰凉的铜板正紧紧的贴在他滚烫的胸口上。
他不觉得凉,他只觉得烫。
滚烫。
那铜板好似已经不再是铜板,而是烧红的铜块,亦或是灼热赤红的火把,烫的他浑身都在哆嗦。
五百七十六枚铜钱。其中三百枚大钱,二百七十六枚小钱。这本是他数过无数遍的,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沉重。
里屋里突然一阵窸窣,比虫蚁的声音更大,却比蛇鼠的声音更小。
那是有人起夜的声音。
傅驴蛋长长的呼出口气,平静下颤抖的心情,低声道:
“没事的,你不要起了罢。”
于是那本要起夜的人,便再一次躺回了床铺,躺回了那冰冷潮湿的被窝。
三
春天,江南。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一阵带着桃花芳香的春风,轻柔的吹过大地,温柔得就仿佛情人的呼吸,甜蜜的让人沉醉。
绿水在春风中荡起了一圈圈涟漪,一双燕子刚刚从桃花林中飞出来,落在小桥的朱红栏杆上,呢喃私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一个年轻的女子,正倚靠在朱红的栏杆上,看着这明媚的春景,看着这迷人的风光。
江花红胜火,春水绿如蓝。
一艘画舫正静静的停在这平静醉人的湖面上。
这画舫是从柳荫深处摇出来的,翠绿色的顶朱红的栏杆,雕花的窗子里,湘妃竹帘半卷。
一个身材窈窕的绝代丽人,正坐在窗口,调弄着笼中的雪白鹦鹉。
她一只手托着香腮,手腕圆润,手指纤美,眉宇间仿佛带着种淡淡的幽怨,仿佛正在感怀着春光的易逝,情人的离别。
情人本是在千山外的,但现在却已经奇迹般地出现在了这画舫的船头。
这是一个俊美的男子。
眉目清秀,皮肤白皙,五官俊美的好似精雕细琢的玉像。
他正斜靠在船头的舷板上,一手握着书卷,一手握着折扇。
折扇轻摇。
她已经看见了他,他也已经看见了她。
于是她笑了,他也笑了。
原本停在栏杆上的燕子突然飞起,又呢喃着飞入桃花深处。
太阳忽的便到了西边。
夕阳漫天。
轻雪般的绿柳,半开的红荷,朦胧的远山,倒印在闪动着金光的湖水里。
朱红的画舫,还停泊在粼粼的湖面上,静静的飘荡着。
远处不知是谁在曼声而歌: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春光总是易逝的,深秋很快就会到来。
四
长夜深沉。
深沉的长夜里,一切都已被黑暗所笼罩,只剩下一条灰白的路,漫无目的的通向前方。
傅驴蛋手中提着一盏灯笼,灯笼摇曳,照亮了他的双脚。
他已经走了很久。
这条路不过百尺,但他却好像总也走不到头。
两只黄狗正卧在路旁的枯草里。傅驴蛋走过,它们便睁开眼瞅上一眼,然后继续沉睡。
天更冷了。
但他并不觉得冷,反而觉得燥热。
他好似已不再是年过六旬的垂垂老朽,而是血气方刚的精壮少年。
他突然想起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还是一样的秋,还是一样的夜。就连这条路,也是一样的灰白,一样的枯燥。
那卧在路旁的老狗,仿佛也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
就连他要去往的目的地,也依旧是三十年前的哪一个。
只不过上一次是为了他自己,而这一次则是为了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傅狗剩,此刻正睡在那间残破不堪的茅屋里,焦急的等待着。
秋风更冷。
这偏远荒凉的山村,仿佛千百年来都不曾变过,一代代的人出生,又一代代的在这里老去。
傅驴蛋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的看见一间青黑的瓦房正燃着灯火。
灯火昏黄,好似巫婆阴翳的昏黄眼珠。在引诱着过路的旅客,投入向恶魔的怀抱。
傅驴蛋便好似受到了蛊惑一般,双腿迈得更急,步子也跨的更大。
他是不是也已经受到了蛊惑?
或者,他的目的地是否本就是这灯火阑珊的瓦屋?
傅驴蛋走到屋前,静静的定在那。
定了良久,终于下定决心似的,伸出干瘪扭曲的手掌,轻轻的扣在了那扇紧闭着的房门上。
“咚~”
“咚~”
“咚~”
房门打开,露出了一张干瘪蜡黄的脸。
这是个老女人的脸。
一只尖尖的鹰勾鼻子,随意的安放在这皱巴的脸上,几乎占据了脸的一半。
一个长长的下巴向外翘着。配合着同样尖尖的鹰钩鼻子,就像两个钩子,几乎要贴在一起。
一头油腻又蓬乱的头发,一半白一半黑。半白半黑的头发上,却插着一枝艳红的红花。
就连这老妪的身上穿着的,也是一身同样艳红的褙子,胸口绣着两朵硕大无比的牡丹花。
这老妪两只布满白醫的眼睛,正紧盯着站在门口的傅驴蛋:
“来了?”
傅驴蛋紧张的咽了口唾沫:“是。”
那老妪撇撇干瘪开裂的嘴唇,笑着道:“那么钱呢?”
傅驴蛋道:“钱在这儿。”
那老妪伸出鸡爪般的手,伸到傅驴蛋的面前。
傅驴蛋便掏出怀里的布包,递到那老妪的手中。
布包温热,原本冰凉的铜板,早已被傅驴蛋的身体捂热,原本干燥的布包,此刻也已经沾满了汗水。
老妪颠了颠手中的布包,看着旁边的一间小屋,阴沉沉道:“就在里面。”
说罢便转身向屋内走去。
“幺婶。”
那老妪停住,回头:“我们丐帮办事,你自然不用操心。”
傅驴蛋点头:“是。”
虽然祖居在这荒远闭塞的深山里,但他对于“丐帮”的名声却清楚的很。
幺婶道:“就连你当年,不也是老婆子我帮你找来的?”
傅驴蛋的眼神中露出一种奇异的神色:“是。”
幺婶瞥了傅驴蛋一眼,冷冷的道:“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傅驴蛋突然变得局促,局促的脸都变得通红:“是。”
“明天我会让人送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