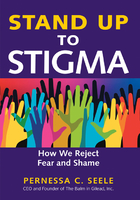第一部
乔治·杜洛华递给管账女人一枚五法郎的硬币[12],接过找回来的钱,走出了饭馆。
他自知长得漂亮,又有前士官的翩翩风度,便故意挺直腰板,以军人的熟练姿势卷了卷胡子,用他那美男子的目光,像撒网一样,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客人。
女客们都抬起头看着他。其中有三个年轻女工,一位年近半百、不修边幅的音乐女教师,身上的衣裙总是歪歪扭扭,帽子上也总积满尘土;还有两位和丈夫在一起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都是这家廉价小饭馆的常客。
来到人行道,杜洛华停下脚步,暗自思量该干什么。那天是六月二十八日。他口袋里只剩下三个法郎零四十生丁。但这些钱得用到月底。就是说,只够吃两顿晚饭,没有午饭,或者两顿午饭,没有晚饭。两种做法,随他选择。他想,一顿午饭只需二十二个苏,而一顿晚饭却要三十个苏。如果只吃午饭,便可以节约一法郎二十生丁。换句话说,还可以吃两顿简简单单的香肠夹面包,外加在大街上喝两杯啤酒。而喝啤酒对他来说,是晚上最大的开销,也是最大的乐趣。想到这里,他迈步向洛雷特圣母院大街走去。
他拿出当年做轻骑兵时的架势,挺起胸膛,两腿微微分开,仿佛刚从马上下来似的,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大踏步前进,粗暴地碰撞别人的肩膀,把挡路的行人推开。头上那顶已经相当残旧的礼帽歪戴着,鞋后跟在路面上敲得橐橐作响,俨然是一个平民打扮的漂亮的退伍军人。他神气十足,挑衅似的傲视着面前的一切:行人,屋宇,甚至整个城市。
他身上那套衣服只值六十法郎,虽然俗了点,但说真的,穿在他身上也颇有些气派。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一头金栗色而稍带红棕的头发,两撇往上翘起的胡须仿佛紧贴在唇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中间是小小的瞳孔。头发天生鬈曲,从头顶分缝儿。这种模样和打扮,十足像通俗小说里的坏蛋。
这是夏天的一个夜晚,一丝风也没有,巴黎像个蒸笼,人人汗流浃背,热得透不过气来。花岗石砌的阴沟口泛出阵阵恶臭。设在地下室里的厨房也从低矮的小窗口向大街喷出一股股泔水和残羹剩饭的馊味。
看门人穿着短袖汗衫,跨坐在藤椅上,在门洞里抽烟斗。行人都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有气无力地走着。
杜洛华走到大街上又踌躇起来,不知道该干什么。他真想到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森林的林荫道上去,那里树木葱茏,可以呼吸一下清凉的空气。但他心里同时也燃烧着一团欲火,总想有个意想不到的艳遇。
什么样的艳遇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三个月来,他日日夜夜都在盼望。有几次,凭着他漂亮的脸蛋和风流的举止,东偷西摸,倒也弄到过个把女人,但他总希望获得更多、更使人陶醉的爱情。
他口袋虽空,但血液沸腾。遇到在街上徘徊的女人就欲火如焚。她们在街角低声问他:“到我家来吗?漂亮小伙子。”他不敢跟她们走,因为没有钱,再说,他还等着另一种东西,另一种不那么庸俗的吻。
可是,他又喜欢妓女溷集的地方,她们常去的舞厅和咖啡馆,她们经常出没的街道。他爱和她们接触、谈话、亲昵地用“你”来互相称呼,爱闻她们身上浓烈的香水味,爱接近她们,因为她们到底是女人,能给人以爱情的女人。他不像那些良家子弟天生就看不起妓女。
他拐了个弯,跟随被热浪冲击着的人流,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路旁宽敞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人,桌子和椅子一直摆到人行道。咖啡馆前面灯火辉煌,映照着如云的顾客。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或小方桌前,桌上的玻璃杯里盛着红、黄、绿、棕等各种颜色的饮料。大肚瓶里闪动着圆柱形的、透明的大冰块,冰镇着晶莹的凉水。
杜洛华放慢了脚步,感到喉咙发干,想喝点什么。
夏夜这种因天热而引起的口渴使他实在难熬。想到清凉饮料喝进嘴里时的舒服感,不禁悠然神往。但如果今晚他喝两杯啤酒,那第二天的晚饭就吹了,而月底挨饿的滋味他是领略过的。
他心想:“我一定要熬到十点,然后到‘美洲人咖啡馆’喝一杯。唉,真他妈的渴!”他眼睛盯着那些坐在桌子旁喝酒的客人,那些能够开怀畅饮的客人,慢慢地走着,装出一副骄傲而快活的样子,经过一个又一个咖啡馆。他只消对喝酒的人看上一眼,便可以根据他们的面貌和衣着,估计出他身上大概带着多少钱。他看着看着,心里突然对这些坐在那里悠闲自得的人产生一股无名的怒火。如果搜他们的口袋,一定能找到黄澄澄的金币,白花花的银币和铜板。每人平均至少有两个路易[13]。咖啡馆里大约有一百人。两个路易乘一百就是四千法郎!想到这里,他一面潇洒地摇晃着身体,一面喃喃地低声咒骂:“一群蠢猪!”如果能在街角的暗处抓住其中一个,天啊,他一定能够像在大规模演习的日子里对待农民的鸡鸭那样,毫不犹豫地扭断他的脖颈。
于是,他又回忆起在非洲当兵的那两年,想起在南方小据点里绑架阿拉伯人,索取赎金的情形。想起有一次偷偷跑出去抢劫,杀死了乌莱德·阿拉纳部落的三个男人,而他和伙伴们却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一些金子,另外还获得了足够乐上六个月的笑料。想到这里,杜洛华唇上掠过了一丝残忍而快活的微笑。
这次暴行的凶手始终没有找到,实际上也根本没怎么找过,因为阿拉伯人似乎已经被公认是士兵们天然的猎物。
但在巴黎,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能挎着战刀,持着手枪,肆无忌惮地从容行劫而不受法律的制裁。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内心还保留着征服地无法无天的士官的全部本能。当然,他非常留恋在沙漠里度过的那两年时光。真遗憾没留在那里!事情就是这样,他本希望回来会更好一些。可现在!……唉,是呀!现在可倒好!
他用舌头舔了舔上颚,发出一声低微的响声,觉得上颚又干又涩。
精疲力竭的人群懒洋洋地在他身旁流过。他暗想:“这群畜生!这些混账东西的背心口袋里肯定都有钱。”他不断用肩膀碰撞周围的行人,嘴里吹着快乐的小调。被他碰撞的几位绅士回过头来不满地嘟囔,几位妇女则骂了一声:“简直是头野兽!”
他走过滑稽剧院,在“美洲人咖啡馆”前面停了下来,心中思忖是否现在就喝那杯啤酒,因为他渴得实在难受。他站在马路上,委决不下,抬头看了看剧院那几个发亮的大钟。刚九点一刻。他很了解自己,只要满满一杯啤酒端到面前,他马上会一口气喝完。喝完又怎么办?十一点以前这段时间怎样打发?
他走了过去,心想:“我一直走到玛德莱娜教堂,然后慢慢踱回来。”
到了歌剧院广场拐角的地方,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和他擦肩而过。这个人的面孔隐约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尾随着这个年轻人,一面回忆,一面暗自嘀咕:“这家伙好面熟,我在哪儿见过呢?”
他想了好久也想不起来,突然眼前一亮,出现了这个人的另一种形象,没现在胖,但比现在年轻,穿着轻骑兵的制服。他不禁失声叫了起来:“嗨,是福雷斯蒂埃!”于是,他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去,在前面那个人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对方转过头来,看了看他,说:
“您找我有事吗?先生?”
杜洛华大笑道:“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得了。”
“第六轻骑兵团的乔治·杜洛华。”
福雷斯蒂埃伸出双手说:“哎呀,老兄,你身体好吗?”
“很好,你呢?”
“我吗?不太好。你知道吗,我的肺现在就跟纸糊的一样,一年要咳上六个月。我回到巴黎的那一年,在布奇瓦尔[14]得了气管炎,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已经有四年了。”
“是吗?可是看起来,你倒挺结实。”
于是,福雷斯蒂埃挽起这位老伙伴的胳臂,对他叙述自己如何得了病,如何去看医生,医生如何诊断,又如何劝他,还说,处在他那样的地位,很难按医生吩咐的去做。医生要他到南方过冬,他能做得到吗?他已经结了婚,现在是新闻记者,地位很不错。
“我在《法兰西生活报》负责政治新闻,为《救国报》采访参议院的消息,有时还给《行星报》编文学专栏。瞧,我混得还可以。”
杜洛华惊讶地看着他。发现他变多了,也成熟了。既有风度,又有气派,穿着打扮完全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举止充满自信,而且大腹便便,可见吃的都是美味佳肴;而以前却是又瘦又小,顽皮好动,爱吵爱闹,一刻钟也安静不下来。想不到在巴黎住了三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身体胖了,神态也严肃了,虽然年纪不到二十七岁,两鬓却已添了几根白发。
福雷斯蒂埃问:“你现在上哪儿去?”
杜洛华回答道:“哪儿也不去,我准备转转就回家了。”
“既然如此,你就陪我去《法兰西生活报》好吗?我要看几份校样。然后,咱们一起去喝杯啤酒。”
“好,我跟你去。”
于是,他们就手挽手走了。以前,他们是同窗好友,后来又同在一个团队当兵,现在久别重逢,自然格外亲密。
“你在巴黎做什么工作?”福雷斯蒂埃问道。
杜洛华耸了耸肩膀,回答道:“老实说,我都快饿死了。服役期一满,我就到这里来,想……碰碰运气,干脆说吧,想到巴黎来享享福;六个月以前,在诺尔省铁路局找了个职员的位置,一年只挣一千五百法郎,多一个子儿也没有。”
福雷斯蒂埃喃喃地说了一句:“哎呀,这油水可不算厚。”
“说得是呀!可是,你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孤身一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人引荐哪。我并非不想有所作为,问题是没有门路。”
他的老朋友像有经验的商人鉴赏一件商品似的,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很有把握地说:
“你知道吗?老弟,这里一切都靠胆量。人只要机灵点,当部长比当科长还容易。不能去求别人,而必须使别人服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在诺尔省铁路局当职员而不另外找一个好点的位置呢?”
杜洛华回答道:“我到处找,但什么工作也没找着。不过,最近倒有点眉目了,有人请我去佩尔兰养马场当骑术教练。在那里,少说也能挣三千法郎。”
福雷斯蒂埃猛地停下脚步:“这可不行,那是傻瓜干的活。就算能挣一万法郎,你也别干,否则,前途就断送了。坐办公室,至少别人看不见你,也没人认识你。如果你有办法,你可以甩掉它,另谋高就。但一当骑术教练就完了。这好比在巴黎一个人人都能去的饭馆里当堂倌。你一给上流社会的人士或者他们的子弟上骑术课,他们便再也不会对你平等相待了。”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接着又问:
“你有高中毕业会考的合格证书吗?”
“没有。我考过两次,都失败了。”
“这没关系,反正中学课程你都学完了。如果谈起西塞罗[15]和提比略[16],你大致知道是什么吧?”
“知道。大致差不多。”
“不错。谁也不会比你知道得更多。不会对付的也就是二十个左右的笨蛋。要别人承认你有学问也不难,根本的问题是别让人当场发现你无知。遇到困难就耍点花招,躲过去,碰到障碍就绕道而行,从字典里找点难题把对方问住。人都是笨得像猪而又蠢得像驴。”
他像很有阅历似的侃侃而谈,脸上带着微笑,看着周围的人群。突然,他咳了起来,只好停下脚步,等咳嗽过去。接着,他伤感地说:
“这气管炎总不好,真烦死人了。现在还正是夏天哩。唉!今年冬天非到芒通[17]疗养不可。豁出去了,身体要紧。”
他们来到波瓦索尼埃大街一扇大玻璃门前面,门后张贴着报纸。有三个行人停下来看报。
门上方有六个用煤气灯排列成的光灿灿的大字:“法兰西生活报”,似乎在招引过往行人。一走进这六个大字射出的光圈里,便仿佛突然置身于正午的太阳光下,纤毫毕现。越过这个光圈,人又立刻回到黑暗中不见了。
福雷斯蒂埃推开门,说了声:“进来吧。”杜洛华走进去,踏上一座豪华而肮脏的楼梯。这座楼梯从外面整条街都可以看得见。他们来到前厅,两个杂役向福雷斯蒂埃躬身施礼。接着,他们走进一个候见室,这里到处都是灰尘,凌乱不堪,墙上挂着绿色的假丝绒,颜色已经发白,上面污迹斑斑,有的地方像被老鼠啃过。
“你坐一会儿,”福雷斯蒂埃说道,“我五分钟就回来。”
客厅有三个门,福雷斯蒂埃说罢从其中一扇门走了进去。
这地方隐隐有一种特殊的、说不出来的怪味,一种编辑室所特有的气味。杜洛华有点胆怯,甚至有点惊讶,站在那儿不敢随便走动。不时有人从一扇门跑进来,但没容他来得及看清楚,便又从另一扇门出去了。
有时候,跑进来的是些小伙子,年纪很轻,样子非常忙碌,由于跑得太快,手上拿的纸都微微颤动。有时是些排字工人,穿着染满油墨的棉布工装,雪白的衬衣领露在外面,长裤是料子的,和上流人穿的一模一样。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一叠叠印好的报纸,或者刚冲洗出来的湿漉漉的底片。偶尔走进来一位矮小的绅士,穿着打扮出奇地讲究,燕尾服绷在身上,裤子很窄,紧贴着两腿,脚登一双尖头皮鞋。那是来送当晚消息,专门采访上层社会的外勤记者。
进来的还有别的人,都板着脸,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头上戴着平边大礼帽,好像这样才能显得与众不同。
福雷斯蒂埃挽着一个男子的胳臂出来了。这个人又高又瘦,年纪约莫三四十岁,黑礼服,白领带,深棕色头发,胡子尖尖地往上翘起,一脸傲慢和洋洋自得的神气。
福雷斯蒂埃对他说:“再见,亲爱的老师。”
对方和他握了握手:“再见,亲爱的。”说完,挟着手杖,一面吹着口哨,一面下楼去了。
杜洛华问道:“他是谁?”
“是雅克·里瓦尔,著名的专栏作家和决斗家。他刚校阅完他那篇文章的清样。加兰、蒙泰尔和他,是当今巴黎三个最有才华的专栏作家。他在这里工作,一星期只写两篇文章,每年却挣三万法郎。”
他们正往外走,迎面遇见一位留着长发,身体肥胖,样子很邋遢的矮个子男人,正气喘吁吁地往楼上走。
福雷斯蒂埃对他深深一躬,然后对杜洛华说:
“这是诗人诺尔贝·德·瓦兰纳,《死去的太阳》就是他写的,也是个名人。给我们写短篇小说,一篇就是三百法郎,每篇最长不到二百行。咱们到‘那不勒斯人咖啡馆’去吧,我渴死了。”
福雷斯蒂埃刚在桌子前面坐下,就大喊:“来两杯啤酒。”接着一口气把自己那杯喝光,而杜洛华则小口小口地仔细品尝,仿佛在喝琼浆玉液。
他的同伴一声不吭,好像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突然问杜洛华:“你为什么不搞搞新闻呢?”
杜洛华吃了一惊,看着他好一会儿才说:“可是……这……我从来没有写过东西。”
“得了,可以试试嘛,可以从头学起。我可以雇你去搜集新闻,去活动,去采访。开始的时候每月二百五十法郎,外加车马费。我跟经理说说,你看怎样?”
“我当然愿意喽。”
“好,先办一件事,明天你到我家来吃晚饭。我只请五六个人,老板瓦尔特先生和夫人,雅克·里瓦尔和诺尔贝·德·瓦兰纳,这两位你刚才已经见过了,还有我太太的一个朋友。就这样说定了?”
杜洛华很犹豫,红着脸,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最后才喃喃地说了一句:
“问题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
福雷斯蒂埃非常惊讶:“你没有礼服?真糟糕!这可是不可缺少的玩意儿啊。你知道吗?在巴黎,宁愿没有床也不能没有礼服。”
说着,他突然翻了翻背心口袋,掏出一把金币,挑了两个路易,放在他的老朋友面前,诚恳而又亲切地说:
“将来你有的时候再还给我好了。拿去租一套你需要的衣服,或者买一套,先付一部分钱,一个月付清。不管怎样,安排一下,明天一定来我家吃晚饭,七点半,封丹路十七号。”
杜洛华不好意思地拿起钱,讷讷地说:
“你太好了,真谢谢你。请相信,我一定不会忘记……”
对方打断了他的话:
“那好。再来一杯怎么样?”接着,他喊道,“伙计,两杯啤酒!”
喝完酒,新闻记者问道:
“去走走好吗?逛一个钟头。”
“好啊。”
于是,两个人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
“咱们干什么好呢?”福雷斯蒂埃问道,“在巴黎,人们说,逛大街的人总有事可干,这话不对。我晚上想蹓跶的时候,总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到布洛涅森林转转吧,如果没个女人陪伴,那毫无意思,可女人总不能手头老带着。有歌舞的咖啡馆只能供我们的药剂师和他的老婆消遣,可不能解我的闷。那干什么好呢?没事可干。这里该有个夜间也开放的夏季公园,像蒙梭公园[18]那样,可以坐在树下,一面欣赏优美的音乐,一面啜饮清凉的饮料。这花园不该是个游乐场,而应该是个逍遥闲逛的地方,门票应该卖得很贵,好吸引漂亮的贵妇人。花园里,人们可以在有电灯照明的铺着细沙的小径上散步,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坐下来欣赏在附近演奏或从远处传来的音乐。这些玩意儿,以前缪扎尔咖啡馆倒有点,但总带着低级乐队的味道,舞曲太多,地方又窄,没有什么幽暗的角落。应该有一个非常美,非常大的公园,那样多好。现在你想到哪儿去?”
杜洛华感到很为难,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才下决心说:
“我没去过‘风流牧女娱乐场’,很想到那里转转。”
他的朋友失声叫了起来:
“‘风流牧女娱乐场’?哈哈,咱们到那儿非被烤熟不可。不过,好吧,那个地方倒是挺有意思。”
于是他们转身向福布尔·蒙马特尔大街走去。
娱乐场正面灯火辉煌,把在这里汇合的四条街道照得通亮。出口处停着一排马车。
福雷斯蒂埃正要走进去,杜洛华拦住他说:
“咱们忘了买票了。”
福雷斯蒂埃很神气地回答:
“和我一起,不用买票。”
说着,他向检票口走去,三个检票员同时向他打招呼,中间的那个把手伸给他。记者问道:
“有好包厢吗?”
“当然有,福雷斯蒂埃先生。”
福雷斯蒂埃接过递给他的票,推开那两扇包着皮软垫的大门。两个人来到了大厅。
大厅里烟气弥漫,远处,舞台和剧场的另一端都仿佛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从观众们的雪茄和香烟中冒出来的缕缕白烟,袅袅上升,直达天花板,在巨大的拱顶下,在吊灯的周围,以及最高一层观众席上面,形成一个烟雾缭绕的天幕。
入口处有一条宽阔的过道,通向环形走廊。走廊里,许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混在穿深色衣服的男人中间,东游西逛。有三个柜台,其中一个前面,有几个女人正在等客。三个柜台后面各坐着一个卖饮料兼做拉皮条生意的女人,她们虽然抹着厚厚的脂粉,但已是人老珠黄了。
她们身后那几面又高又大的镜子,照着她们的后背和来往行人的脸。
福雷斯蒂埃分开人群,迅速地前进,像是个要人,谁都应该尊敬他似的。
他向一个女招待走去,对她说:
“十七号包厢。”
“这边走,先生。”
他们被带进一个小小的包厢。包厢是木板做的,没有顶盖,四周有红色挂毯,四把颜色相同的椅子靠得很近,侧着身子才能勉强走过去。两位朋友坐了下来。只见左右两面,沿着一条直达舞台的长长的弧线,排列着一连串同样的小包厢,里面也坐着人,只露出脑袋和胸部。
舞台上,三个穿紧身运动服的小伙子,一高一矮,另外一个中等身材,正轮流在高杠上表演杂技。
首先是高个子,迈着急促的碎步,微笑着走到台前,用手作了一个飞吻的姿势,向观众致意。
紧身衣下面隐约露出了他手臂和腿部的筋肉。他鼓起胸脯,好掩盖过分凸出的肚子。头顶正中有一条缝,把头发整整齐齐地分成两半,活像个理发店的学徒。只见他很优美地一纵,双手抓住吊杠,身体悬空,做大车轮的动作。忽而又两臂伸直,身体平卧在空中,一动不动,只靠两腕的力量悬挂在单杠上。
然后,他纵身下地。池座的观众纷纷鼓掌。他微笑着再次施礼,接着转身走到布景前面站好。每走一步都充分显露出他腿部肌肉非常发达。
第二个小伙子身材略矮,但更加强壮。他也走到台前,把同样的动作做了一遍。跟着最后一个又表演了一遍,观众的掌声更热烈了。
但杜洛华并不注意台上的表演,而是把头转过去,向身后的回廊频频张望。回廊里站满了男人和妓女。
福雷斯蒂埃对他说:
“你看池座,都是些带着老婆孩子的老百姓,专门来看表演的笨货。坐在包厢里的,是经常逛剧院的人,有几个是艺术家,还有几个二流妓女;而咱们后面,却是巴黎最古怪的大杂烩。他们是些什么人?你好好观察观察吧。什么都有,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但坏蛋占多数。有职员,包括银行、百货商店和政府各部的职员,还有外勤记者,妓院老鸨,穿便服的军官,穿礼服的纨袴子弟,有的刚在小咖啡馆吃过晚饭,有的刚从歌剧院出来,又要去意大利剧场,总之,全是些不三不四、形迹可疑的人。至于那些女的,清一色都是在‘美洲人咖啡馆’吃夜宵的那种人。这些一两个路易就能弄到手的女人整天想找能出五个路易价钱的外国佬,一有空就通知老相好来会面。这些人,大家都见了十年了,除了有时她们到圣拉萨或者卢欣纳卫生站去检查身体以外,一年到头,每天晚上,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她们。”
杜洛华已经心不在焉了,因为那些女人当中,有一个用胳臂靠着他们的包厢,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是个肥胖的棕发女人,皮肤上抹了雪花膏,显得很白,黑黑的眼睛,眼角描得长长的,衬着两条浓黑的假眉,过分丰满的胸部在深色的丝质衣服下高高耸起。涂上口红的双唇像血淋淋的伤口,多少带着点过分热烈的野性,但却能燃起人们心里的欲火。
她向身边经过的一位女友——一个把金发染成红色,身体也很肥胖的女人——点头示意,并且故意用谁都听得见的声音对她说:“瞧,好个漂亮的小伙子。如果他肯出十个路易要我,我绝不会不答应。”
福雷斯蒂埃转过头来,微笑着拍了拍杜洛华的大腿说:“这是对你说的。你真行,亲爱的,祝贺你。”
当过士官的杜洛华满脸通红,机械地用手指摸了摸背心口袋里那两枚金币。
幕已经落了,乐队正奏着华尔兹。
杜洛华说:“咱们到走廊里转转好吗?”
“随你便。”
他们走出包厢,立刻就卷进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被人们挤着,推着,夹着,拥着往前走,眼前所见的只是一堆帽子。那些妓女两人一对地在男人群中任意穿行,从他们的胳臂肘,胸脯和后背间钻过去,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又如水里的鱼儿,在男性的海洋中,轻快地游动。
杜洛华乐不可支,随着人群往前,如醉如痴地吮吸着被烟草和人的气息以及女孩子们的香水味弄得混浊不堪的空气。但福雷斯蒂埃却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住地咳嗽。
“咱们到花园去吧。”他说道。
于是他们向左拐,走进一个像室内花园的庭院。院内有两个粗俗的大喷水池,这里的空气颇为清爽。栽培箱里种着紫杉和崖柏,树阴下有男人和女人在小桌旁喝酒。
“再喝一杯啤酒怎样?”福雷斯蒂埃问道。
“好啊。”
他们坐了下来,看着不断在面前经过的人群。
偶尔一个游荡的女人停下脚步,庸俗地笑了笑问道:
“能请我喝点什么吗,先生?”
福雷斯蒂埃回答道:“请你喝杯喷水池里的水。”那女人嘟囔了一句:“去你的,真没有教养!”接着就走开了。
这时候,刚才靠在他们包厢后面的那个胖胖的棕发女人又出现了,她挽着那个肥胖的金发女人的胳臂,傲慢地走着,真是天生的一对,搭配得好极了。
棕发女人微笑地看着杜洛华,两人四目相视,似乎许多心里话都通过目光传递了。她拉过一把椅子,大模大样地在杜洛华面前坐下,同时叫她的女友也坐下,然后说了声:“伙计,两杯石榴露!”
福雷斯蒂埃吃了一惊,说道:
“你可真不客气。”
“是你朋友招我来的,”女人回答道,“他真是个漂亮小伙子。我想他一定会使我神魂颠倒!”
杜洛华有点胆怯,不知道说什么好。一面憨笑,一面卷着往上翘起的胡子。侍者端上果子露,两个女人一口气喝光了,然后,一起站了起来。棕发女人微微点了点头,用扇子在杜洛华手臂上轻轻打了一下,对他说:“谢谢,我的小猫。要你开口可真不容易。”
说完,两个女人扭着屁股走了。
福雷斯蒂埃大笑起来:
“我说,老兄,你知道吗?你对女人可真有吸引力。应该珍惜这一点。日后可能会有好处的。”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然后,像做梦似地自言自语道:
“要想以最快的速度飞黄腾达,还是得通过她们呵。”
看见杜洛华一味微笑而不回答,便问道:
“你还不走吗?我得回去了,我不想待下去了。”
杜洛华喃喃地说:“嗯,我再待一会儿,时间还早。”
福雷斯蒂埃站起来说:
“那好,再见了。明天见,别忘了,封丹路十七号,七点半。”
“一言为定,明天见,谢谢你。”
他们握握手,新闻记者走了。
他一走,杜洛华顿时感到自由了,他高兴地又摸了摸口袋里那两枚金币,然后站起来,走进人群,用眼睛不断地搜索。
他很快就看见了那两个金发和棕发的女人,她们仍然像乞丐一样,在拥挤的男人堆里骄傲地转来转去。
他径直向她们走去。到了近前,他又胆怯起来。那个棕发的问他:
“你舌头找回来了?”
“当然。”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他们三个人停下来,剧院走廊的人流被堵住了,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漩涡。
棕发女人突然问道:
“你愿意上我家去吗?”
“愿意,可是我口袋里只有一个路易。”
棕发女人无所谓地笑了笑:
“这没关系。”
说着她挽起杜洛华的胳臂,表示杜洛华已经属于她了。
他们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杜洛华心里想,拿剩下的那二十个法郎租一套夜礼服以备明天之用是毫无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