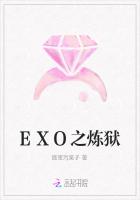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长时间的耳鬓厮磨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是让懵懵懂懂中的白若冰对邱云峰的感情从依靠慢慢过渡到依赖,继而碰撞出超出兄妹感情的小火花。
当然这个过程是渐变的。虽然之间少不了邱云峰有意无意地制造能够促进两人感情的机会。但白若冰却胜在并非完全无心,在半混半醒之间被邱云峰“润物细无声”的爱点滴浸润着,完全失去了对陌生男人的抵抗力。
邱云峰的爱心照顾让白若冰的病情在日复一日地恢复中快速好转:她自言自语的时候少了,逐渐平息了阵发性的烦躁不安,脸上也难得的浮现出了少女原本该有的红润,甚至浅浅的笑容里也重现了往日的羞赧……
但一切的表像,仍掩盖不了她还是一个病人的事实,是一个心智和情商都异于常人的精神病人。日常中更多的时间,她惯于一个人面无表情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我而执着,大半天一动不动,不说一句话,让人猜不到她在想什么;或者,她会选择性地记住或者忘记一些事情,有时候会毫无征兆地主动提问一些以前的旧事,有时候又对邱云峰有意识提起的一些往事完全没有印象,即使那些事刚刚发生在昨天,她也完全不记得,就像那些事根本没有在她面前发生过一样。
邱云峰在和医院专家的不断交流中,不停地改进和变化应对的治疗方法。在白若冰清醒的时候,他会给她提供一些她原来喜欢的医学书籍,放在床头或枕边,方便她随手拈来读书;“章一含”和“刘向晖”这几个字是她不能轻易触碰的隐形炸弹,邱云峰极力回避在她面前提起这两个名字,以免引起白若冰突如其来的崩溃。只是偶尔白若冰会不经意地自言自语:“咦,刘向晖不是挺爱我的吗?他怎么不来看我了呢?”
每当这个时候,邱云峰心里除了满满的苦涩,还有一丝的期望和高兴:能记起刘向晖这个人,说明白若冰的脑子里还有正常的脑细胞在活动,那她恢复正常人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就不会白费。等到刘向晖回来的时候,自己也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把她完璧归赵。
邱云峰以一个男人所能做到的的极致体贴,细致入微地照顾着白若冰,期望着她能早一天恢复正常,融入火热的生活中;同时又矛盾地在心里希望她被自己照顾的时间能久一点,再久一点……这样他就可以面对面地见证她的成长,虽然辛苦,却有说不出的幸福。这种幸福在很久以前他就幻想过,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状态。他现在甚至已经很“自私”地喜欢上了这种“一男一女两人三餐”的生活。
邱云峰其实过得很辛苦。
这种辛苦不是体现在工作忙顿和日常的劳心费力上,而在他和白若冰相处时那种矛盾又无法自拔的爱情折磨上。邱云峰一边告诫自己不要当真,一边又无法遏制面对白若冰时爱的冲动;他很享受白若冰拿他当哥哥时的那份开心,他也随着她放肆地大笑大闹;他更欣喜于白若冰看他时眼里若隐若现的柔情,虽然不确定这柔情里有多少爱的水分,但他依然珍惜这一刻,甚至多少次都差点抑制不住想放纵地亲吻她的冲动……
晚上躺在床上,望着黑漆漆的屋顶,他的脑子里却想象着白若冰红润的唇是如何的柔软……但理智最终还是让他把自己困顿在良心和道义的谴责中,独自默默承受那份蚀骨的折磨。
自责之余,邱云峰在心里暗自庆幸白若冰的心智不清,病中的她可能不会真正读懂自己的心思,否则他不知道第二天该以何面目面对白若冰清纯的眼睛。他无数次在黑暗中狠狠拧自己的大腿,或是扇自己耳光,努力驱散这些拉低自己素养的胡思乱想,然后在在苦恼不已中辗转反侧,有时候睁眼到天亮……
邱云峰尽心尽力地伺候着生病的白若冰,把大姑娘的她当成小孩子来宠,凡事都力争做到尽善尽美,唯恐委屈了她去。但细心的他百密还是一疏,他疏忽了病中的白若冰混沌之余还有偶尔清醒的时候。
白若冰清醒的那一刻,她会不动声色地望着眼前这个男人忙碌的身影,在脑子里一幕幕地过滤过去能够记起的点滴往事:她记起了自己的恋人好像叫刘向晖,记起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去了很远的地方,但她却想不起来他的模样了,只是模糊地还能记起他说话的声音,低沉的带有磁性的男中音,很好听;她很忧伤恋人为什么不来看她,她明明觉得他们很相爱的;她还能模糊地记得自己好像还有个朋友章一含,不过她自杀了,而且还留下了一本日记……由于邱云峰的再三解释和开导,白若冰已经慢慢习惯了想起这些,不再像当初一样,听到“日记”两个字就像被火烧了手指头,全身痉挛颤抖,无法自制。现在的她会学着邱云峰的样子,摊开双手自己劝自己道:日记是别人的,好像和我没啥关系咾!
每逢听到白若冰说这些话,正忙东忙西的邱云峰都会回过头来,鼓励地奖赏给她一个微笑。这时的白若冰就会以少女的敏感红了脸,逃避似的不再面对邱云峰眼里的小星星。她害怕那些小星星,怕它们终有一天会跑到自己的心里来。她记得自己是名花有主的姑娘,怎么可以背叛曾经的爱情呢?
可是让她困惑的是,眼前这个让她叫哥哥的人,既不是她心心念着的恋人,也不是她从小熟悉的哥哥,他好像只是一个外人;但不知为什么,此刻的他,却又甘愿担负着恋人和哥哥的双重角色,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她,关爱她。
过度的思考让白若冰头疼,病魔让她重新变回傻白甜的混沌病人状态:白若冰开始坦然接受邱大哥的贴身照顾,衣食住行,甚至穿衣戴袜,都让他手把手的服侍。而且自己还模仿着小时候的记忆,会撒娇地把头枕到哥哥的胳膊上,然后冲着他傻笑,唱儿歌……
每当这时候,都是这对“非常兄妹”最高兴的时候,他们各自心中都有自己不同定义的幸福,但却又心照不宣地陶醉在这种幸福里……他对她的感情很明确,就是男女之爱,虽然他深埋在心里;而她对他的感情,则就比较难定义了,说兄妹之情吧,她眼里又有控制不住的少女怀春;说男女之情吧,处于犯病期的她简单的思维里又只把他当哥哥……
但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并不影响他们互相依赖,彼此需要,抱团取暖,并慢慢结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似乎谁缺了谁,生活就不再是完整的一坨。
他们别样的感情终于被房东看出了端倪。
“邱干部,这姑娘不是你亲妹妹吧?你们说话的口音不一样,模样不一样,就连姓氏都不一样,哪里让人相信是亲兄妹呢?”
房东是个四十开外的陕北婆姨,姓郭,胖墩墩的,快人快语,又是个难得的热心肠。平时邱云峰有要急的工作回不来,就把白若冰拜托给她照顾。所以时日久了,她和这对“兄妹”混得很熟。
“郭大嫂见笑了,忘了告诉你,这不是我亲妹妹,是干妹妹。”邱云峰笑着解释。
“干妹妹也不像!”郭大嫂一口就否定了,“兄弟,嫂子是过来人,你们是不是兄妹关系,是骗不了我的眼睛的。这么给你说吧,就凭你瞅这个姑娘的眼神,我就敢断定你没拿她当妹妹待。这是汉子看婆姨的眼神呀!你是把这姑娘当成婆姨给疼了吧?”
邱云峰像是被人当众揭开了谎言,有些不知所措。他惊慌地回头看一眼白若冰,发现她正眼望着别处发呆,根本没注意这边两个人的谈话,这才稳下神来,摇手示意郭大嫂别说了。
郭大嫂却“噗嗤”一笑:“兄弟,你还是年龄小,经事少,不懂我们女人的心思。你是真把白姑娘当傻子了,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其实你错了,白姑娘有病不假,但她犯糊涂的时候并不多。你对她好,她心里是知道的,你没觉出来她那小眼神整天跟着你转悠呀!”
邱云峰一愣:是吗?这一点他还真没注意过!
郭大嫂顿一顿,继续说:“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们郎才女貌的,除了白姑娘有点病,我看不出你们哪里有不般配!你就把白姑娘娶了得了,那样照顾起来更方便!也免得不知道的人说闲话。”
这话让邱云峰害怕了:“郭大嫂,你快停下嘴吧,莫乱说了。我承认我有对白姑娘胡思乱想的地方,可看人家白姑娘是清清白白的人,她有心上人的,是我战友,还是个战斗英雄,打完仗就会回来的。你没注意白姑娘清醒的时候常常念叨他吗?他们的感情很好!我只是在替我战友照顾她。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那会把我置于不仁不义的地步了!”
郭大嫂听到此处,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叹息道:“哦,这样啊,那是不能胡说了。不过,你们两个都是好人,能这么相处一场也算是缘份。只是,委屈了你了大兄弟!以后但凡你有不方便的地方,就让嫂子来!”
……
邱云峰第六次带着白若冰来医院检查。赵九章和精神科主任会诊后,给了邱云峰一个大大的点赞:“云峰,你真是好样的!若冰在你的照顾下,恢复得非常好。相信再有个一年半载的,她基本上就能痊愈了。恭喜若冰!谢谢你!”
邱云峰深深呼了一口气:“若冰真能痊愈,那可太好了!我也就能结束这‘苦难’的旅程了。再这样过下去,我都要崩溃了!我太难了!”
赵九章同情地拍拍邱云峰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小伙子,不论人品还是修养,你都是这个!等若冰的未婚夫回来,我们一定给你请上一大功!”
“请功倒不用,不过,刘向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或许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解放了!”邱云峰向往地自言自语道,像是说给别人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是啊,刘向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