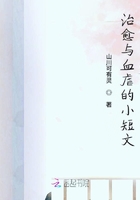接下来的几日,习韵言都很少说话,只是偶尔会出院子里走一走,更多的时候是在屋子里盯着窗户发呆。
“小姐,你这几日不言不语,阿娇有些担心,心底有什么事莫不要藏起来,和阿娇说说,阿娇虽不能替你解决,可总是会让小姐舒服些的。”阿娇忧心忡忡的说道。
习韵言转过头看着她,笑了笑,“莫要担心。我只是,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
松戟从前殿走来,看到两人肩并肩站在院子里,挥了挥手,阿娇就先退下了。
“天气虽转暖,可这里比不上西秦的气候,还是凉的。”说罢,习韵言感觉肩头多了一件貂皮大衣,上面还透着松戟的气息。
“谢谢。”她轻声说,“在北凉,冬都这样长的么?”
松戟看着她的侧脸,那双眼睛直直的看着远处的山峰,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他抓不到看不清。松戟点点头,“是啊,北凉的冬长。雪也下的紧,看这天气,多半还有一场。”
松戟的话刚落,习韵言就感觉什么冰冰凉凉的东西落在自己的脸颊上,她伸出手,一片雪花落于她的掌心,慢慢的,消融,“你看,雪来了。”她的眼睛清澈的像雪融的水,松戟看着她,可这样的清澈让他有些害怕,是那种什么都没有了的,更贴切的说,是空洞。
他拢了拢她身上的大衣,“这雪,你可喜欢?”
“我喜欢。”她脱口而出,转过身子看着他,“你知道吗?在秦禾很少下雪,若是下,也是小小的。每次遇到这小雪,我便和姐姐兴奋许久,跑到大院里,偏偏要堆一个极小的雪人,娘亲和爹爹笑我们,站在屋檐下,云崖在一旁喊着不要着凉...”她的脸上慢慢浮现出笑意,连带着松戟都看到她眼中那遥远的从前,她不知是雪落在眼角还是真的落泪,摸了摸,一片湿润,看着松戟呆呆的笑了。
这样的她,着实让他心疼。他伸手将她揽在怀中,她没有拒绝,轻轻的依靠在他的胸膛,感受着他的心跳,听到他在自己头顶说,“苏言,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你要信我,只要我在,你就不是一个人。”
苏言...松戟,若你知道,我连名字都是骗你的,你还会不会待我这样好。
处死习家一家后,秦雍的身体也江河日下,这几日更是无法上朝。黄岩稳坐宰相的职位,心高气傲的很,秦雍不在时,居高临下,仿佛他才是正主一般。
秦雍心里明白自己撑不了多久,黄岩这个人狡诈,他下旨让秦穆代理国政,压制黄岩。
“太子。”秦雍看着儿子,说道,“朕希望你能守好西秦的江山。”他有些虚弱,额头上不停的冒着虚汗,“朕知道,习家的,习家的事,包括太子妃自尽,给你很大打击。可朕还是想告诉你,这就是,帝王。片刻的心慈手软,也决不允许。”
秦穆跪在秦雍床前,点点头,“儿臣明白。”
“朕,自小对你...”秦雍猛地咳嗽几声,“过于严苛,心里明白。记得为父的话,不狠得下心来,难,难成大,大事。”秦雍的呼吸声越来越微弱,最后竟死死的握住秦穆的手,“记得,记得...”便永远闭了眼睛。
“父皇说的话,儿臣谨记在心。”
翌日,秦穆登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看着跪在朝廷之上的文武百官,眼神清冽,缓缓张口,“平身!”
“从即日起,全力捉拿李家余孽李慕钦,还有...”他握了握拳头,想起习韵婉那日死在自己怀中,“安阳郡主习韵言。”
此话一出,整个秦禾流言四溅,大街小巷均盛传,安阳郡主还活着?不是和亲出了岔子死了么?
赞木今日上朝,宣布这件事,“西秦已下通缉令,安阳郡主尚存于人世,若有发现,立即上报。”
“不知日后这西秦待我北凉又是怎么一番局势。”
“我们莫要自慌阵脚。秦雍素来待我们不冷不热,其早已把我们视为眼中钉,看这松戟上台不知会有何改变,我们北凉当做好万全应对之策。”
习韵言待在松戟的府上,两耳不闻窗外事。
“新上任的皇帝竟还在追究先帝的事情。”她听到几个人说。
新上任的皇帝?难道秦雍已死?现在,是秦穆?她的双眼突然的睁大,跑到正殿,松戟刚刚回来,见她,问道,“怎么了?”
她吞了吞口水,平复了呼吸,“二爷,我问你,秦雍死了?”
松戟没有料到她会这么问,点点头,“是,秦穆于前几日登基。”他看她面色不对,以为又是身体不适,忙走过来,“身子不舒服?”
她摇摇头,垂下双手,秦雍怎么死的这么快。李家的,习家的,那昏君死的也太过容易了些。“没事,我只是,道听途说想确认一下罢了,我先回去了。”
她刚走了没几步,就听到松戟对白柳说,“今日父王上朝,竟说前来和亲的安阳郡主还活着,下令搜寻。这公主也真是命大,若活着怎不前来?”
她身子一僵,心头狠狠一颤,握了握拳头。
秦穆怎么知道她还活着?娘亲绝不会透露,若不是姐姐在将死之时觉得对秦穆有些愧疚?可秦穆怎么会大张旗鼓抓她回去?秦穆...是要开始恨自己了么?
她坐在房间中,松戟推门进来,看着发愣的她,开口,“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哦,没什么。”她回过神,“只是想到以前的事情,这天下也变得太快了些。我在秦禾那段日子,秦雍,”她冷笑一声,“还活的好好的。”
她语气不善,松戟听得出来,“秦雍向来名声不好,这次换了个主,也不知是什么情况了。”
“是。”习韵言低下头,摸摸桌上的茶杯,“听说,安阳郡主还活着?”
他皱了皱眉头,不知为何今日她如何在意这朝中之事,“是。你今日为何如此在意?”
她突然咧开嘴一笑,“他们打算定这安阳郡主什么罪名?”
“她本是习家的人,再加上如今逃婚抗旨不遵,怎么着也是死罪。”他说,没有看她的表情。
“哦。”习韵言淡淡的回应,抬起头,看着正在喝茶的松戟,松戟,若我告诉你,我就是那安阳郡主,你又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