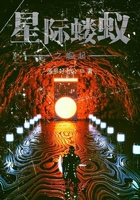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三年了,这十三年里我也常常想起要写一些纪念他的文字。可每次总怕触及内心的疼痛,所以一直没有动笔。
我的父亲年轻时应该是一位俊朗潇洒的男子,他到六十五岁去世之前,身材依然挺拔,依然清瘦,从来就没有长过“将军肚”。父亲爱好古典诗词,有很深的古文功底,谈吐儒雅,待人真诚。假如他这辈子能够成为大学的老师,一定会获得无数学子的崇拜和爱戴。然而,父亲只是一位农民,一位爱读书的农民。
农闲的时候,或者农忙的间隙,他便找来一本书,沉浸到书的意境中去。父亲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家有个书箱,大约只有一米高,半米宽,里面码放着几摞线装书,有《诗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还有几本线装书的名字我忘了。书是很旧的,仿佛在这书箱里已经放了几百年,打开书箱就弥漫出一股霉味。所以,天气晴好的时候,父亲会把书箱里的书拿出来晒一下,晒书的景观是我家独有的,别的人家不会有,当然,这是我小的时候。后来,村庄里读书的人家也多了起来。
父亲小时候上过两年还是三年私塾就辍学了,因为家境贫寒,他又是长子,要支撑门户。他天性喜欢读书,虽然辍学了,书却没有离手,日积月累,所以古文功底深厚,成了方圆几里都知道的“文化人”,村庄里有什么“文化”上的事就由父亲操办或跟父亲商量。有“文化人”的旨趣,却只能做个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也有不甘心的时候,他思考自己的命运,慨叹小时候家境不好,自己也没能赶上好的时光,不然读书考学出去,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应当不在话下。
“去年已被秋风误,无端岂肯误春风。”在他的身上,传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书香一卷。”他渴望我们姐弟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文化人”,实现他未曾实现的梦。
我家老屋的堂屋上,曾贴着一首老掉牙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反悔读书迟”。这是父亲委托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表叔写的。表叔写这幅字的时候,大约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前后,我也在场。当时表叔还笑着说,有人把他写的繁体字“鸡”误读成“鹅”,读成“三更灯火五更鹅”了。表叔在乡村小学当老师,他和我父亲志趣相投,常常是父亲去他家,或他来我家。两人在一起聊古文,聊古代的文人趣事,常常能聊一宿不睡觉。现在,表叔也去世了。在那个世界,父亲一定不会寂寞了吧。
我很小的时候,便深深地受父亲的影响,捧起那些线装书,父亲也教我学识繁体字,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学《唐诗三百首》。
这些平平仄仄的东西,曾经那样地深入我的骨髓,曾经那样地纠缠过我,一个在唐诗宋词里浸泡得久了的男儿就变得容易凭花落泪、多情敏感起来。
可是,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却觉得父亲教给我的那些东西是那么不合时宜,那么迂腐。那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想起父亲所谓的“文化人”,我满脑子里摇摇晃晃的全是孔乙己的形象。那时候,初出茅庐的我,正试图从书卷中走出来,要扎到商海里,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儒商。
但父亲教给我的,毕竟已经深深地刻进我的骨子里了,“文化人”“生意人”,我实在难以两全。
那年的深秋,我在大连,感觉挣扎得累了。因为一种机缘,走进了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园。静悄悄的夜,我一个人听叶落沙沙的声响,看幢幢教学楼窗口明亮的灯光,老家堂屋上那首老掉牙的劝学诗突然闪现在脑海中。那一刻,我想,我还年轻,我也一样有金色的年华呀,我也要读大连理工的硕士、博士,去圆父亲“文化人”的梦。
那时,父亲还健在。我感觉自己身上突然涌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求,感到父亲的目光正穿越千山万水向我投来,投到我的脊背上,使我再无理由退缩。
细细想起来,这种与生俱来的渴求是源于父亲和他的书的。父亲去世后,我又一次打开了他的书箱,以为那几摞线装书是善本藏书。我重新翻检,发现都是极普通的书,印刷的时间也不长,多是民国时期的,现在大概都收在老家后来盖的新居里。而表叔题写的那首劝学诗,随着老屋的拆除,没有保存下来,去了它最终要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