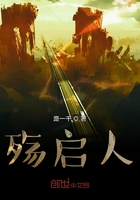我难道还不能高兴一下吗?这个世界上,令我发自内心高兴的事太少了。
我的父亲告诉我不要在朋友圈发一些消极沮丧的东西。我翻到早上编辑的“每天靠一颗药续命,不是铁打的。”于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等待和他重修于好吗?不需要。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再怎么修复也无法复原。
以我现在的身体,支撑不了多久。我知道。
比起谈恋爱,天天出去吃喝玩乐,放纵自己的欲望明明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两边都太随心所欲了。
而且大部分时候,找你不到。手机调了静音。
我接起来的时候,你那边挂断了。
一件事想的越久就越不想做。
我会反复看曾经写过的文字,一遍又一遍。如果玻璃知道会碎的话,应该不愿意被认真擦拭。
我的高中时候居住的地方,是一座雨城。我在日记本上写到结尾地方,“雨依旧在下。
不打伞的少年,用塑料纸板遮在头顶上方,匆匆跑过。
雨,一定凉。
窗外的松针树依旧挺拔,槐树落下嫩黄的茸花,踩上去,消失了声音…”
也写过这样的句子:
“这个学校我丢了好多东西,还有我的两把伞。”桔子这样跟我抱怨着,我忽略她皱起的眉头,听起来更多像撒娇。像夏天慵懒的暖风忽然忘记。以及快要消失的忽远忽近的雨。”
一个地方,同一个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
去上海参加新概念比赛的时候,我们住在黄浦江的一个有些旧有些古朴的房子,打开窗子可以看到车水马龙的上海。只有对于有钱人来说,上海才是欲望之都,繁华圣地,才是十里洋场。
我们不属于这里。
视线停留在很远的地方,面对前途未卜的未来,谁都没有了思绪。只能像面对江岸大喊大叫“梦想已经走失”或者“被梦想抛弃”的人一样,第二天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好好生活。我们是平凡的人,虽不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依然有机会在世界规则的浸泡下生活的很好。
我把手靠在背后,一蹦一跳地上楼梯。“你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送给我们番茄的姐姐叫住我说。不止看起来,这次是从心里。
贞凉的小友琴药人狠话不多,不说话很有些大家闺秀的气派。说出口的话也都是金玉良言。这样的妙人,却不知道便宜了哪家公子。“红颜知己止于脸。”“甜言蜜语不用来骗人,留着作甚?”
民国时期的人美。时光缓慢,明白去昨。贵族少女少妇,是很有些华服的。胭脂水粉,漂亮衣裳,精致的物什。留给女儿作几件首饰,也是极有面子的。
琴药在姑母的晚宴上见到阮姐姐,这位姐姐神秘的很,很有些来头。急于说上几句话,琴药就破天荒地冒昧开口了“因为听别人说起过你多次,今天可算见到真人了。”“怕是说我愚笨不堪吧。”不免宽容的笑了。“决然没有的事,你身份高贵有又无架子,平日里广施恩义。我是一直盼着与你做朋友呢。”本想着是几句客套话,没想到这丫头心眼这样实在。阮姐姐立刻慷慨大方道“我太高兴。”同样是率真自然的人,当别人说想认识自己时,不是俗气敷衍的“我倍感荣幸”,而是真性情的表达真情实意的高兴还不止,我太高兴。如此甚好。琴药这丫头对于长得美的人儿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力,她太专注痴迷,遥想到“哪一天我也这样风情万种的样子?”沮丧的小脸上看不出刚刚还是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贞凉调侃她“哪天啊?这样就放弃啦,你还没开始呢。”难得琴药没有回嘴,她也许是气馁于自己的不可塑性。姑母说“你可别来招惹她,等下又折腾个没完没了了。”索性随她去吧。
琴药这几日,愈发沉静了。读王佳芝被易先生枪毙那一段。使眼神让他“快走”,飞也似的就逃了。险些就成功了啊。王佳芝也许是不想都按计划走和那些不顾她死活的朋友摆布,在生死攸关时刻任性一把。被枪决时,琴药一直在等故事的反转,“再等等,也许有转机,易先生总要救他心爱女人的。”“喂喂琴小姐你快从小说世界跳脱出来,书电影你不都看过了吗,都死了。这就是,大、结、局。”
原来电影也不得圆满。爱比起命来,还是命贵重些。向来如此。读者的等待,也不过为了再失望一次罢了。
易先生亲口承认,爱过王佳芝,“如果政局不那么动乱的话,我必定来救你。”她合上书,沉沉安睡。因为她清楚,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开学第一天傍晚就在图书馆对面的小花坛蹲下哭了。我这样一无是处的人。
这次回来全是陌生的面孔,但依然年轻活力。经历过的东西就没那么渴望。
看到很多只“牛油果”跑来跑去,和那个爱看书的宿管阿姨彻谈很久,俘获对方的心,和阿姨最贴近的一次。中午第一餐就治愈了我的胃,挑剔又脆弱的胃。离开池州,就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牛肉拉面。偶然碰到凯瑞兄,兑了两杯果茶。诚信度加一分。中午和阿远像平常上学一样睡了午觉。安心的睡到闹钟响起。和一些朋友渐行渐远,只能在背后着急又抱歉地喊着“保重身体,有缘再见”。看见一个男生背着另一个喝醉的男生艰难地上坡。
大学是一个你会怀念,但没事也不会刻意回去的地方
这次走了不知道啥时候还会回去
可能一天,可能好多年
我把热情付诸在哪里,一点点变得薄情。
从起点回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