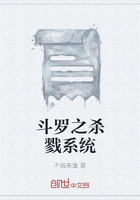在天桥上对望,越看越陌生。
苏唯夏年轻时爱做的事情,靠着栏杆尽力往后仰,做出下坠的姿势,难以呼吸才突然回过身来。
记得在H城的运河边上,有的是一种木质的敦厚的桥。每块木板两端都放着点燃的自动蜡烛,灯火与木质地板独有的光泽交相辉映,大有一种十里红妆布置的意思。踏上去的那刻,苏唯夏心想“若是和喜欢的人一起走该有多好,那便像是走完一生了吧。”她央求林白焰一起走一遍。林白焰没有拒绝,“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路过这里,回来再走吧。”苏唯夏说“好”。可是回来的时候的确刻意回来这里,但灯火全部熄灭,只有路灯稀稀疏疏透着微弱光芒。
那种有着白色风车的阿尔卑斯小房子,苏唯夏非要吵着说是城堡。她整副身躯环着膝盖坐在圆形的栅栏围成的椅子上,背面坐的是柒与白,他此刻在思考着什么,眼神游离在很远的地方。他突然转过身来告诉我说,“如果春天来的话,这些全是樱花树,花瓣飞的到处都是,那才美呢。”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安定人心的力量。“白焰,白焰”“嗯?”,“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大概是类似于归于最初的某个祝愿,我也解释不清”,他们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一直聊天到暮色四合。远远的还是有人点,在拍婚纱照。
约好的时间,却因为假日赶上了密密麻麻的热闹,她们在人群中找彼此。以前就常常玩这样的游戏,并且乐不此疲。这次不同,是真的走散了。苏唯夏是出了名的路痴,曾在家的附近看幼稚园的孩子背书入迷,而找不到家在哪里,据她所说“那声音犹如天籁,我忘记别的也正常”。在五颜六色的喷泉(灯光原因)升起来又落下的时候,才终于看见,他朝她使劲地挥手“唯夏…”,靠的太近,她的棉麻裙摆沾了水珠,好在是夏天。她来不及微笑,朝他跑过去。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她朝他的方向跑过去。
横亘在滚滚江水上方的石桥,风仿佛从深深的地底呼呼吹来,不是美好的色彩,是深沉的淡灰色,有些诡异离奇,她扯着他的衣角说“你坐下来,休息一会我们再走,我太累了。”于是他们两个就坐在那里,吹了很久很久的风。江风怎么可以如此冰凉如水?不太像夏天,倒像是刻意营造的虚假梦境。
“他有关注你的生活吗,一点一滴?”我怕苏唯夏难过,可我还是脱口而出地问了,问了就后悔。只能当做弥补地祈祷不要说没。过了一会她说“不知道”。听不出开心还是难过,但我被她成功骗过,以为已经若无其事。
苏唯夏站在那里听入迷,一个精致眉眼的女孩子唱《慢慢喜欢你》到声音梗咽,甚至超越莫文蔚的声线。她没有学其他人拍照,晚上回去把那首歌单曲循环听了11遍。
你说的那些,均不在意。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每次没事就往四楼瞎跑,蹲点看美丽的金黄色落日,阳台上,天空离得特别近,大团大团软软的云朵,用老板拿来冷藏茶叶的冷藏室冰酸奶喝,每天给老板的盆栽浇水。我时常再想如果当时我是在那个像勤杂工一样被使唤来使唤去的小饭馆做了两个月,那我还是你们认识的那个渣渣吗?早就变麻木,粗俗了吧,甚至耳濡目染下就飙脏话?可怕。所以“傻人有傻福”,操心是操心不来的。
社会会因为你是学生就对你另眼相看,但不会因为你是学生就一直有耐心。这是我暑假悟出的道理。暑假我做了性格修正,是‘爱憎分明’。别人对我好,好那我十倍奉还,别人犯我,好,以牙还牙。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老好人。。老板女儿大学毕业一年,一点也不世故,经常给我许多好吃的,给我四块一个的糯米糍,给我买火炬,我又多了一个好朋友,这是我的小幸运。妈妈说她怕我第一份工作找的那么好,以后吃不了苦。我觉得不然,“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
刚放假那段时间我热心减肥,的确两个星期就华丽丽减到了59.3kg,这似乎就是我的极限了。然后就开始懒了,不动就算了,还每次不上班的那天天天逛吃逛吃,现在我家那边的两条小吃街我都无感了。罪孽深重啊。我弟弟形容我“上班瘦一斤,不上班胖三斤。”所以我就还是长胖了。不仅没戒掉我最爱的奥利奥奶茶还添了新宠――香草味双皮奶,味道太正宗了,椰果红豆都给的多,超满足。于是乎我的暑假就在吃的狂欢和又长胖了之间喜忧参半了。
那就这样吧,我的一整个快活、自由、颓靡的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