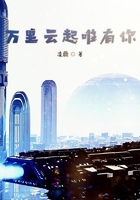1
糟糕的事情才开始,父亲在联中替我做了所有的事情之后,就回去了,我好像被父亲遗弃了一样,有些无所适从,我不会买菜,不会买馒头,不会像别人那样快乐。我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上的班是重点班。
在我父亲的学生中,上这个重点班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叫霍非同的男孩,另一个是个女孩,她叫皮玉,说实话,我学习不如他们俩个,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这个班的,我并没有考上,只是通过父亲的努力,我顶了姐的名字,才得以挤了进来。这是我不光荣的历史的开始,从此以后弄虚作假,对我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真的我站在这里忏悔时,便觉得再无遮掩的必要,尽管我依然很虚伪,这就是实话。
也许是因为我的欲望高于了我的能力,我想弄到更好一点儿的东西,结果是我只能把自己的脸抽肿,来冒充胖子,其实这种做假的感觉并不好受。现在我明白,如果做假时,你有不适感,那说明还不够成熟,这比如你初吸海洛因时的恶心,如果你能坚持下去,不适将很快消失,你会熟练起来,在你熟练地具体操作过程中,你将获取快感——做假的老手,在他习惯这种快感时,他会忘掉假和真的区别。惬意地做“胖子”。
开始我总觉得顶了人家的名有点儿丢人,但好在别人都不知道这事,我很快忘了这些不快。日子过得很快。霍非同是我父亲的学生,他的姑家在镇上,我和霍非同一起住进了她姑家。一个月了,我还不知道怎么生活,霍非同每天都回他姑家吃饭,我就跟着去,我好像还不明白,我不能老吃人家的,我手里捏着父亲走时替我支取的饭票,当时我不明白父亲说的话,他说:“这一张二两的票做一斤用。”我似懂非懂地接了饭票,也没好意思问别人到底怎么花。一天放学,我看见学生从食堂里吃着包子出来,便叫霍非同停会儿,我去买两个包子来,当我掂起脚,竭力把一个半斤的票递上去说要两个包子时,我听见那个年轻的师傅心不在焉地说再拿一张,我心里一沉,涌起一股子失落,忽然觉得很无助。
我从没有离开过家,买饭对我来说太陌生了,经这师傅那句话,我再也提不起买包子的欲望。头一低,走吧。走了,没有叫住我。到门口对霍非同说:没了,走吧。我和霍非同又去他姑家吃饭,现在想起来,真笨行可怜。
我开始想家。想哭,不过我没哭出来。我们班的女生们却哭得惊天动地。听说女生寝室里一片哭声。如丧考妣蛙声连天。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报之的是不屑和轻蔑,女孩子,真熊包!那时心里不知怎么树立起了大男子主义。
不过我已经很有理想了。12岁已不是个小年纪。我的理想便是做一个了不起的领袖,理想归理想,现实让我极不乐观,我整天紧锁着眉头,心事重重,终于有一个家伙,惹怒了我,那小子怨我抢了他的位置,这是哪有的事啊?我比他低,当然要坐在他前边。然而他却事事与我作对,说话刻薄。他妈的,我心里实在看不惯他那大舌头的恶心样,又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我心里一急,呼地窜了上去,一把卡住他的脖子,死命地把他摁在桌子上,他被憋得满脸赤红。我们很快被分开了,这次反击成功了,他真贱,从此对我客气起来。
我开始看武侠小说,课也不听,我讨厌老师在堂上南腔北调的说教,学习成绩一落再落,最后,再不学习了,捱日子,过一天少三晌,我讨厌庆祖一中,讨厌这儿的一切,我向往县一中,向往县城,于是每当我心烦时我都会跑到庆祖一中东边大路边的河桥上,望着北流的河水痴痴地想:这些水是流向城里的呀!它将从县三中旁边流过,我羡慕这些河水。
最后还是失落地回来,忧伤布满归来的路。
2
为什么非要去城里呢?为什么什么都要最好的?为什么赶着鸭子上架?为什么让鸭子学会仰望天空,学会幻想?
我是个丑小鸭,父亲要我变成一只白天鹅,父亲耳提面命,朝夕灌输,终于让丑小鸭有了一颗天鹅的心。
那就是理想!人就要有理想!理想就是对美好充满无休止的向往!我从一点点就开始向往城里,向往城里的生活!
我第一次去城里的县三中,可能是五岁,十几年了,我记忆犹新。那时候叔叔在县三中教书,姐姐就跟叔叔在城里读书,我哭着闹着跟老爸看姐姐,看叔叔,于是我就来了一趟城里。
我第一次见到了楼,宽广的路,从进城一直到三中,一路上我目不暇接,在激动莫名之际我被父亲带到一座两层的建筑前,告诉我说这是叔的住处,那时以为这一切都太神奇,而且还有地下室,我那时不知道,这是座老教堂。
当我和父亲一齐踩着长满青苔的石台阶时,那种感觉平生仅有,我惊诧的是,这种感觉在一个五岁的男孩的心中竟留下如此强烈的印像,我对这儿的一切有一股无比的向往,姐姐就在这上“育红班”。父亲隔一个月便来看姐一次——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般美好,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她不稀罕这里的一切。
父亲敲开了门,叔叔一开门就瞧见了我,一把把我抱进屋里,兴奋地在他的木质地板上转圈。那种感觉就是现在进了五星级宾馆也找不回来了。中午我、叔和姐还有父亲去三中食堂吃饭,人很多,地方很大,我们俩个并排坐在凳子上,看着叔叔排队买菜,这是我记忆里最最难忘的一顿饭,是蒜泥黄瓜,我是贪婪地吃净了所有的菜汤,多年来,母亲还以此取笑我。
没办法,一个小乡巴佬第一次看到了城市就晕了头,渴望过上这样的幸福生活。从此三中、城市成了我的一个噩梦。
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有过理想,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有真情的一面,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纯真领地,可我悲哀地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道德理想。在贫瘠的社会里,道德永远都只能被大众形式地追求。人们看来,道德这种精神崇高只是善良吧,是一种美好愿望。
精神在无知中荒芜,我在这种贫瘠中慢慢地长大。父亲灌输了他的全部知识和观点,都是窗外的细雨。我的内心感受不到水分的滋润,我小时候干涸的心田里一片茫然。
心里面再干燥,大脑再迟钝,我还是不停地长大,这是自然规律。我没脸没皮地又坚持长了五六年,个子超过了姐姐,有一天姐姐说:“小暮,人家都说你笨,我觉得不对,你看看你,还是照样长个子,不挺有本事的吗?”
我张口结舌,再笨也不致于笨到不会长个子的程度吧?
他们都不知道,怀揣异想的孩子,注定要忍受煎熬。
3
现在以追忆的方式思考这段时光,更觉得难过,有一种从思想上压来的沉重,那种艰涩每当我稍有暇思的时候,便悄然袭来。我骚动的内心里仅有那种喷薄欲出的激情便随之袭来,化成了一股销心蚀骨的惆怅,我从此背负了这种情绪,挥之不去,纠之不清。
惆怅对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已算是一种奢侈的情绪,我肯定我是一个不平常的男人,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要做一个英雄。然而事实却一再抽我耳光,我被挫败搞得一团糟。每当我坐在书桌前,便心乱如麻。我确信我并没有像父亲骂我那样“笨得像猪”,因为我有这样几件事证明,除了偷钱时的“智慧”外,就连藏钱的事也不算,我仍有这样的事可以证明,我是聪明的,因为那时我也不过七岁。
父亲一大爱好就是给我们三个买画册、小人书啦,那次父亲又从外边带回来一本关于聪明的猴子的连环画。故事是说猴子要通过一座唯一的桥去河对岸,但是桥上有一个狐狸看守,不过这个家伙总是爱睡觉,可每次又只睡四分钟,不妙的事是通过这河必须要用五分钟,这个矛盾让小猴一时为难,要是让狐狸发觉了他必须掉头返回。怎么办?怎么办?父亲说完这故事时,夸张地盯着面前的同样为难的我们姐弟三个,结果还是我最快反应了过来,说了句使父亲脸上开花的话:小猴可以走着走着,等狐狸快醒时掉头往回走。……哇噻,太棒了!对,父亲当时喜笑颜开。我甚为得意,虽然姐和弟都说我预先看了小人书,可我知道我没有看。
可为什么现在学习这么难呢?特别是数学,父亲的回答是我笨,长了个猪脑筋,把所有的聪明的“伟绩”都忘却,我甚至以为自己的确笨了。人再笨,目标可是没有改变过,考最好的学校。
弄来弄去,把自己搞得跟只大头猪一样,非要一头撞死到南墙上,不见棺材不落泪,反正还没成年,一个劲地读小学,考初中,考初中,结果年年考三中,还是没考上。
笨蛋!是个人都骂我,那些日子真不好过。
你知道狗熊是怎么死的吗?笨死的。你,就是那只狗熊。
我无言以对。
我在庆祖镇联中呆了半年,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乱糟糟,父亲非常失望,马上考初中的时间又要到了,就让我退学回家了。
4
回家的那些日子压抑得厉害,其实父亲只是想看着我,让我自己学习。折腾来折腾去,两个月之后我的一切好奇心和浮躁给消耗得差不多了,总算能安心学习了,正准备考试呢,不料我姑姑跟人家吵架,把事闹大了,动了兵器。
农村打架是家常便饭,打伤也是常事,打死则不多见。双方都是老实人,只是两个老爷们儿的媳妇委实太多嘴了,说东道西的,挑出了事,结果对方弟兄几个一起来姑家兴师问罪。这场事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怨姑家在他们村里是冤大头,门儿里人少,姑父的二弟又有精神病,单门独户,当然是任人打骂了。有事没事地铲你几棵豆秧,拔你几株树苗,骂你几句,说几句风凉话,你要不想找事,就睁只眼闭只眼,掩住耳朵充耳不闻,不然他们便会兴师问罪而来,任你招架,定然是招架不住的。
对方势不罢休,人家老三是村支书,很有面子,兴师问罪那是自然,理也不要多说,双方手里都动用兵器,大打出手。
事情打了个激灵,就结束了,姑父落荒而逃,对方的老大不治而亡,姑和几个孩子也跑回了我们家。接着姑家被抄,人家四处搜拿姑父。姑和孩子都藏了起来。姑全家都逃跑得没影了,结果妻离子散;对方死了一个人,结果家破人亡。这并不是祸害的结果,不幸才开了个头。
如果只是讲讲故事而已,听者和说者可能都会觉得挺传奇的,可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另一种味,事不关已,总是小事。痛不关已,总是不痛。
我还没感觉,姑家的一帮人如今都已经没有家了,他们以后的苦和辛酸,自是无法为外人道,这可能就是生活。
代价是如此的惨烈。现在姑父正坐着牢,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他做为一个农民愚昧的结果。也只有这么说了,表面的豫北农村是如此的宁静,可我知道这是沼泽的表像,沼泽里同样也没有风浪,那里有水,也有水草。夕阳照到这里,如果用审美的眼光看这里,还有一股子粗犷生动的野味之美。可是当你靠近了,你就能闻到那一股子原始腥臭。鱼儿在这生活得很艰难,鳄鱼和蜥蜴在这里却很快乐。
“出人头地”也许就是那些鱼儿的梦想,想快长出翅膀,飞离吧。
也许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农村里并不是全都这样恐怖,然而村里的人们对这些事,并不以为很特别,只是适合做一个不错的谈资。他们在街头巷尾,发表一番看法后,以为再也没什么就置之脑后了。他们的一致观点是姑父和死者都可惜了。二者都是老实人。言外之意也都明显,多嘴的媳妇是祸水。都是邻居,怎么好当面说,只能背后说吧。然后都各收起脸前的碗筷,拍拍腚上的土回家去了。不过他们很快又会回来,就三三两两装了半口袋花生,边吃边打开三十年前就备好的话匣子,夹着半截上次没抽完的老汗烟的李四干起了“口仗”——这里的战争没有硝烟——东家长西家短。月高了,鸡睡了,狗都不叫了,他们都各自散了,各自作着各自的春秋大梦,不用说明天和今天定然无甚不同。
我躺在床上却怎么样也睡不着。
我已经学会了失眠,现在父亲的情绪处于极低潮期,我的学习不好,姐姐的成绩也已经有所下降,够他苦恼的了。叔叔很少回家,因为叔的第二个女儿已出生了,母亲主要照顾猫儿,还要给我们做饭。这都是小活,另外地里还有8亩地,母亲是主力,奶奶和母亲的关系因为要照顾猫儿,所以好了点儿,母亲去地里时,猫儿暂时由奶奶照管。她很乖,已会说话,母亲为此常高兴得合不拢嘴。猫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就连一向乖戾的父亲,也从不对猫儿白眼……可是我的出路在哪呢?我躺在床上,瞪着眼。
月光透过窗户,悄悄地探过来,猫着步子,满地都是散乱的月光……里屋传来母亲的咳嗽声,父亲在翻身和呓语,猫儿的小哭,母亲的呵哄……钟表的无体止的嘀哒,嘀哒……我的出路在哪里?我到底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太敏感,无疑放大了自己的困厄,我的内心开始沉淀伤感了,主要是我的梦,我的这个不是在睡觉时做的梦。
其实,我再努力地探问内心和尘世,都只能更困惑,不可能得到答案。在我的圈子里,没有人能回答我,人活着都是为了什么?可是我已明显地感到我需要这个答案了。这是个歧路吗?我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但却毫无所得?然而无可问处,只反问迷惑求解,这是我的悲哀。
理想是什么?是威风八面?是流水行云?是有钱有势?还是其他什么?
这半年转眼而逝,我又落榜,心痛之余,卷土重来。学习上再不敢儿戏,疯了般地硬是每天钻到夜里两三点。前几天,父母不以为然,接连下去,父母又心疼起我来,每深夜中醒来见我的灯亮着,就说:“别熬了,明儿做不一样吗?”
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动人的话,特别是母亲那带着浓重睡意的鼻音,极轻柔地传了过来,让我体味很久,微弱的灯光,托着我,还有伴着我的奇大无比地影子,漫漫的夜啊。
我或者答应一声,或者不吭,很快他们又传来了鼾声,半年下来已很难知道我的数学成绩达到了什么高度,现在做数学卷,超不过半个小时,且都是全对,这像个神话。我创造的神话,以后,我成了他们几个“后进”的老师。
5
生活乱七八糟,说不了就出什么事情了。侮辱生活和被生活侮辱,侮辱别人同时也被别人侮辱着,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仇恨和愤怒。
隔壁的邻居是我的本家四叔,结婚六七年了,早从老院子里搬了过来,那几年我们家没拉围墙,院子敞着,现在呢,父亲想盖四间房子,这样四叔的路便会被截断不能从我们院子里过了,把自己的庄基由人横行穿过是村俗的大忌,父亲和爷爷当然坚持不让步,定要拉起围墙。四叔家坚持非走不可,矛盾激化,直至大打出手,我自然加入了战争,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热闹了。
四叔不是父亲的对手,结果招来了四叔的父亲即我的本家爷爷——顺爷,还有二叔,他们把父亲一顿饱揍,我们败下阵来。我当时泣血痛苦。这是村子里的人当我的面打我的父亲。我只是无力地暴跳,这不过是他们继续打我的理由——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狗屁一般的小孩子,没有战斗力,四叔一个飞脚过来,我应脚仰面倒地,肚子苦痛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