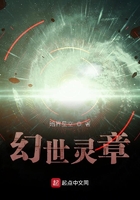1
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系主任张老师会打电话过来,我被电话铃惊醒后,闭着眼抓起了话筒:“喂,找哪位?”
“你好,我找小暮同学。”一个我不熟悉的男中音,我说,我就是。
对方说:“小暮你好,我是张华老师。”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哎呀,张老师,您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我刚知道你要退学的消息,我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觉得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你的事情,想跟你谈谈,你真的认为没有必要读完安阳师院了吗?”
“我,我四门不及格,老师,我……”我结结巴巴,不知道说什么,突然蹦出了一句,“我想通过自学考试那本科证,然后考研究生。”
张老师笑了笑说:“我知道你的情况,你没考好,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整天泡在图书馆,不上课,也不学自己的专业。你是不是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如果不喜欢可以申请调剂一下啊。关于四门不及格的事情,我已经找有关老师商量过了,你的情况还算是特殊,只要是下次考试不要再挂红灯就行了,老师都是为你们着想的,如果是这样退学了,考研的资格就很难具备。要三思而后行,我不多说了,你仔细考虑一下,我等你消息。不过,要快。明天怎么样,我等你的电话。”
我说谢谢老师,谢谢。张老师挂了电话。我想在他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捣蛋的孩子,而现在,在外边疯够了,得回去了。
好像一场戏就这样被我唱到了头,回到安阳师院,我直接去找张老师。
晚上,我们一起去外边吃饭,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等老师一再说回去吧的时候,我想我大约是喝醉了。我们打车回去,我还记得抢着付打的的钱。到了学校,我只觉得晕头转向,街上冷冷清清,也许天已经很晚了,我胃里难受就跑到路边的厕所里吐,然后就失去了知觉……也许过了很久,我走了出去,竟然发现老师还站在路口,微笑着说:“你喝醉了,以后要少喝酒。”
唉,这样喝醉也是很好的,就算是出了丑,就算是幼稚得可笑。
后来,听另外一个老师说起我退学的事情,我才知道,事情并不如张老师说得那么容易,开始,他无意间听到了一个学生主动退学,而这个学生并不是一个混蛋学生的时候,他决定了解清楚,这时候学校已经批准了我的退学申请。张老师开始做学生处的工作,抽回了文件。看这张老师的笑脸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为什么这样呢?
那天我在老师的建议下请学生处和我们系书记和辅导员吃饭,饭场上大家都要敬张老师喝酒,想让他喝醉。我站起来说:“各位老师,感谢你们对一个不合格学生的关照,特别是张老师,说句心里话,除了我父亲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我很感激,就让我替张老师喝酒吧。”
他们大笑,我喝酒。事情就这样被了结,我继续我的学生生活。
2
我常常想起金非说我的那句话:你的生活是假的。
痛心疾首的年代过去了,我早已不再是一个可以撒娇的孩子,是应该用更加平常的眼光来看看自己,这么多年,这么多事情,难道真的是我完全能把握得了的?
一年多来,我忽然想家了,趁了一个星期天我回了趟家,父亲比一年前老多了,看见我似乎愣了一下,随后笑了起来,大声对母亲说:“他娘,你看看,小暮回来了,小暮回来了。”
母亲说:“看看你,喊啥,我看见了。”
难道我离开他们真的那么久了吗?父亲骑着摩托车去割肉去了,说要和我喝两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老爷子越喝越兴奋,一瓶白酒完了,父亲说话开始含糊,他说:“小暮,你是个混蛋,你知道不知道,老子想你了,臭小子,我想打你,就像小时候一样,按在地上,用腰带打你屁股,啪啪啪。”
“哈哈,老头儿你醉了。”我抹了一下嘴上的油渍,回过头对母亲笑了笑,“娘,他喝醉了。”母亲不说话。
我回过头来对着父亲笑,我说:“爹,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暴力。为什么又想打我?”
“为什么?你不知道?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就你,唉,你除了给老子添乱,你还给我干啥好事情了?”父亲的脸红的跟关老爷一样,“你上学花钱,就跟抽我血一样,哈哈,你还不好好念书,搁小时候不打你打谁呀!现在不同了,你成了大学生了,会问为什么了……儿子,我知道你是好样的,打不垮,毛病多,优点也多,跟你姐姐和弟弟比,你是最野的,吃的苦也最多,我对你还是放心的。”
他真的喝高了,说话开始打转转,前后矛盾。我不跟老爸争论了,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听你的。”
父亲终于躺到了床上,呼噜呼噜睡着了,我坐在灯光下,跟母亲说话。
母亲说:“你看看今天喝了不少,以后在外边可不能喝这么多。听见没有,喝多了自己难受,有啥好处?”
我说:“知道了,知道了。”
“你知道个屁呀!扭头就忘。你听过大人一句?”
……啊,唠唠叨叨的娘,呼噜呼噜的爹,家,远方的弟弟和姐姐,还有什么呢?在家呆了两天,小院子里父亲的几个小学生哇哇乱叫,鸡飞狗跳的。那全是童年的记忆,就这样,五六岁的小孩挤在廉子外边偷窥我,父亲喝斥他们,他们嗡一声跑散了,在院子里跑,喊叫,没过多久又有一群孩子挤在门口,脏兮兮的笑脸,乱蓬蓬的头发,唧唧咕咕的声音:“老师,老师。”他们不停的在外边骚扰父亲,说谁谁打架了,说谁谁没完成作业。
他们,我,小孩子,时间,流水,我开始想起我小时候,我不应该只记得那些痛苦的往事,那时不对的,那并不是我真实的童年,那个喜欢教训我的父亲也不是父亲的真实面目,我以前的生活或多或少都被我主观地改动了。
你只有不断地回头看,不断地暖化心灵,不断地成长,你才能发现,你是多么的幸福,而那些悲痛无非是为了让你珍惜这些幸福而已。
3
回学校了,父亲给了我1000块钱,说这是为我准备的钱,昨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这钱是父亲给后街的邻居借的,我拿住了这薄薄的十张粉红的纸,叹了口气,我对父亲说:“我要是有力量拒绝这些钱就好了!嘿嘿。”
父亲裂了咧嘴说:“钱算啥,有多少花多少,没了想办法,拿着吧。”看着轻松的父亲,我没觉得难过,这句话说得有点像劫富济贫的飞贼。
上路了,这是我最轻松的一次离家,路上我一个劲的想,我这是怎么了,本来该难受的,为什么不难过了呢?回到学校天已经黑了,我总觉得自己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二天我买了一个信纸本,准备给父亲写封信,就去了图书馆,坐在一个角落里,打开思绪,童年的影子浮现在眼前,我写道:
我是怀着惭愧之心来写这些文字的。当我又要以愁怨之心来抱怨自己的尴尬处境时,我对这心情熟悉得近乎腻了,我丧失了什么呢?我想仔细地清查一下我的内心之地是如何的陈旧,这可能对我认清自己有所帮助。
没想到,一开头文字如决堤的水涌了出来,总算是找到能干的事情了。断断续续地我开始又一次接近自己的童年,那个惶恐的孩子慢慢地长大了。
每一次写完一段文字,我总是兴匆匆的找个人来听我读,然后读一段问一句:“怎么样?我写得好不好?”
开始他们说好。有时候好几个人听,在宿舍里,我大声地朗诵自己的“小说”,然后挨个问:“怎么样?”
有时候他们犹豫,想半天才说:“好。”十几天过去,听我读小说的越来越少,我有点担心,肯定是我的小说出了问题。
有一天,我找不到人听我读,就呼高欢的BB机:“速回宿舍,有急事,小暮。”
高欢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我说:“你来听听我的小说好不好,我给你读一段,我刚写的。”
“我靠,这就是你的急事啊!你干吗非要折磨我!”他暴跳如雷,他说他正在跟一个美女约会:“这下完了。你就不能消停一点吗,我亲爱的小暮哥哥。”
既然来了,就听一段吧,我给他念,他像一只蛤蟆一样趴在床上听我的小说。我读着读着他突然打断我:“猛男,难道你真的觉得你的小说能出版吗?”
我想了想,说能。他嘿嘿的笑了,也不知道啥意思。以后给他打传呼,他就不再听了,他说:“我从小就听‘狼来了’这个故事,你难道没听说过。”
后来我用小毛的名字传他速回,结果他又上了一次当,然后我又对其他同学如法炮制几次,小毛,小a,小b,小c,小d都上过当,嘿嘿,小说终于读完了,他们一致评价:“不错。”
把心里话说出来,真不错!我心头的大石头被放了下来。
我伸了伸腰,好像终于煎熬到了头,望着面前着厚厚的一摞手稿,我知道,我已经给自己了一个交代。
我要把这本书出版了!
4
一学年很快到了头,2002年依然还有些陌生,但是已经过了一半,进了六月份了。大一结束啦,看着桌子上的一沓子书稿,我说:“我要到北京找出版社。”
来到北京后,日子过得平淡无奇,让人失望,校园就是人多,男男女女,川流不息,生活其间,我总有被淹没的感觉,被完全地忽视了。这些书稿成了我的心头病,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退稿退稿退稿……没完没了。
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清淡,接近水的味道,一个人独来独往,那背影变成了淡蓝色的,我总是渴望下雨,渴望早晨,渴望黄昏,这样的心情和高中的时候正相反。
一次在喝酒的时候高欢说:“小暮,你知道不,以前你的笑比哭还难看。你现在才学会笑了。”大概我真的变了。
高欢又强调一句:“而且变得无耻了,无耻知道不,就是卑鄙下流,色狼。”
我嘿嘿地笑着,他说得没错,那些郁积在心头的阴云散去了,我觉得轻松自在,我何必那样苦苦地板着脸,我的变化是应该的,我要活着,高高兴兴的活着,这就是长大了。就像牛x,亲爱的牛,不也是变了吗,当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他也一样板着脸,现在不当了,也变得无耻了起来,走在路上总是看女生的屁股,看女生的胸脯,色迷迷的。这样真不错。
我开始学会了上网,然后申请了一个QQ,取名“爱玫瑰的诗人”,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小鱼”北京女孩,那是一个绝对偶然的机会,我们在聊天室认识,我们随便聊了两句,然后我要下线,小鱼随口说了一句:“要记得快乐哦!”我愣了一下,说:“你加我的QQ吧。”
她加了我,她的头像就是一条黄色的小鱼,小鱼总是能把话说到我心里,我给她讲了我所有的经历,她说你从现在就准备考研吧,越早越好,她总是不时地鞭策我学习专业课,学习英语,她说他在北京等我,我说我考上研究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她。她说,一定。
每次下线之前她都不会忘记鼓励我一句:“要记得快乐哦!”
这是我常对温小柔说的一句话,我从没对别人说起过,我几乎已经把这句话忘记了。
这是个神秘的女孩子,常常让我想起一个人,她。我们终于网恋了,爱上一个幻影,一个无法触及的东西,那一年我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了聊天,读书,幻想之中,我成了彻头彻尾的虫子,2003年来了,我的糟糕的大学生涯就要走到了尽头,我舒了口气,天就要亮了,那个小虫子慢慢地爬到了阳光的边沿。
5
2003年3月份刚过,我们就开始变得兴奋,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然而忽然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一场瘟疫来了,“非典”传播盛行,人们开始恐慌,一时间所有的单位开始戒严。门被锁上了,不让出去,也不让进来,同学们被闷进了罐头。
时间变得前所未有的缓慢。像一个蜗牛,原地不动。有时候,我总情不自禁地嘶声喊起来,我们宿舍的那几位爷们,通常都会立刻与我互应。他们说这是一种类似于狗日的生活,大家都比较变态。对于这些观点,宿管站看门的那个干枯的老大爷是深有感触的,一天他说,不知道那个狗日的坏蛋,竟然把尿撒在了宿舍楼大门的铁锁上。害得他每一次开门的时候都摸一手臊气。
我们嘿嘿鬼笑。
后来,老头就用一条长链子锁挂住大门,撒尿的事也再没发生过,错开一个门缝,我们的寂寞就可以挤出去了,要不然,更恶心的事,保不准又是怎样恶心的东西出现在这肮脏的大门上,寂寞难耐啊,寂寞难耐。那些无聊的日子,慢慢地把我们捉去。就这样,我们无所事事的被囚禁了。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在孤单的时候,无所谓地微笑,独自在校园的每一个地方毫无规律地出没。我常在宿舍说,这是行为艺术,这是尤利西斯十年流浪。懂不懂?
他们说我扯蛋,说我得了失心疯,我不理会,庸俗的他们。
都不要说话了,我给你们唱首歌,我说完开始,撩拔着断了弦的吉他,唱着老狼的那首唱不厌的歌:
……
我只能一再地让你相信我
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
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
你和你的爱情在四季传唱
……
哎,猪,要不要打牌?牛推门进来问。
不打,我摆了摆手,牛充满鄙视地嗤了我一声,关上了门。
我打,我打,高欢尖叫着追了出来,毛子也追出去了,片刻功夫,他们竟然抬着桌子回来了,一个一个脱得只剩下一个小裤衩,牛说:我们宿舍太热了,还是你们这里凉快。我们宿舍立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众兄弟赤裸上阵,奋勇拼杀。
我依然咿咿呀呀唱着我的歌。
……
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
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
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
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
小暮,弹点别的,就那个什么……靠,别动,我出黑桃K。毛子百忙之中抽出身子,对我说,就那个对面的女孩子看过来,那个,我喜欢。说完啪地甩出一张黑桃,然后,龌龊地笑起来。
我白了他一眼,拔了个花彩,就弹起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他又点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朴树的《白桦林》我都弹了。
高欢也要点,哇哇地怪叫着,说要听《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我也弹了,然而六个人赤裸打牌,始终还是吵得厉害,他们又不是真心地欣赏我的歌,我干脆出去算了。当我出了宿舍,我才知道,外面比里面还热。浑身湿津津的,难受得厉害。路上鲜有行人,都躲起来了。如此也好。我沿着树荫转吧,在这么高温的中午出来瞎转悠的人,怕也只有我一个,开始心里还有些沾沾自喜,怡然自得的样子,走走停停,不敢越出树荫一步,半个小时之后,汗如泉水般地渗出来,T恤粘在背上,火辣辣地难受。前面一转弯就是澡堂了,幸运的是,短裤的口袋里还有两枚硬币。冲澡已是经够了,剩下五毛钱还可以弄个冰棍,于是就直冲向澡堂。
澡堂子里空无一人,我哈哈大笑。光着屁股跑来跑去,把所有的水龙头号都拧开了,那就是疯了。站在水柱下面,手舞足蹈,像个小孩子。我心里是清楚的,自己此时最多就是对自由的欲望,渴望自由。无论我怎么手舞足蹈,怎么叫喊,那裹紧肉体的东西,我始终是解不开的,我被牢牢地困着,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最后还是安静下来,在水柱下面一遍又一遍搓自己的身体,直到门口响动,又来了人,自己的世界仿佛被入侵了,恨恨地冲了最后的一遍,离开。
路上依然是空无一人,阳光正毒,能看得很清楚,远处的空气幻动,世界变软了,要熔化了,我趿着拖鞋刚走两步,背上又吱吱地渗出汗来。
我走得很慢,阳光刺得眼不开眼睛,样子不用说,很是狼狈,好不容易走完了这段赤裸裸的路,刚转弯,就听见身后有人叫我。
谁叫我?我回身问,阳光正好刺在眼上,一片模糊,看不清人影,谁叫我?
没有人应,我嘟囔了一句,转身要走。
皮子,别走,你……
皮子?我?我丈二和尚般地站在那儿,眯着眼半天才看见拐角的地方站着一个黄衣服的女孩。
你叫我?我冲她喊,看不清她,我走过去,又问了一句,你叫我?
她猛地抬起头:谁叫你,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