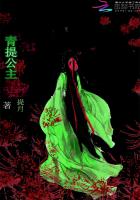悠悠扬扬的琴声自断桥处传来,琴声清涴,又带着些孤高自傲的气息。
“曾小姐的琴声很好听吗?”见齐风拉着自己朝断桥走去,弦月忍不住的问道。
“郡主是大晋第一才女,好听不好听,自己不会听吗?”齐风不明白,她靠近自己,女子身上特有的沁香,让他迷离。还有她一片纯净的笑意,像阳光一样温暖无比。
“我觉得有神却无魂,想来这曾家小姐从小就弹琴,有份功底也算不错了。”弦月看着断桥的一条奢华无比的大船。
船头坐着一个女子,女子面纱蒙面,看不清楚样子,露出的两只杏眸,顾盼生辉,只要那么一眼,便可勾魂守魄,女子身边站着几个丫环,丫环个个骄傲至极,对那些上来献殷勤的男子轻诮无比。
“以琴会知音?”弦月皱眉,古人就是喜欢风雅之事,就连身边这个坏蛋齐风也被般头曾小姐的风采迷惑了。
又有不少的年轻公子送诗,送画,送琴曲上来,可惜都被曾小姐的丫环一一回绝过去了。
这曾小姐实在是太自负,弦月拉着齐风坐在了断桥旁边的一家茶舍旁边。
“夫君,这么盯着那船头的美女看,莫不是看上人家了?”她没好气的说道。
“人家好歹有赏心悦目的地方供人欣赏。”齐风深邃的眸子,闪过一道趣味。
弦月微微一笑:“那美女可是蒙着面纱的,夫君怎知她赏心悦目?或者是个丑八怪说不一定呢?”
“郡主是妒忌?如若是丑女,肯定守在闺房里自惭形秽去了,哪里还会这般自信地公然招婿?”他看到女子眼里些愠意,嘴角一弯,勾勒着浅浅的笑意。
“妒忌?本郡主会妒忌她?”弦月一拍桌子,怒视着齐风:“夫君,如此欣赏曾家小姐,不如就把她娶回去当小妾如何?”
“郡主这是耍性子?看来权贵还女子多半刁蛮,一点也没有错!”她的样子,像只母狮子。他笑意更深。
“本郡主刁蛮,是本郡主的事,那是本郡主有这资本!”你管不着。
“天下人传闻郡主才华无双,看来仅是传闻。”他悠闲地给自己倒上茶,慢慢地饮着。
“才华无双不敢当,不过总比船头的那只喜雀有内涵!”她无缘无故生气了?自己都意外。
顿时有大片目光朝弦月这边看过来,弦月感觉四周冷冽的杀气。
她不过是说了句曾家小姐是喜雀,这些人怎么都跟她有仇似地,要将她大缷八块?
不过她觉得曾小姐那琴声,越来越让她不舒服了。
齐风只是淡淡地看着她,什么时候,迷恋她贤惠面具背后的那些小性子,有点刁蛮,有些气极败坏,还有些轻狂不羁。
他甚至不会看到,她丑陋的脸蛋,其实只要她那温暖的笑容,那脸上的黑斑,就如乌云被阳光冲破一般。
看着她摆弄着桌上的杯子,齐风幽深的眸子一片柔和,问道:“郡主这是干什么?”
“本郡主只是证明,自己比曾小姐高那么一点点而已。”弦月轻轻敲打了一下杯子。一道沉沉的声音荡开来。
她扬腕,又敲了另一个,声音清脆婉转。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音符,在她的手里,渐渐地也如一曲跳动的乐章般,生动起来。
齐风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俊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女子水袖翩然,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从杯音跳跃出来,如清清细泉,哀哀婉婉。
“断桥旁,桨声渐响。
随波逝去的有爱和你的面庞。
月夜凉,灯影摇晃。
那夜烛火和我一同相思成狂。
九曲巷,琵琶又响。
我用一生的孤独和等待奏爱的断章。
梦一场,散得匆忙。
可忘不了你说地久天长。
等到我,鬓如霜。”
女子的声音,如被风吹过的云朵般,一朵一朵的漾开来,空灵渺渺。
齐风目光更深,灼灼地看着女子手腕中漾开的音符,微风吹起女子的裙角,带着丝飘逸若仙的感觉。
弦月感觉到身边的目光,抬眸之时,正好撞上齐风灼烫的眸瞳,心脏仿佛被人撞击了一下,有一丝的慌乱。手中敲打的筷子突然落地,她的脸上有些窘迫。
围观的人本来注意力在船上的曾家小姐,身上,此时听到弦月的歌声,目光都停驻在她的身上,看得她有千疮百孔一般。
人群中一瞬间的骚乱,一个家奴带着几只个凶悍的大汉围住了白弦月与齐风。
齐风站了起来,将弦月拉近在自己的身边,目光凌厉地盯着来行的十几个人。
“就是你在捣乱?”领头的那粗犷的男子眯眸看着白弦月。
“什么捣乱?”白弦月轻描淡写道。
“我们小姐招亲,弹琴弹得好好的,你在这里干什么?又是敲碗,又是乱吼的,是什么意思。”男子指着白弦月,脸上的一片怒叱的狗腿之色。
“这位大哥,我敲的不是碗,是杯子好不好?还是,我在乱吼吗?”弦月的声音带些冷,居然说她唱歌是乱吼?
“大哥,少跟他们废话,我看这对狗男女就是来找碴的。”男子身后的十几个大汉,手里拿着棒榻,蠢蠢欲动。好些天没打过架了啊。
“你们放肆!”弦月蹙眉,怒色道。居然骂他们是狗男女?
齐风的脸色也是一青,手掌紧握得咔嚓直响,他一手拉着弦月,一个踢脚已经扫倒了站在面前的几个大汉,拉着气呼呼的女子,连跑带飞的跃过小巷。
好不容易才落地,弦月甩开齐风的手,怒视他道:“他们欺人太甚,你干嘛要跑?”
“郡主,我以为你很聪明,没想到竟然如此冲动?”齐风看了一眼弦月,大步迈出。
弦月一愣,她白弦月从不低调行事,今天的事情,怎么能就这么完了。她从来都是有仇必报之人。
半夜,夜色如水,寒意碜人,喻城曾家遭遇洗劫,府里的主子奴才们都被人下了药,睡得若死猪,洗劫的人倒是心狠,一片纸片也没有也曾府留下。